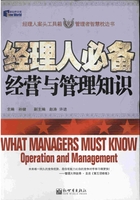--关于它的准备、实现和日期诸问题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开始,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它的准备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几十年来,罗尔纲同志作过很多考证研究,为后来者认识这一段历史作出了贡献;简又文在其《太平天国全史》中也有《金田起义记》专章。但由于文献残缺,记载分歧,理解互异,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
本文是对金田起义的准备和过程的探讨。其中有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和分析,有对这一过程中某些问题的考证和研究。仍以"金田起义记"为题,而内容则有所异同,以示旧题新作之意。全文共分八段,即:
一、关于拜上帝会与王作新斗争的事实,认为其结果并不是王作新和地方封建势力的胜利;
二、冯云山事件时拜上帝会的危机主要来自内部一些人各搞神灵附体传言而引起的矛盾,杨秀清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是拜上帝会内各种力量消长之一大转折;
三、探讨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和基本群众队伍的形成,分析穷苦人民和客家人在拜上帝会中占多数的原因;
四、分析拜上帝会在起义前面临的几种社会力量:封建官府、地方团练、"盗匪",认为广西封建统治的软弱是拜上帝会起义的极大有利条件;
五、关于金田起义实现过程的事实,认为被称为金田起义史上第一件大事的李殿元封锁花洲山人村,是不存在的;
六、关于金田起义的"日期",认为金田起义包括了洪秀全通知各地会众汇集金田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是指发生于一段时期内的事,而不是指发生于某一天的事,因而不可能指明某一天是金田起义日;
七、关于起义时期人数、给养来源和称王建国等问题的研究考证,并认为"米饭主"制度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迥不相同,没有渊源关系;
八、关于太平军在大黄江口、武宣东乡、象州中坪等地盘旋战斗的事实,认为这一过程是金田起义的继续。
文中所有这些看法和其他论述,都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
关于金田起义爆发的缘由,久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清朝地方官吏对拜上帝会压迫过甚而临时发动的。其最初的根据主要来自洪仁玕。他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689页。)又说:"初时并无举行革命之计划,但因官与兵之压迫及残害为吾人所不能屈伏,并无别路可走故耳。"(《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6册,822页。)但洪仁玕这一说法,与他自己对韩山文的述词不符,在那里,他说:"他(洪秀全)早已制定了他的计划,并准备好了承受其后果,只等适当的时刻到来,就采取决定性的一步。"(《太干天国起义记》第十节,此处译文,据英文原本重译。)金田起义前洪秀全的许多活动都表明,所谓起义是临时激变之说,看来是不确实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已作了很好的辨明。关于金田起义缘由的另一种说法是,洪秀全在1843年应试落第后即蓄反清革命之志,经七八年之筹划准备而实现了起义。从太平天国始终以上帝教立国而洪秀全之始拜上帝和宣传上帝教起于1843年这一点来说,也可以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始源于1843年;但这里说的是反清武装革命,从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斗争的角度来说,洪秀全在政治方面为起义所作的准备却不是从1843年而是从1847年以后才开始的,因为在此以前洪秀全本人还没有确立革命造反的思想。(关于这一问题,参看本书《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所以,关于金田起义的准备,这里从1847年谈起。
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1847年7月21日)第二次去广西。这是他在罗孝全处学道受洗不成而直接从广州出发,于七月十七日在紫荆山见到冯云山,获知了拜上帝会发展的情况。一个多月后,"主(洪秀全)与南王冯云山、曾沄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处所栖身焉"(《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2册,648页。)。这至少对洪秀全、冯云山来说,是他们酝酿反清斗争的一个标志。洪秀全随即由大冲曾家移居于形势险固的高坑冲卢六家。("高坑冲在紫荆山西南部,东、西、南三面都是大山,冲口向北。从冲口北行三里就是蒙冲,西进七里就是大冲,北越山岭可通黄泥冲,南越"瑶老界",就是鹏隘山。冲槽曲折狭窄,林箐茂密,形势远比大冲、黄泥冲险固。"见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72级:《太平天国起义几个问题的调查》,载《文物》,1975(1)。)
洪秀全等在此后进行的宣传独拜上帝、不事偶像的活动,明显具有政治色彩和政治作用。在此以前,洪秀全在家乡也宣传拜上帝,但只限于不事偶像,除去偶像,包括灶君、门神和孔子牌位。他与冯云山分手后回到花县两三年,未见有捣毁花县的神像寺庙的记载;在八坜教书时早晚都要经过水口庙,但从未毁打神像。然而这一次重游广西并选择了险固处所安身以后,紧接着就兴师动众前赴象州打甘王庙,这是异乎寻常的举动。
"甘王"是桂东南著名的神道。据说五代十国时期象州古车村有甘陆其人,从征南汉有功,其侄甘佃"家饶好施",生前都有法术,善决吉凶,能为祸福,死后为人所祀,但被合二而一,称甘王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浔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之郑献甫等撰《甘王庙碑记》,油印翻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这部《浔州府志》原刻本,未署编者姓名及刊刻年份,但从《例言》、《职官表》、《大事记》可以判断,此志系光绪十七年(1891)起任知府的夏敬颐主持编纂,刻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以后。
本书以下引用,均称光绪《浔州府志》。)甘王庙在浔州府城、桂平县弩滩、紫荆山马河所在都有,而以本籍象州甘王庙较为显赫。这里的甘王威力大,为人畏服,曾附灵于一少年身上强迫州官给予龙袍,而这位甘王又有许多恶行:"生时极信风水堪舆之说。曾有一风水先生为其择得一好穴,但同时谓如用血葬,全家必得大福。此人于是回家杀死其母而葬之于此穴中,借谋自身及子孙之后福。彼又尝逼其姐与一下贱浪子通奸。彼又最爱听淫荡歌曲。"(《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见《太平天国》,第6册,859页。)这一切都触犯拜上帝会的宗教道德信条。于是洪秀全决定擒贼擒王(紫荆山内的甘王庙近在咫尺,洪秀全并未去捣毁。《重修紫荆马河镇灵宫甘王庙碑记》称:"迨咸丰贼乱,庙貌倾圮,过往彷徨。"这是说因战乱而致倾圮,并非捣毁。这也可见去象州打甘王庙是经过选择的。),破象州甘王庙以立上帝教之威,于10月26日偕同冯云山、卢六、曾沄正等到象州捣毁其偶像,撕烂其袍服,打破其香炉祭器,写十天条贴于壁,并题诗于壁:
题诗草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妇女雷当劈,害累人民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见《太平天国》,第6册,860页。)
冯云山也题诗一首:
奉天讨伐此甘妖,恶孽昭彰罪莫逃。
迫我弟妹诚敬拜,诱吾弟妹乐歌谣。
生身父母谁人打,敝首邪尸自我抛。
该处人民如害怕,请从土壁读天条。(《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2册,650页。)
洪秀全等打毁甘王庙后,象州人悬赏缉拿犯事者,但甘王的神灵却附在一童子身上说:"这些人是纯正的,你们不可能伤害他们,你们只须重修我的神像便了事吧。"(《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译文据英文原本作了修订。)于是就取消赏格,不敢追究此事。显然,所谓童子附身,很可能出于洪秀全等的安排。
接着,洪秀全等又毁除了紫荆山内的雷庙及田心水、花雷水一带的社坛。社坛,即土地庙,在当地极普遍。所谓雷神,陈姓,广东海康人,也是华南一大神道。("神姓陈氏,名文玉,海康人,唐时为海康刺史,有功德于民,民祠祀勿衰。"不无意思的是,洪秀全打了雷庙,而洪秀全的远祖洪迈曾为雷神加封。见姚福均:《铸鼎余闻》卷一,《雷庙、雷神》。)
洪秀全打毁甘王庙和这些神像的激烈活动,起了一定的动员群众的作用。迷信鬼神是当时人民的普遍现象,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所熟悉的为他们敬畏信服的鬼神,甚至连州县官也害怕,忽然被捣毁,被制服,这必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有些人看到他们的神道并不灵验,就会把敬畏信服之心移向另一个更高明、更有力的神--拜上帝会的独一真神;而且,洪秀全、冯云山所宣传的独一真神也具有若干中国化、民间化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和满足这些迷信的人民的精神上的需要。(这一问题已在本书《"拜上帝会"释论》一文中论述。)这样就使拜上帝会信心大增,信誉日起,信徒日众,渐渐成为地方上的一大势力。另一方面,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也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造成拜上帝会活动的困难。但群众中赞成和反对两种态度的分化,是使事态得以发展所必需的。它使矛盾逐步激化,使拜上帝会和反拜上帝会双方势力的分野日益分明,这在客观上是进行一次武装起义必不可缺的过程,是起着有利于发动革命的作用的。
捣毁偶像等活动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发生的当地绅士王作新捕捉冯云山的事件。王作新是紫荆山石人村人,与其堂兄王大作都有秀才的功名,颇有田产。冯云山初到紫荆山教书传教时,曾与其有往来。当洪秀全、冯云山大张旗鼓捣毁神像后,王作新率领一些人捕捉了冯云山,但被拜上帝会教徒卢六等夺回。王作新先后控之于江口巡检司和桂平县。其向桂平县的呈控书说: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桂平县紫荆山生员王大作等,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乞恩严拿究办事。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业经两载,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紫荆山内水分左右)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某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查,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乡民,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妖匪党曾亚孙、卢六等抢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伏乞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则沾恩无既。( 方玉润:《星烈日记》,据桂平知县李孟群著《鹤唳篇》节录,见《太平天国史
料丛编简辑》,第3册,82~83页。)
王作新等代表着地主阶级和传统封建势力向拜上帝会发动进攻,拜上帝会抢回了被王作新拘捕的冯云山,这使双方发生了短兵相接的冲突。王作新于是向封建衙门呈诉,请求支持,而奇特的是桂平县知县王烈却严厉地驳斥了王作新。知县的批示是:
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应知条教,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呈禀,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 方玉润:《星烈日记》,据桂平知县李孟群著《鹤唳篇》节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82~83页。)
桂平县知县之所以采取这一态度,一方面是由于洪秀全、冯云山虽然以打毁偶像的激烈行动来动员和积聚力量,但当时终究只是在宣传拜上帝的范围内行动,即所谓"要从西番旧遗诏书"。而对于拜上帝,当时清朝政府根据外国传教士的要求,已经明令弛禁。至于所控的"不从清朝法律",并未能举出确实证据;另一方面,当时清朝官场腐败颟顸,官吏只顾搜刮,其他一切都以敷衍放任为主,宁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辖境内发生重大事故,所以桂平县知县也不愿王作新多事。关于这一点同太平天国兴起的关系,下文还要论及。
桂平县知县要"严提两造人证质讯",于是江口巡检司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差传冯云山、卢六到案解县。(据同治《浔州府志》、民国《武宣县志》等分别记载,王作新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次捉拿冯云山时,有洪秀全在内,但洪逸去;王作新十二月十二日再次捉拿冯、洪、曾、卢四人送江口巡检司而该司只解冯、卢二人到县。按据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方面追查此案的结果,王作新并无第二次捉人之事,冯云山、卢六是江口巡检司差传到案解县的。这应是执行桂平县知县"严提两造人证质讯"之批示。)冯云山也先后向江口巡检司和桂平县提出了申诉:
具诉童生冯云山,系广东广州府花县民籍,为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乞究索诈诬控事。……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二十四年冬,某到紫荆山探表兄卢六,次年设教高坑冲,又次年设馆曾玉珍家,又次年复馆。只因遵旨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某谨将唐虞三代书句开列,伏乞鉴察。(方玉润:《星烈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83页。)
冯云山避开了打毁偶像之事着重从合法的宗教宣传方面进行了巧妙的辩护。王作新起获缴官的"冯云山抄书一本",知县认为"内有"耶稣"二字,系西洋天主教书","尚无违悖字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邹鸣鹤奏审拟失察冯云山案件官员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另周天爵奏"抄书"作"会簿"。在现存的太平天国早期出版物中,《原道觉世训》、《天条书》均有"耶稣"字样。但《原道觉世训》中有"他是何人,敢然称帝"之句,虽非专对清帝而发,也构成了对帝王的不敬。所以这本被抄缴到官的书,可能就是《天条书》写本。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冯、卢被拘后,拜上帝会弟兄曾将十天条呈送县官,请求秉公审查。)。冯云山已被解送到县,但原告王作新却屡传不到。这是由于在拜上帝会已有相当的势力而知县又不支持他的情况下,他只好外出躲避,不敢出庭。但不幸的是,卢六在羁押中病故了,冯云山乃于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1848年5月30日)向浔州府控诉:"为恃衿横嚼架题寻害,号宪严牌饬县提讯以雪无辜事。"(冯云山解县和向浔州府呈控日期,均据《邹鸣鹤奏审拟失察冯云山案件官员折》。)浔州府知府顾元凯批示:"冯云山因何讦讼送解到县,桂平县立查案讯明,分别究释具报,慎勿稽延滋累。"(方玉润:《星烈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83页。)这对于冯云山也是有利的。继任桂平县知县的贾柱判定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以无业游荡之名将冯云山押解回广东花县原籍。(据顾颉刚先生生前告知,他曾听他的祖父说,桂平县把抓到的冯云山送到府里,顾元凯看冯是个读书人,以教书为生,谅不致成造反之大事,便把他放了(顾颉刚先生和顾元凯同出一房,顾元凯十一世,顾颉刚先生十六世)。从这一口碑可以推知,桂平县知县把冯云山解送回籍,也是顾元凯的意见。)但冯云山却在途中说服了两名解差信仰上帝教,一起回到了紫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