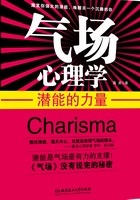关于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最典型的是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的: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君见祭,甚善,但常为蛟龙所窃,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此外,《襄阳风俗记》也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举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也。其实,一切传统习俗都是当下的,都具备此时此地性。因此,端午节尽管产生很早,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逐渐附着在了对屈原的纪念上也就不奇怪了。屈原热爱故土,又写有极具楚地色彩的《离骚》,因此被广泛纪念也不奇怪。屈原于是独享了这个中华民族的重要节日。
因此,端午节其他的风俗如龙舟竞渡,本为驱邪避灾而生,也逐渐与纪念屈原叠合。从此,屈原、楚辞、端午节合为一体,从而也具备了某种时间上的永恒性和空间上的超地域性。
楚辞还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风尚。
梁启超曾经说:“《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梁启超讲读书》,13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后来,尤其是建国之后把楚辞定位为一种“浪漫主义”文学,其审美也是一种“浪漫主义”风尚。这个概括当然是不合适的,“浪漫主义”这个术语主要来自欧洲,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审美意义,套在楚辞身上颇显不伦不类。但是,梁启超也的的确确看到了楚辞之不同于《诗》的审美风尚。这就是楚辞带给中国文化那种非中庸的、充满想象甚至有些神奇怪异的审美风尚。
楚辞的渊源之一为祭祀之巫歌,因此,楚辞也带了“巫”的色彩。从《离骚》中龙马骖璃、周游宇宙的宏大想象,到《九歌》中“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的山鬼形象,无不刺激着后代文人墨客的神经。如李白、李贺的诗歌,八大山人的画,郑板桥的字。他们都以与众不同的审美风格而独树一帜,并且为别人所不能模仿。
此外,宋玉《九辩》中的悲秋之情,也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悲秋”之审美风尚的来源。
同时,楚辞对审美风尚的影响还体现在戏剧、音乐、绘画领域中楚辞题材的大量出现。比如郑思肖,宋亡后发誓不与北人交往,取号“所南”,隐居在苏州的时候坐卧不北向。据《遗民录》记载,他画的兰花不画土,所以根部露在外面,有人问,他就说:“地为人夺去,汝有不知耶?”他的书房名曰“本穴世界”,意即“大宋天下”。他最擅长的是兰花,而兰花也正是屈原的所爱。郑思肖曾自题画兰云:“一国之香,一国一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楚辞之影响,略见一斑。
而古代绘画史中“楚辞图”、“屈子图”更是数不清,前者的代表如宋代李公麟所绘的《楚辞图》;后者如陈洪绶绘的《屈子行吟图》等。这些题材以及其中的审美色彩,也是受楚辞的影响。
楚辞中的神话也影响了中国文化。
中国的神话并不发达,楚地却独独有着相对完整的神话系统。不过,楚辞中的神话已经经过了作者艺术的过滤,逐渐摆脱了那种狰狞与可怕的形象。从此,这些神话塑造的天宫地府、神仙精灵,也慢慢进入了普通民众的世界观。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对天地宇宙,万物生息都有着自己的看法。称之为迷信也好,称之为民间信仰也罢,这种世界观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它受制于中国庞大且复杂的神话系统。
中国的神话在发展中与道教、佛教有着密切关系。但是神话的早期文献也就是《山海经》、《淮南子》以及楚辞等。楚辞的影响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楚辞本身就不局限于一本书、一个人,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也不仅限于文学艺术,而是从个人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三)楚辞与中国古代之文学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主张:“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也。”他将骚体置于“文之枢纽”地位,就宣示了楚辞对后世文学发展深远的影响力。
在当代,楚辞主要被看作文学作品。纵观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楚辞无疑处在这条河流的源头处。姜亮夫曾在《楚辞今绎讲录》中说:中国文学史自从有了楚辞,特别到了汉代,得到汉高祖的提倡,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因为它适用于整个民族的语调。楚辞是楚民族文化的精华,几乎取代《诗经》的地位。唐代诗人,据说有人不读《诗经》,但没有人不读楚辞的。要是没有屈原的作品,就不会有我们后代文学的这个发展,或者说我们后代文学的发展不会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子,像汉乐府,唐人律诗,宋以后的词曲等,可能是另外一个路子。姜亮夫的这段话,并不是过誉之词。诗、骚两大文学传统对文学史的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前者似乎主要规定了中国文学的思想品质,而后者才保证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质。这种审美品质也是极丰富的,小到词语的斟酌、句式的使用,大到个性的张扬、思维的飞翔。下面,就楚辞对文学的影响略作片断式的讨论。
第一,从形式上看,楚辞开创了独特的文学形式,并直接推动了赋等新的文学体裁的形成与发展。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一点在本文的前面也已经详细论述了。其实,汉代人自己也是这样看的。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王逸认为楚辞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汉代诗人们仍然热衷写作,并高度赞扬了楚辞的优点首先就是“华藻”,显然他认为这种词句的华丽是楚辞所独有的,也就意味着是《诗》所不具备的。
而六朝骈文对辞采的重视,对华丽辞藻的追求,楚辞之“华藻”也是功不可没的。
楚辞这种形式上的影响,也集中体现在“兮”字的使用上,后代诗人也常常写“骚体诗”,就是一种句式灵活、使用“兮”字,但又与楚辞并不相同的诗歌。严格来说“骚体诗”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体裁,但能够看出楚辞对诗歌形式的影响。
第二,从内容上看,楚辞中对楚地山水的描摹影响了后代山水诗的产生;楚辞中包含的远游的内容,影响了后代游仙诗的产生。
楚辞中无处不充满着对楚地景物的细腻描写,当然,这也是楚地的美丽所成就的“江山之助”。比如《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写秋天之洞庭的佳句;再如《山鬼》中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句子,也是描写气候景物的佳句。
显然,楚辞对景物的关注,远远超过《诗》。
当然,在屈原、宋玉等人眼里,这些景物并非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情感在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要到六朝“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才出现。不过,楚辞的开创意义亦是相当巨大的。
第三,楚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性,正是从屈原开始,中国的诗人们才真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或激烈或温和的情感,诗人才真正“像”一位诗人。
屈原在《惜诵》中有“发愤以抒情”的句子,这既是对楚辞抒情色彩的精妙概括,同时也开创了这样一种抒情传统。这一传统也同时被后人所发扬光大,其中不仅有诗人,也有其他的文人作家。
比如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把这种抒情传统继续发挥为“发愤以著书”,他的《史记》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从此,这种发愤抒情的传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著作。
如李白,他的独立人格与屈原很相似,都张扬着个体的精神。当然,李白生在盛唐,与屈原的衰楚不同,因此李白人格中体现的盛唐气象把这种个性发挥到了新的高度,甚至达到了中国古代诗人的顶点;他的诗歌充满着瑰丽的想象,他与屈原都对梦境有着独特的感受,也都因为梦境而写出横绝一世的诗篇。
再如曹雪芹,其《红楼梦》对人生存于时间之内所产生的无常之感,在楚辞中那些对时间匆忙流走的哀叹中也能找得到;《红楼梦》对人的个性的维护、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与屈原亦是合乎同一节拍的;而《离骚》中香草美人的陨灭,与《红楼梦》中众多女孩子的随风飘逝,都代表了美好的毁灭。这种悲剧内涵的一致性,恰好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和尽头得到了统一。
这一点,陆侃如亦曾在《宋玉评传》中说过一段话:二千年来,所谓“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读他的作品的,读了也没有一个不崇拜的。二千年来无数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屈原的影响的,没有一个不以屈原做模范的。所以扬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说屈原死了便“无堪与言”,所以苏轼说他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只有一个屈原。
从他的作品里,产生出赋,产生出骈文,产生出七言诗,“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二千年来,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节,竞渡角黍之风普遍了全国。这一个令节,几为他一人所独占。在长江流域一带,连穷乡僻壤都会有他的庙宇。这一种福气,是没有第二个文学家能够赶得上的。总之,楚辞对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且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