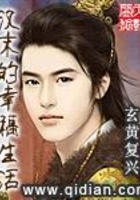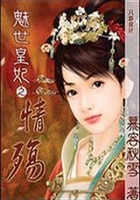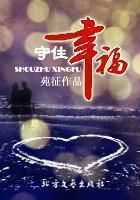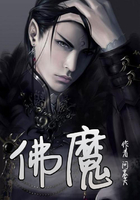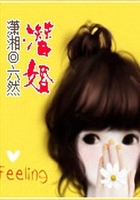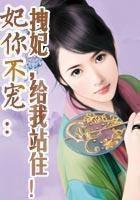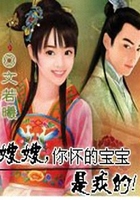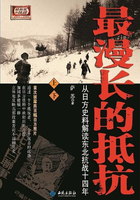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来看新文化史如何在诞生以后 ,又如何持续变化的发展。美国英国文化史的专家、46岁就去世的嘉内特 ·奥本海姆 (Janet Oppenheim)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虽然奥本海姆英年早逝 ,但她在去世之前,已经出版了三部著作。像亨特的研究一样 ,奥本海姆的研究 ,也体现了一种从旧文化史到新文化史的转型。她的第一本著作 ,出版于 1977年,考察的是英国政府如何通过资助艺术创作和博物馆收藏 ,塑造一种民族文化。这一研究,有近代传统的痕迹 ,因为考察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但奥本海姆的视角,则已经注意到了政治与文化、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互动。而更有趣的是 ,在出版这部著作以后 ,也就是在亨特写作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的时候 ,奥本海姆则在研究近代英国文化 ,而且将视线转到了边缘的角落。她的后面两本书 ,一本有关占卜和算命 ,而另一本有关精神忧郁症这样的社会问题。而正是这两本书,使她成为美国英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
小的就是好的
因此 ,当今 “新文化史 ”的研究 ,并不特别注意事件的大小 ,也不特别在乎该事件有无典型意义 ,也就是该事件是否能说明问题 ,抑或 “以小见大 ”。他们并不十分在乎这个 “大”,也就是历史的特征和走向等 “大写历史 ”的问题。换句话说 ,即使写了这个题材 ,只是以小见小 ,他们也无所谓。但要将小的、似乎没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写好 ,叙述的文学性、生动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当代史学与文学的交融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后现代主义从理论上强调历史学和文学没有很大的区别 ,引起了史家的注意。
同样是写小的东西 ,当然还是有上下之分。小的题材很多 ,史家可以不加选择 ,但史料的有无和多少 ,则不得不考虑。如有名的 “微观史 ”、“新文化史”著作《奶酪与蛆虫》,就是一个例子。卡罗 ·金茨葆 (Carlo Ginzburg)不但文笔生动、故事讲得好 ,而且他所讲述的故事 ,还能折射当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书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普通的磨坊主 ,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之所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拷问 ,正是因为他不但对新的科学知识 ,有所掌握 ,而且还加以宣传 ,引起了教会的恐慌。不过 ,这些看法 ,基本上是读者、特别是同行史家看好这本书的原因 ,而金茨葆本人 ,并没有强调他写作《奶酪与蛆虫》,就是为了说明科学知识在下层社会的普及。
金茨葆的做法 ,其实也不是绝无仅有 ,而是大有人在做。如在中国史的领域,以前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的田汝康教授 ,就写过有关理学思想、特别是贞节观念普及的著作。田先生是伦敦政经学院毕业的 ,其专业其实就是社会人类学。他在文革以后 ,长期在海外研究 ,著述很多。我曾经有幸在一个场合 ,有缘与他在海外重逢。他在《男人的焦虑和女人的贞节 :明清两代伦理观念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 ,其实理学家的女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观念 ,虽然在明清以前就提出 ,但真正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要到明代中期以后。所以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交流 ,有一定的时间差。
有关上、下层文化的交流 ,的确成为了 “新文化史 ”研究的一个重点。法国年鉴学派的第四代领头人罗杰 ·夏梯艾 (Roger Chartier),就提倡对书的印刷、出版和流通的研究。显然 ,书籍的印刷和出版 ,是文化上下沟通的渠道。所以书的历史 ,成为当今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这一热点在中国史研究中 ,也有反映。如香港出身、后来到美国随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攻读博士的周启荣教授,现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他在 199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明清转型时期的礼教文化。到了近年 ,他的兴趣转到了明代出版业的研究。他与美国学者包筠雅 (Cynthia Brokaw)一起编辑了《明清的印刷与书文化》,同时自己还写作了《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和权力》,主要探讨明代的出版业的繁荣及其影响。
包筠雅的书文化研究 ,以福建的四宝印刷行业在清代的发达为对象。她的《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宝的书籍交易》,牵涉了许多问题 ,都是 “新文化史 ”关心的问题 ,如男女的识字率、书籍印刷与普及教育之间的关系、书籍作为商品的交易与流通状况等等。包筠雅指出 ,四宝印刷的书 ,希求薄利多销,大都是为了符合一般读者的需要 (如科举考试、休闲阅读等 ),所以从中可以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不过她的研究虽然精细 ,而且篇幅巨大 ,但在结论部分 ,她几乎都没有表明自己的一个明确的观点 ,像明清时代的商业文化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 ;城市文化又发展到什么程度 ;男女的识字率又有什么定论没有。这些重大的问题她都不谈 ,虽然她都讨论 ,但是都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论点。这也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仅仅 “叙述 ”、不做解释的新文化史的做法。
在中国史的领域 ,耶鲁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也被人视为 “微观史 ”的专家。史景迁的确写过如《王氏之死》和《胡若望的疑问》等篇幅不大、事件也小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英文世界里 ,影响很大 ,因为它们从一个小的角度 ,展示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一个方面。当然 ,它们的流行,显然也得益于史景迁本人流畅的写作手法和精巧的构思。
史料与史识
要写小的题材 ,所以也并不容易。需要有一定的史识 ,然后很好的文笔。但历史写作的问题是 ,你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小的、有趣的题目 ,但相关材料不多,整个故事很难连成一篇、言之成理。这个时候如何处理。以前的史家 ,不敢随意猜测、强作解人。但 “新文化史 ”的实践者 ,则常常突破这些常规。这里有名的例子就是当代著名的 “新文化史 ”的代表人物娜塔莉 ·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 ·基尔的回归》。这个故事的情节许多人都知道 ,我在《后现代与历史学》的书中也提到过 ,所以只要简单地讲一下就可以了。一个叫马丁 ·基尔的人 ,因为与父亲争执 ,离家出走。那时他已结婚 ,并育有一子。若干年以后 ,他回来了 ,他的叔叔和四个姐姐都认可了他。他的妻子还与他又生了孩子。但是叔叔起来疑心 ,特别是当这个马丁想与他争夺财产的时候。最后他们之间就打起了官司 ,但马丁的妻子则一直维护他。最后在法院有点相持不下的时候 ,真的马丁回来了。他离家以后 ,去了西班牙 ,后来又参了军,在战场上瘸了一条腿。假马丁被处死 ,在临死的时候 ,他承认了自己假冒的行为。
以前人们阅读这个故事 ,一般都认为可能马丁的妻子有点蠢 ,居然会被人骗。但戴维斯的解释 ,却与众不同。她说马丁的妻子其实知道真假马丁 ,只是因为当时教会势力强大 ,如果丈夫去世 ,妻子也无法轻易改嫁。而她的丈夫又许久没有回来 ,所以就干脆认贼作夫了 ,以求过一种家庭的生活。戴维斯的批评者说 ,这样的解读 ,表现了明显的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 ,而与史实不符 ,因为马丁的妻子如果知道真相而故意隐瞒 ,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她应该不敢、不会这么做。
这里的问题是 ,史料只有这么一些 ,就是当时审讯的记录 ,其它的都是史家的解读。这些解读 ,自然有猜测的成分与合理与不合理的地方。而戴维斯的研究 ,能为许多人接受 ,正好说明了史家观念的改变 ,所以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新文化史 ”的兴起 ,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戴维斯的著作 ,也为当代许多史家激赏。她在出版《马丁 ·基尔的回归》( 1983)的四年后 ,也就是 1987年,成功当选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 ,成为该学会的第二位女性的主席。
这种引申式的解释 ,在另一本有名的 “新文化史 ”的著作《猫的大屠杀》中也有反映。该书的作者是罗伯特 ·达顿 (Robert Darnton),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教授 ,刚刚退休成为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达顿也是法国史的专家 ,他的哥哥是一个有名的、《纽约时报》的记者 ,而他本人也做过记者。因此他虽然是专业史家 ,但文笔精彩。他在研究法国近代早期历史的时候 ,发现 18世纪的时候 ,在一个小镇上 ,有一批学徒杀死了许多猫 ,而且还从中取乐 ,好像很得意的样子。他就解释说 ,这是因为这些学徒 ,长期受主人的压迫 ,生活十分压抑 (包括性压抑)。而这些猫却得到师傅、特别是师娘的宠爱 ,过得比他们还要舒服 ,所以他们就心存不满。他们故意在晚上学猫尖叫 ,引起主人的讨厌。最后当主人说要他们把猫抓起来 ,然后驱走的时候 ,他们就趁机泄愤将这些猫给吊死了。达顿的研究 ,受到他当时的同事、人类学家吉尔茨的许多影响。他想通过这一奇特的事件 ,描写一个特点社会的群众心理和集体行为。但达顿将学徒杀猫的行为与他们对主人、也即师傅的不满 ,加以联系 ,则显然是一种延伸的解读。还有 ,这些学徒在吊死这些猫之前 ,还对它们进行审判 ,把这些猫视为巫婆 ,或许也有发泄性欲的成分在内。而且猫在西方语言里的一个称呼 ,也可以指女性的性器官。
但是 ,如果以近代史学的标准衡量 ,这两部畅销的著作 ,其实对增进人们对宏观历史的理解 ,帮助不多。它们的成功 ,主要是因为题材新颖的、独特 ,而且叙述精致、吸引人。以戴维斯的《马丁 ·基尔的回归》来看 ,照以前的观点来看 ,只是讲了战争对一般人生活影响的一个侧面。但对于当今史学 (社会史、妇女史等 )的关注来看 ,则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例子虽然特殊 ,但有助揭示当时的文化氛围和家庭关系。达顿的《猫的大屠杀》,也许可以从中看到中世纪行会的内在问题 ,但它的受欢迎 ,则显然不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些著作的成功 ,也展示了史学界观念的剧变。
达顿在 1999年也当选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上面提到的史景迁 ,虽然在美国的中国学界 ,常常有人批评 ,说他阅读史料的粗疏和解读的随意 ,但他也在2004年当选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今年 (2010)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劳瑞尔 ·乌里克 (Laurel Thatcher Ulrich),也称得上是一位 “新文化史家 ”和 “微观史家 ”。她的主要著作叫《一个助产婆的故事》,讲的是一位普通的、生活在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位助产婆的生活。乌里克所用的材料 ,在她的副题已经标明了出来 ,就是主人公本人的日记。当然乌里克在写作中 ,做了不少加工。该书对了解早期美国生活的家庭生活、两性关系、妇女地位、医疗卫生等许多方面 ,都有帮助。但也许最主要的是,像前面提到的几位 “新文化史家 ”一样 ,乌里克文笔漂亮。她的《一个助产婆的故事》获得了不少奖项 ,其中包括美国新闻界的大奖 —普利策奖。
由此可见 ,“新文化史 ”的兴起 ,是史学走向文学的一个反照。一部 “新文化史 ”的成功 ,必须要有精彩的题材、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文笔。就像上面所说的 ,如果史学不再专注对历史的动向 ,做出解释 ,那么历史著作写作的好坏,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为什么报告文学不是史学?
其实 ,这种基于基本的历史事实 ,但又适当进行一些文字加工的尝试 ,在中国由来已久。以前中国的历史写作有 “演义 ”体,现代又有 “报告文学 ”,都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知识。依我看来 ,“报告文学 ”应该成为历史学的一支 ,不应简单地把它看做是一个文学体裁。因为许多的 “报告文学 ”,都依据核实过的历史资料、甚至一些私密的档案写成的。它们与史学著作的不同 ,主要在于没有引文出处 ,作者也会根据内容 ,编写一些对话。但是 ,其实在许多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历史著作中 ,这种情形也到处可见。比如被誉为古代的 “科学史家 ”的修昔底德 ,就引述了不少演讲词。这些演讲词 ,不可能都是由他亲自听到而且笔录下来的。但我们从来没有质疑修昔底德卓越的史家地位。同样 ,司马迁的《史记》,也有一些精彩的对话和活灵活现的描写。这些都表明 ,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距离 ,从来就不很远。比如毛泽东就称呼司马迁为中国古代伟大的 “文学家 ”。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西方当代史家的一些作品 ,可以见到他们对于故事叙述的偏重。如史景迁写作《王氏之死》,就采用了一些我们看来是野史、甚至包括《聊斋志异》的材料。这样的做法 ,中国史家可能不太敢做的。但我看来却是有点自缚手脚。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史学专业化之后 ,对于历史研究的精深化 ,显然是有好处的。因为史家的写作 ,要受到同行的检验。但是 ,如果专注同行的意见 ,则往往会丧失历史著作的可读性。报告文学之所以比历史作品更有市场 ,就是这个道理。换句话说 ,我们在求真的时候 ,也要注意可读性。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们对三国时代史事的了解 ,是通过阅读陈寿的《三国志》还是通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是后者。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就是因为罗的《三国演义》,比陈的《三国志》,更能吸引人、更有可读性。在如今 ,许多人想了解三国的历史 ,又读易中天的作品或听他的讲座。而想了解明代历史的人 ,则又常常通过阅读网路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
所以我们又回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优劣的问题上了。其实这是历史学内部的一种张力、一种对立。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平衡 ,不要顾此失彼。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 ,不太容易。“新文化史家 ”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也就是恢复被科学史学所磨掉的史学原来具有的文学和艺术的成分。这也是后现代史学思想家海登 ·怀特许多论著的主要意图。不过为此目的 ,“新文化史 ”和后现代主义 ,都走得有点过远 ,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历史解释在史学著述上的重要地位 ,而将这一工作拱手让给了政治学家、未来学家等等。有关这一弊病 ,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