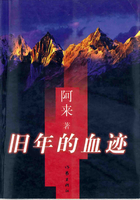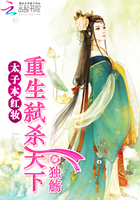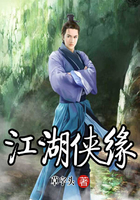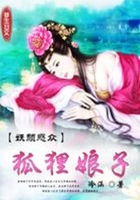这种安慰毕竟是暂时的,片刻的平静过后,忧虑之情又隐隐泛起。这使得士人不禁要起疑虑:是否自己就只能选择做一个怨妇,苦苦地期待着国君的眷顾,甚至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士人在赞慕屈原高洁品性、哀叹屈原不幸命运之外,开始了对屈原的反思,有那么一刹那,他们觉得屈原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执著,贾谊《吊屈原赋》云:“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司马迁对此亦表示认同。班彪《悼离骚》亦云:“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引则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
贾谊、司马迁和班彪对于屈原还只是“一声叹息”式的遗憾与惋惜,扬雄和班固则已有明显的责备批判之意。扬雄《反离骚》一再地批评屈原不能审时度势、深隐自藏;不能和光同尘,高蹈远引。班固《离骚序》亦批评屈原“非明智之器”,认为屈原之“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终至“以离谗贼”,有悖明哲保身之旨。
这种对屈原人格命运的审视和反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士人已经开始自觉地思考人格理想、处世态度等问题,他们的价值观较之屈原也已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使他们逐渐靠近了《庄子》,“逍遥游”思想给了他们不少启发。东方朔的思想历程正好反映出了这一时期的士人是如何从骚走向庄的。诙谐幽默的东方朔对于他们这一代士人的处境却有着最为严肃清醒的认识,其《答客难》假设客人向作者问难,嘲笑他虽有“博闻辩智”,却难与苏秦、张仪的地位相比,然后主辩解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战国之时,诸侯并争,“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谈说之士,身处尊位,而如今天下一统,朝廷掌握用人大权,贤与不肖已没有区别。文章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在汉代大一统局面下才智无所施展的压抑感,作品采用说反话的形式,充满了牢骚不平之气。其另一篇文章《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之口,发表“谈何容易”的感慨,也是抒写不遇之情的作品。但东方朔没有止于发牢骚,他开始积极考虑处世之方,庄子优游处世的思想影响了他,他采取了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随时应变,与物俱化。其《戒子》诗云:“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 《歌》曰:“陆沉于俗。”表现出了对庄子思想的直接接受。
如前一节所论,东汉中后期,文人的思想情感起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此前士人所关注的只是个人“遇或不遇”的命运,那么,此期士人关心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的存亡走向;如果说此前士人对这个社会还充满希望和热情,那么此期的士人意识到世界已不可救药,不再对它抱拯救的希望;如果说前期士人对于现实政治是依附的,那么此期士人已经开始尝试着从这种依附关系中游离开去;如果说此前士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时命,此期士人则开始主动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这样,士人的精神离骚渐远而靠庄愈近。
这种变化反映到文学领域中,即是文学的不遇主题演变为述志主题,顺世而游转变为超世而游,文学中对于社会政治的哀怨和牢骚转为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这一时期,文人多在诗文中表现自己的志趣选择,如张衡《思玄赋》、《归田赋》,仲长统《见志诗》、《昌言》,郭泰《答友劝仕进者》,冯衍《显志赋》,徐稚《与郭林宗书》等。而士人的人生选择都建立在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张衡审视眼下之世:“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只怀忧”(《思玄赋》),《归田赋》云:“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渊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审视的结果是“谅天道之微昧”,自己只能“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郭泰察人事,观天象,明时势之不可挽救,“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于是毅然离去。而仲长统 “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请旷,以乐其志。”(本传)他的思路更近于庄,其人生选择非为一时一己的遭遇而作。
存绝世之志,士人开始追求一种超世高蹈的行为方式,仲长统《见志诗二首》云:“至人能变,达士拔俗。”“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其二“大道虽夷,见机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 冯衍《显志赋》云:“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们找到的是庄子的遗落世事,随化而变。
士人还开始于现实生活之外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张衡翩翩有仙想:“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然仙不可求,于是他走向了田园,“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归田赋》),仲长统、冯衍、郭泰等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这一条归隐之路。仲长统《昌言》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郭泰云:“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他们开始自觉地思考死亡的问题。跳出屈骚式的价值观念,他们发现生命原来属于自己,死亡的恐惧于是来得更加真切。而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也与屈原不同。张衡《冢赋》详细设计自己将来的冢的位置、构造,表明他已经将死亡当成了一个非常私人化的问题,他没有像屈原一样将死亡视作实现某种价值理念,成就生命理想的手段。死亡就是死亡,是生命的自然过程,其《髑髅赋》接受了庄子的死亡思想,认为 “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况我已化,与道逍遥”,人死之后,与自然合一,“造化为父母,天坠为床褥,雷电为鼓扇,日月为灯烛,云汉为川池,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
救世的热情回落,文人开始与现实政治疏离,他们对于这个社会倒是看得更清楚了。屈原只道自己的悲剧是有奸人作怪,楚国的君主只是被谗言蒙蔽,而这时期文人则认识到了整个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对之加以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赵壹《刺世疾邪赋》即是代表作。赵壹生活的顺、桓、灵三世,正是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为祸最烈、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赵壹性情耿直,愤世嫉俗,他在该赋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祸乱不止,生灵涂炭。秦汉以降,统治阶级更是自私自利,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更加恶劣,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无耻之徒得富贵,刚直之人沉下僚。他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认为社会罹病的原因,实是执政者不贤明,被群小包围,不辨是非。“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喜垢求其瘢痕”,爱憎任性,以致忠诚报国无门。国家危在旦夕,执政者却仍在贪图享乐,这无异于涉海而失柁,积薪而待燃。在这里,庄子的现实批判精神得到了有力的嗣响。仲长统《昌言》中《理乱》、《损益》、《法戒》诸篇,纵论天下盛衰,为政得失,礼义刑法,政教风俗等,对当时社会弊害揭示颇为深刻。且矛头所指,不避帝王权贵。因此,仲长统被研究者评为“魏晋士人批判精神的先驱者”。并且,由其《见志诗》,可知“仲长统批判社会丑恶,汲取了老庄道家精神”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西汉至东汉末,庄、骚交换了主角和配角的位置,而《庄子》一旦登上主角的位子,终魏晋之世没有退下。需要指出的是,屈骚并没有从这一时期的阅读视野中退出,甚至还有人提出作名士只需常饮酒、熟读《离骚》晋王恭说:“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但魏晋士人对于屈骚的解读却与汉人有了根本不同。如同前文已论及的由汉到魏《诗经》接受的转变,魏晋人在屈赋批评实践中也不再像汉代人那样重视对屈赋进行政治功利批评和道德伦理批评,而是更重视对屈赋作文学评价,重视对屈赋文学精神和文学意义的揭示,关于这一点,已有研究者论及。这里以曹丕与扬雄对于屈原、相如赋的评价为例:
扬雄《法言》: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
(《文选·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
曹丕《典论·论文》: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北堂书钞》卷一百引)
曹丕所论看似承扬雄法言而来,但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二人评论的着眼点已有了明显不同,扬雄所论尚着重屈原、相如赋的内容,而曹丕已多关注二人之赋的修辞、文势。由此可以管窥此期学术、文学批评转向的信息。此期的仿骚之作也多侧重楚骚的文学形式,如东晋前期庾阐仿楚辞作《涉江赋》,但主要状江中物色,而兴托不寄。
而更能体现魏晋时期庄骚艺术传统转向的是,魏晋人在对屈原人格进行评价时,或者以庄子的眼光来进行批判,或者竟将屈原人格庄子化了。
前者如李康、曹摅、挚虞等。三国时人李康,性介立而不能合俗,其《运命论》一篇,以不遭明主之怨骚起,以乐天知命之达庄终,他论屈原曰:“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文选》。以庄子之达观来看屈原,则屈原就不是为后人仰慕的圣人了,因为“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乐天知命矣!”西晋曹摅作《述志赋》,对屈原之无辜遭忌表示同情,但从其赋作的整体思想倾向可知,他仍然觉得明哲全身的处世哲学更高一筹。此外,挚虞《愍骚赋》也表现了度时以进退之意。谢万作《八贤颂·屈原》,称赞屈原人格“玉莹冰鲜”,然而《八贤论》以处者为优而出者为劣《晋书》。屈原比之渔父,作者抑扬之意自见。
这种批评思路显然是对班、扬一系的继承,而另一种思路,即对屈原人格作庄子化的解读,更能体现这时期的思想特色。
西晋文学家陆云尝作《九愍》以拟楚辞《九章》。其《序》云:“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遂厕作者之末而述《九愍》。”一个“玩”字颇具意味,它表明作者对于离骚已经不再是“入乎其中”作同命相怜式的哀叹,而是带着“出乎其外”的超越心情来赏玩。《九愍》依《九章》拟题命意,分《修身》、《涉江》、《悲郢》、《行吟》、《纡思》、《考志》、《感逝》、《征》、诸章。其九云:嗟有生之必死,固逸我以自休。彼达人之遗物,甘褰裳而赴流。矧余情之沉毒,资有生以速忧。悼居世其何戚,固形存其为尤。想百年之促期,悲乐少而难多。修与短其足吝,曷久沈于汨罗。投澜漪而负石,涉清湘以怀沙。临恒流而自坠,蒙濬壑之隆波。接申胥于南江,于。鼓层云以携手,仰接景而登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