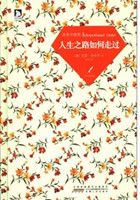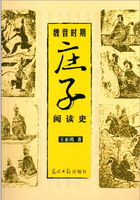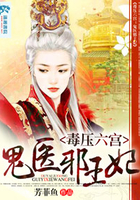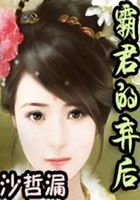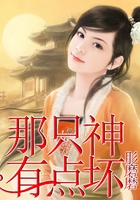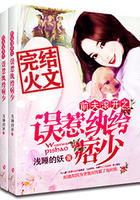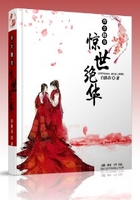王阳明心学在理论上继先秦心性之学,又集宋明以来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其思想并不是直接传承哪家学说,而是像明初陈献章一样,完全出于“自得”。他的心学更是个人实践道德的产物。本篇分心理合一的人性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致良知”的实践道德本体论、心物感应的论证方法、“万物一体之仁”的道德理想等几章来论述其思想体系。
人性论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论证“心”本体的关键一环。王阳明的人性论,其核心内容是将心、理合一,这是他对朱熹学说的批判,也是对陆九渊学说的发展。朱熹哲学以基于自然观的客观“天理”为宇宙本体,推衍到人,形成以“格物致知”为主旨的人生道德学说;陆九渊哲学以基于人生伦理内容的“本心”为本体,主张明心,将本心扩展到社会、自然、宇宙,当作主宰一切的本体。他们虽各成一说,却都没有将自然与伦理的两方面内容融为一体,因而形成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两种不同趋向。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欲将朱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一方面他要纠正朱熹“天理”论的客观倾向,同时又要弥补陆九渊心学在本体上论证的不足。于是他别开生面,避开了本体的思路,不是从自然观上论证“心”本体,而是从人性、人的道德意识根源方面探索宇宙本根,说明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这样,在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上,王阳明亦不是注重自然观上生成过程的推衍,而是着重汲取道家的自然人性说。在这点上,他又与明初的陈献章归于一路,或说有某种暗合之处了。
一、以“心理为一”为论证起点
人性论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最初形成于他对朱熹“心理为二”问题的批判。所谓“心理为二”,在世界观上通常指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在朱熹理学特定的伦理主题内,则有着它特殊的内容。这就是朱熹为了解决“理”所具有的自然与伦理、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特性的矛盾,遂把自然观的“理”、“气”论推衍到人性论,人的性、形作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他把“理”
当作人的道德理性本质,用“气”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知觉活动,于是人性便被分为本于“天理”的“天命之性”和杂于形气的“气质之性”,人心也被分为主于义理的“道心”和主于知觉的“人心”。
朱熹从“天理”出发对人性、人的精神现象所作的这番分析,分割了人的意识现象,忽略了人的认识和修养是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忽略了人的知觉、情感中有义理,人的形气、视听言动也无时不受理性支配,具有伦理性;从而将不能截然分开的“性”与“情”、“道心”与“人心”分而为二。陆九渊反对朱熹把理性与精神分割的说法,他的“心即理”命题把“本心”看作人的道德理性,认为这就是主体人生活动的主宰;他又反对理欲及理气之分,认为只要恢复本心、断绝外物,便可由本心来支配人的一切道德行为。他这种说法把“本心”当作绝对至善的道德理性,却无法证明人何以有“恶”的思想意识及行为,所以陆九渊的心本论是不完满的。王阳明提出“心理为一”,正是要解决朱熹及陆九渊在本体论上所遗留的这一问题。
王阳明主张心理为一,他出于论证实践道德的需要,迫切要求把主观与客观合一,以说明封建社会固有的仁、义、礼、智不仅是客观的道德规范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制约,更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人心固有的天然本性。因此,他把具有伦理本性的个体之心当作宇宙本体,用它来同化封建道德的内容,以形成修养论、认识论与本体论一体化的结构,达到社会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的融合统一。
王阳明以人为世界的中心,把天地万物都从人的思维现象推出来。这样一来,其哲学的出发点已不再是概括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客观观念、抽象天理,而是具体的心性,人的道德性和主观精神。他剔除了朱熹哲学中与自然知识相关的内容,把“理”的内涵直接限制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这样就省去了从自然到社会的烦琐推证,把“理”直接放置到每个人心中,以便对人的行为发挥最大的效用。
为了用封建阶级的统一意志去主宰个体意识,为了说明封建伦理即为人们判断是非的共同价值标准,他把“天理”的固有内容与个体的心理活动相结合。其次,由于把人心当作世界的本体,还必须说明人的心性不仅是社会伦理本性,也是一种自然本体,才能找到人与万物统一的基础。
王阳明心理合一的人性论正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
二、心性合一
王阳明主张心性合一。他对性的全部论述都是围绕着心性的统一,即道德与心理活动的一体关系展开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见性即是明理
王阳明首先就天人关系、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来论性。他提出了“见性”的观点,认为“性”没有一定的格式,古人论性不尽相同,只是“所见有浅深”,“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也只是“说性”而非“见性”。“见性者无异同之言”(《传习录下》),性的本体与发用、源头与流弊,都只是一个性,只有从性的不同方面看到它们统一的本质,才是“见性”。这种“见性”的思想直接驳斥了朱熹把性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截的观点。
王阳明认为“见性”就是“明理”。因为性即是理,“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传习录上》)。不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之四德都只是“性之表德”。性本身是不分天人的:“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同上)他把天、帝、命与性、心平列,实际上把天道合于人性之中,无形中降低了“天”的地位,把“天命”与“人性”混为一体了。
王阳明强调心性的一元化,其实质是把思维当作人的唯一本质,用思维去统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说:“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他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因此性、情、才、质都只是人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形上、形下之分。“仁义礼智”是先验的道德观念,“聪明睿知”是先天的才质和认识能力,“喜怒哀乐”是先验的心理情感,它们都源出于一“性”,这就是人性、人的天性。即使被朱熹看作与“天理”完全对立的“人欲”,王阳明也极力从精神的统一性方面来作解释。他以为“私欲客气”虽是“性之蔽”,但这种蔽也是出于人的精神中固有的原因,它是由人的先天气质不同和情感发用不当而造成的对至善道德的蒙蔽。因此,性是没有内外的。
(二)“心即理”与“性即理”
心理合一是王阳明人性论的中心思想,而“心即理”是从“性即理”合乎逻辑地推衍出来的。程朱提出“性即理”,把伦理学上人性善恶的问题提到本体论的高度,同时也就规定了“理”所具有的封建伦理的内容。但是这样的“理”是离不开心的,也就是说,“理”在道德意识方面的内涵决定了它与人的主观精神的联系。王阳明对“心”与“理”的融合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提出了“心即性,性即理”(《传习录上》),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把“性即理”引向了“心即理”。
关于“心即理”,王阳明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同上)他把“理”完全归到心中,其理由有三个:第一,“至善是心之本体”,“至善只求诸心”(同上)。他把“天理”当作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社会政治领域中一个“至善”的极则,并认为“至善”是人的本性,人对任何事物的判断标准都不是来自于客观,而是来自于主观之“心”。他说:“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同上)第二,他认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是人伦之爱,这也根源于人“心”。就大的方面说,“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孝悌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同上)。就每个人讲,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道德原则,不决定于他是否懂得封建道德知识和具体的礼节,而是看其有没有“诚心”,例如对父母“温凊定省”的礼节都只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同上)。第三,他认为有没有“诚心”也是社会上通行的判断道德行为的是非标准。他说:“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因此,“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同上),二者是不可分析而言之的。
王阳明在论说道德意识及道德行为的来源时,看到了人们在一定社会中通过长期社会生活所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念及主观意向、情感意识的作用,把它们当作人所先天固有的道德性。他把先天道德论的原则与封建伦理的特定内容结合起来,得出了“心即理”的结论。“心即理”改变了朱熹哲学中天理的客观性质,使“理”成为人的主观道德意识、主观价值原则。王阳明提倡“心即理”的目的是为了“合心与理而为一”,把封建道德性与人的思维特性结合起来,以便使封建道德的实行具有更加切实可靠的基础。所谓“心、理合一之体”,也就是人的心性,是以封建伦理为特征的知觉思维特性。
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是他由“心即理”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三)性气合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吾心之良知即是天理”,实际上是用主观天理取代了客观天理,随之而发生了天理与人心知觉(即直接涉及天理和人欲)的关系问题。因此,王阳明提出了“性气合一”的观点,进一步为“心理合一”作论证。王阳明说: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 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
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传习录中·答周道通书》)
他用性气的不可分离性来论证性理与知觉的关系。以往朱熹以为言“心即理”即混同了道德之“理”与精神之“气”,以“性”为知觉会使人的行为失去准则。王阳明则认为气与性本来浑然一物,不可分离。人的知觉中有义理,知觉本身就蕴含着天理,所以道德就是精神,理性寓于感性之中。他用“气即性”说明人的精神活动包含着道德伦理:“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传习录中·答周道通书》)又用“性即气”说明封建伦理本身具有精神的能动性,它不是客观的抽象理性,而是寓于人的生命、精神活动之中的“良知”:“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传习录下》)合而言之,他以为“知是理之灵处”,是“良知”的能动性使得理具有可行性,人只要“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停当。故曰……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同上)。
三、“心即天”,心性与自然一体
王阳明以“心”本体论为基础的人性论,还涉及“心性”的起源,即人与自然、心与“天”的关系问题。王阳明认为:“心即天”,“心”没有任何外在的来源;人的心性是一种自满自足的天然之性,它不仅是标示社会人事的范畴,也是代表自然的范畴;心的活动充满宇宙,“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全书》卷五)。
在人性与自然的关系上,王阳明吸收了道家生命哲学的思想。
他以为人心即是自然,它所遵循的全是天然之理,没有任何私意的掺杂,人为的成分,“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著,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传习录下》)“心”的一切活动都在其“天然自有之中”(《传习录中·答聂文蔚》)。只是他把这种自然归为一种先天的道德性,以为具有封建道德特点的“良知”即是人心之自然,是人生命以及言行的最终根源。他说:
“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传习录下》)王阳明以良知为心性自然的这种人性思想,固然不同于道家庄子以自然为宗、摒除仁义和人伦关系的人性自然说,但却已把道家的养生思想融于其中。他说:“养德、养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与陆原静》)即是企图把道家养生原则用于封建道德的修养。又说:“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答人问神仙》,《全书》卷二十一)则更是明显地提倡道家的“全形”、“保真”、顺乎自然的养生之术了。但王阳明吸收道家的养生思想,目的还在于说明“良知”这个道德本体不只具有封建伦理特征,也与人的思维活动、生命运动密切相关。他把道德与精神的关系归结为理、气关系,从本体上统一了人与宇宙、社会与自然。
他说:“‘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但后世儒者之说与养生之说各滞于一偏,是以不相为用。”(《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为了阐明上述观点,这里着重分析王阳明“气”的范畴。
王阳明的“气”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它不同于朱熹理学中那种与理相对立的构成万物质料的形气之气,而是以人的生命运动、意识活动为背景的一元之气。这种“气”既包括了崇尚精神自然的庄子思想,又继承了孟子“养气”说的内容。
我们知道,庄子哲学的“气”是一种偏于自然含义的“气”,其本身无情义而又与人的生命现象直接相关,所以庄子讲“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庄子·逍遥游》);“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孟子哲学的气则主要指社会道德方面,它具有仁义的特点,与人的心理活动、精神状态密切相关,是以“志”为帅,“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就气的范围讲,庄、孟的“气”都是充满宇宙、与天合一的一元之气。所以孟子说“塞于天地之间”(同上),“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而庄子主张圣人“贵一”,“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达生》)。
只是他们“气”的功能以及生成和培养的方法不同。庄子的“气”是自然生成、自然变化的,他主张“动而以天行”,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顺乎自然本能。孟子恰恰相反,他要人们通过人为培养,一方面明义理,一方面坚持“集义”的道德实践,以便养成“浩然之气”。很明显,这种气具有巨大的精神能动性。
王阳明吸收了孟、庄两家“气”的主要含义。他用“元气”来说明精神活动的统一性,认为元气、元神、元精“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传习录上》)。他以气的凝聚来表达“以理言”的“精一”之精,就是说人的精神活动是由天理来主宰的,天理就是人的“良知”:“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他以为“良知”就是“天地气机”的“主宰”,人只要“主宰常定”,就能“与天运一般不息”。他说:
“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传习录上》)在心性修养上,他主张既要发挥精神能动性,又要顺其自然,他以为人体之气兼有伦理与自然的双重特性,是一种神气合一,精神与物质浑然的气。他用孟子的“养气”说来贯穿人的心性与天理,阐明人的伦理本性;又利用道家及庄子的“养生”之气来表现人的生命本质、自然需求。
融会这两种气,他证明了人的社会伦理本性离不开自然的心理欲求,而人的心理自然状态又依赖于道德的“主宰”,因此人是“与天地合德”(同上),天人是“同此一气”(《传习录下》),万物是成其一体之仁的。
王阳明以这种理气一元论为基础,得出了他的良知体用、良知自然的思想。这是他的人性论的最终结论,也是他“心”本体论的核心思想,现简述如下:
1.良知即是“天则”。良知是先天的道德原则,也是天然的心理准则。它与人的知识、能力、情感浑然一体,是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自然心理需求。王阳明说:“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传习录下》)“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
2.“道德”为良知之“体”,“精神”为“良知”之用。良知是具有封建道德特征的伦理本体,又是有知觉特性的精神本体。封建道德是人心“天然自有”的,它与精神活动的关系是良知的体用关系,这样,道德与精神被统一在良知的体用关系之中:“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传习录下》)王阳明承认良知的活泼性,其良知发用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见闻、思虑、情感的精神活动以至声色货利相交的物质欲望。这种活泼性也就是天理所具有的知觉性和人趋于天理的精神能动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传习录上》他在赋予天理主观性的同时,把人的精神活动纳入了封建伦理的轨道,置于封建道德的桎梏之中了。
3.封建伦理秩序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宋明理学中,人与天、精神与道德、自然与社会的最高统一,就是把封建伦理秩序说成自然的、宇宙的永恒规律。王阳明是用主观唯心主义语言来表明这一点的。他说:“《大学》所谓厚薄,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传习录下》)又说:“良知只是一个……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他把仁义礼智信说成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从而把封建秩序归结为人们心理的自觉需要,用主观内省的道德修养来保障它的可行性。这样,所谓天人“同此一气”、“万物一体之仁”,都是以现实封建社会为蓝本的。良知的平等也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维护封建社会的阶级差等。因此,所谓“良知体用”、“良知自然”,不过是把封建伦理强加给宇宙和自然。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是没有什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