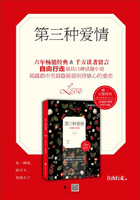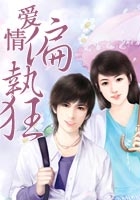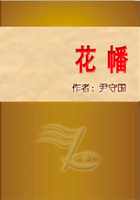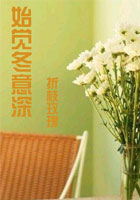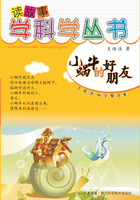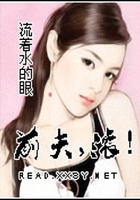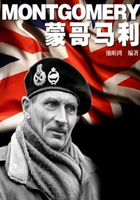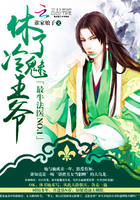其二为共时性的“跨域”。现代小说颠覆了那种单轨走向的时间模式,常常把故事时间加以调整、分散、切割、交叉与重构,改变了原有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进程,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水平时间”。吕红的中短篇小说往往打破传统的线性时间叙述的思维方式,将时间的时钟上下摆动、前后颠倒,把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转换成为五彩缤纷的现实空间,如同多幅不同的空间图案拼贴在一个更大的画框内。而这种“共时”又常常是“跨域”的共时。吕红的中短篇小说娴熟地运用了这种“共时性”叙事,打破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放置或大或小的意义单位和片段,这些意义单元和片段组成一个相互作用和参照的整体,常令读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种阅读第一遍很难理清头绪,常常需要多遍的反复,美国著名移民作家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谈到阅读时说过:“等到我们读第二次、第三次或是第四次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是在欣赏一幅画了。”他把这种拼贴图画非常形象地隐喻为“魔毯”。读《午夜兰桂坊》这种感受特别强烈,这个中篇的现在时是梦薇在香港弥敦道上巧遇梦薇,这只是一个现在时间的画框。作者在这个时间中,不时转换空间画面,时而北京、时而美国、时而香港。穿越一个个地理空间,梦薇与海云两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国内职场的打拼、移居美国的艰辛、商海的沉浮以及女人的婚姻种种都容纳其中了,它是在共时中的“跨域”。在《微朦的光影》中,同时展开了三扇时间的“屏幕”,或日三条线:一是主人公“芯”为朋友送别,陪同这位画家到旧金山一家影院看法国新浪潮电影《广岛之恋》;二是观看影片过程中,《广岛之恋》的屏幕影像与对白的片断闪现与链接;三是“芯”观看影片中心里涌上的离别旧梦,那一段远隔重洋、发生在故国的刻骨铭心之恋,同影片中的故事交错穿插,形成两条时间流,一个是在旧金山影院的屏幕上流动,一个是在心中的梦幻般的回忆中流动,多年前的广州、香港,与情人分别……影片结束,“芯”与朋友告别,咀嚼着一份失落和彷徨,又回想起当年与故国情人离别的情景……这里,三重时间重叠交织,现实与朋友看电影告别的时间、屏幕上《广岛之恋》情节发展的时间、回忆中与情人的心痛往事,构成“同时性”,这里的同时性同样具有“跨域”的特征,而把三者勾连起来的内核是痛苦的“恋情”。
它还表现为时间断裂的“跨域”。这种“同时性”表现为小说人物在当下时间的“瞬间断裂”,意识呈现出幻觉、梦境、潜意识等审美幻象,这种幻象又往往表现为故乡的图景、人物,或故乡与异乡的“跨域”双重图景的拼贴、重组、交织,使意识坠入暂时的时间“黑洞”。吕红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种诗化的意识流动,它是一种现实时间的瞬间断裂,小说中的人物回到主体心灵之中,进入梦幻状态的时间流。在《午夜兰桂坊》中,梦薇夜宿在海云新买的高级住宅楼想起好像是一部巴西电影,写一个女性与三个男人的情爱纠葛,她迷迷糊糊进入梦幻状态:像是在一间军队招待所?他按捺不住澎湃激情就要干;恍恍惚惚有个面熟的男人,就在办公室,他又搂又抱欲强行亲吻,霸王硬上弓(啊,想起来了);分不清是梦里还是真实。在海边之夜,她跟一个帅哥手牵手,去游玩,一忽在海中畅游,一忽在水中嬉戏,肌肤相亲……“是电影的蒙太奇吗?还是梦境?”这种主体心灵的意识流动也是“跨域”的,不仅时间上下恍惚流动、如梦似幻,同时也穿越了东西方的空间场域。
三
现代社会,影视对小说的影响与渗透已形成大潮汹涌之势。艾森斯坦说:几个世纪以来,各门艺术好像都在向电影靠拢。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⑥移居西方的吕红早就与电影结缘。当初她学习创作,就曾尝试过电影剧本写作,到美国后又观赏过大量西方现代派、新浪潮电影,并写下了不少影评与随笔。观赏影视大片的视野与西方名家经典的双重交互作用与浸染,使她对电影情有独钟。她对新锐电影导演的《暗物质》、《颐和园》的解读,对西方影片《情人》、《广岛之恋》的分析,都有精辟的见解与独到的阐释。吕红的小说创作无疑也受到了这种视听语言强大的冲击与影响,她的创作,明显地打上了“电影化想象”的痕迹,她试图在这种新的艺术中找到对小说全新而又有益的表达技巧,凭着对异域生活的敏锐感悟力、对影像艺术的潜心研究,她成功地借鉴了视听叙事的技巧,并将“视觉思维”(强调视觉的理性知觉功能)融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其小说叙事在思维的层面上与影像艺术存在共通相融。吕红小说借小说中的人物说:“还有什么比视觉冲击更能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呢?”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看做作家本人的坦言。她小说中的影像叙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凸显色彩与光影。阿恩海姆说:“严格说来,一切视觉表象都是由色彩和亮度产生的”,“色彩产生的是情感体验”。新移民作家的故乡记忆中常常忘不了色彩。她写部队生活题材的作品《曝光》’记忆很深刻的是灰色与红色:“说也奇怪,整个师部包括团营部、高炮连、防化连、警卫连等,都是清一色的灰砖瓦房、清一色的土包子,唯独医院却是红砖红瓦的小红楼。从红楼出来的男男女女也都是细皮嫩肉、稀稀拉拉的。看电影个个手持一把特殊化的靠背椅,在教导员沙哑的喉咙发出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中’晃晃悠悠走向操场,受到男性们注目礼的待遇。”这里凸显的是灰色与红色。灰色是写实,也是部队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生活单调的写照与象征,而红楼却透露出一群富有活力的青春女兵的生机与朝气。这两种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强烈的视觉感。
环境描写是构成电影感的重要元素,吕红很擅长抓住建筑物的特征、捕捉色彩、窥察光影,勾勒描绘城市景观。她对美国都市的描写五光十色,斑斓炫目,多姿多彩,充满异域风情。如《日落旧金山》中对汇聚民俗风情的意大利区、中国城、越南埠艺术景观的描写;《漂移的冰川和花环》中对百老汇红灯区景观的勾画;《微朦的光影》写旧金山同性恋区的卡斯楚剧院街景:红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的彩虹,在头顶飘荡,在霓虹灯上闪烁等。凸现的是色彩与光影,建筑物的造型、色彩的斑斓、光影的变化等,营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色彩景观。
如《日落旧金山》中对这座城市街景、异域风情的描写:“年前一个烟雨蒙蒙的午后,旧金山好像水墨画一般氤氲迷离。滋润,柔情,抚慰,洗透肺腑,雨中的各式建筑浸染渗透了海滨城市特有的浪漫情调:这里“烟雨蒙蒙”、“水墨画一般氤氲迷离”、“雨中的各式建筑的浪漫情调”,这里突现的是雨中的黑白灰的色彩,水墨底色,浓淡相宜,又显光影层次,如同电影脚本的写景一般,给人极深的视觉印象。
第二,镜头般的动感画面。小说中的画面感与影像艺术中画面的运动性是一致的,在吕红的小说中,表现为对色彩、表情、动作、道具等视觉元素的综合运用’在引起人们视觉冲击的同时又充满了动感性,犹如镜头中的画面一般。而且,这种镜头般的画面中往往有着很大的容量,潜藏在画面呈现的瞬间,“影视与物象的亲近性,主要不是来自于二者形体上的相似,而是二者都处于一种动态(时空运动)中。”
《不期而遇》中有一段描述:“银色的新款跑车在她等候的门口潇洒地划了个漂亮的弧形,戛然停下,好像小提琴家风度优美的即兴表演,芭蕾舞王子的轻快跳跃,游泳健儿从高台上弹起又纵身跃入碧波,自然连贯又戛然而止,一瞬间显露出高超流畅平滑的身体技巧。”这段文字不长,却同时包含了色彩(颜色、碧波)、动作(车划弧形又戛然而止)及对这一动作的三个充满动感的比喻(小提琴家的表演、芭蕾王子的跳跃、游泳健儿的跳水),引发读者的想象,造成视觉冲击力。《漂移的冰川和花环》中对唐人街除夕夜景的一段描写,摩天大楼灯光璀璨,海湾大桥的背景,钟楼下的人群,疯狂的冰上表演,醉鬼扔酒瓶,黑衣警察巡逻……街景与人物合成为具有动态感的镜头。
第三,蒙太奇叙事与表意。前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说过:蒙太奇就是电影的一切。吕红深谙蒙太奇式画面组接的艺术技巧,叙事中常常打破了时空限制,呈现出中断性和跳跃性,以句子或段落拼接,获得了悬念迭起、疑惑纷呈的叙事效果与独特魅力,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极为神似。她小说中的这种时间跳跃、空间场景转换往往以人物为轴心,它不仅是两个情节片段的组接而具有的叙事作用,同时着重于表达人物的某种情绪或情感,兼有蒙太奇叙事与表意的功能。
短篇《不期而遇》中,萧萍在舞会上,那位男子上前邀请她跳吉特巴,在激情的旋律中,那男子说好久不见,你好吗?下面紧接着是“原来是你,认出他,萧萍也有些意外”,下一段接上“那年,他和她在舞会上相遇”的一段,把旧金山的一场舞会与当年在上海的舞会组接起来,这两个段落将相距多年的中、美空间连接起来,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且让人心生悬念,产生一种期待效应。《微朦的光影》是吕红融入电影元素比较集中的一个短篇,在男女主人公观看电影《广岛之恋》的叙事中,娴熟地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六次变换时空,把镜头转换到多年前广州、香港的往昔,如前所述,形成三条时间流。小说中运用蒙太奇手法将旧金山、影片中故事情节的地理位置与广州、香港三个空间发生的事件组接起来,获得电影一般的蒙太奇效果:它既是在叙事、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在表现人物情绪的流动起伏。影片中的人物命运与现实中的人物互为交织、甚至有点纠结难分,给读者的感受也是多重而复杂的。
吕红是一位艺术感觉敏锐而富有才情的女作家,又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文学素养,在充分肯定她的创作成绩的同时,也有更高远的期许:如题材的拓展,艺术视野的宏阔,深邃的思索与现代艺术技巧的有机整体融合等。期望她能超越经验叙事,突破已有的审美范式,升腾、飞扬想象的羽翼,开拓新的创作空间,写出挑战自我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