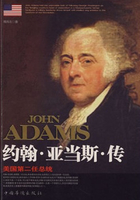穆思云的长发随意的披散在肩后,她不太记得自己到底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梳理自己的头发了,身上的睡衣好像也有三天没有换下来了,脚上就穿着一只拖鞋,另一只或许在这屋子的某一个角落,不过这一切对于她来说都并不重要了,真的不重要了。
穆思云就这样坐在木地板上,初夏的微凉与微热仿佛是天堂和地狱一般将她的身心都给折磨得通透。她一直低着头看着因为要撕太多的婚礼请帖而变得红肿的手,十指的破损比比皆是,不过请帖还有太多,看来今天是撕不完了。
在过去她从未做过任何的家务,双手皮肤细嫩,十指纤细修长,直到她决定自己在这里操持家务,为了将来的婚姻和家庭做准备开始,她努力地学习各种的家务,只是现在看来那时候一心一意的她傻得可爱,然而那摆放在面前正对着五十寸液晶电视的六十寸油画架婚纱照中甜蜜笑着的两人就像是最残忍的刽子手在看着遍体鳞伤的她,那被她随手丢在沙发上雪白的长拖尾婚纱更是象征着她这段还没有完成婚礼仪式就已经结束的不幸婚姻。
所有的东西都在寂静之中嘲笑着她,嘲笑着她这个从不知人心险恶的小姑娘变成还没有穿上婚纱就离婚的愚蠢女人的人生。
或许,穆思云的人生已经因为叶长永的骗财骗色而宣告失败,她作为豪门千金的所有幸运与幸福都在她不听父母劝告的时候宣告结束,她这辈子的第一次自主的行为换来了自己无法面对的悲惨结局,可是……这又如何?
她已经一无所有。
穆思云深呼吸了一口气,艰难的从地上起来,双腿因为在地板上盘坐太久所以非常酸痛,只是她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在登记结婚以后,她听信了叶长永的话,以为他当真因为生意失败而欠了外债,再加上她一直负担着叶长永父母的开支,完全不会想到他们一家老小合伙骗她,十五万的现金以及一辆崭新的奥迪,这一切对于过去的她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可是对于已经离开家里,刚用自己的存款买了房子以及筹备婚礼的穆思云来说,这已经是她名下所有的积蓄了。
这套房子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和水电费都已经不少,穆思云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不得不将主人房外的一间房间出租,那里本来是她打算作为婴儿房使用的房间,可是现在却成了她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了。
房屋中介说那可以豪爽支付每个月三千五百元来租一个房间,与她同屋的租客这几天内就要搬进来了,所以她必须在对方来到以前将房子打扫好,所以那张挂在墙壁上的六十寸婚纱照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取下来!
穆思云用力地将那张长沙发推到一旁,然后踢掉脚上唯一的一只拖鞋以后踮着脚尖用力的想要将那六十寸油画架的婚纱照从墙壁上取下来,其实她知道自己一个女人是完全搬不动这张巨大的婚纱照的,可是这里就只有她一个人,她已经无人可求。
没由来的,穆思云想到了自己那位远在欧洲的堂姐穆思音,比她年长四岁的穆思音是欧洲有名的女商业家,美丽,强势,才华横溢,并且从不为自己的婚姻担心,因为她身边不缺乏追求者,如果将那些男人聚集起来惊讶的发现任何国籍任何人种都有,完全就是一只联合国军队。只是……穆思云过去并不明白为何穆思音要游戏人间,因为她无法了解穆思音条件优秀为何就不能为爱情多花点心思,可是现在穆思云明白了,一个女人并不是自愿成为一个女强人的,那只不过是她没有找到一个能让她依靠的男人罢了。
在没有能让她依靠的男人出现的时候,女人往往能顶起一片天,她的天地里有太多为她喝彩的男人,唯独缺少了那可以给她一个世界的男人。
本来,穆思云以为叶长永会是可以让自己依靠的男人,但现在事实证明群众的目光的雪亮的,一直不讨她身边的人喜欢的叶长永最终证实了不过是一个骗子。
双手托着那沉重的油画架好一会,穆思云依旧没有办法将婚纱照从钩子里抬起来,于是不得不将肩膀也顶了过去,有着精明花纹的油画架狠狠地压着她的肩膀,华丽纹路之下是一片红肿。
就在穆思云被压得连气都几乎喘不过来的时候,一阵门铃响起,本来温和的门铃声此时此刻仿佛是最尖锐的哨子声,声音划破屋内的寂静,将穆思云狠狠地吓了一跳,随着她的颤抖,那已经被她好不容易托着离开了钩子牵制的婚纱照猛地滑过她的肩膀从墙壁上摔了下来,一阵巨响以后,玻璃的架面便成了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