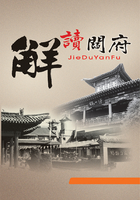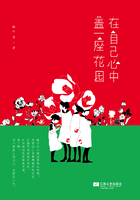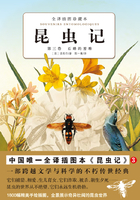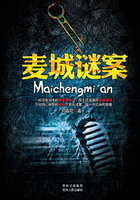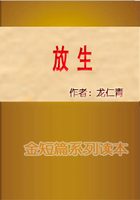正值秋收时节,我从中共越西顺河区委会去保安乡,途经番族聚居区新桥高级社时,遇着大雨,便在番胞家里借了一宿。所见所闻和受到的热情招待,真使一个素昧平生的过路人,久久地不能忘怀。
番胞好客 名不虚传
一进村,只听鸭扑鸡啼,一堆堆的玉米、荞子放满晒坝,社员都冒雨出工了。几个老婆婆见来了客人,热情地跑到村口来接我们。刚坐下,又是烟又是水,并特地给我们砍来一捆玉米秆解渴。歇了一会,我们便到党支部书记周阿呷家去借宿。
周阿呷同志到乡上开党总支委员会去了,只有她的女儿阿衣嫫在家。这孩子虽然才十三四岁,并且不会说汉话,但一见有人来却笑嘻嘻地跑出来,只顾把我们往屋里拉。进了屋,我们连挎包还未放下,她就端来了一簸箕煮熟的洋芋,叫我们吃。正在推推拉拉的时候,冒雨进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婆婆,她赤着脚,查尔瓦里包着一簸箕热气腾腾的洋芋。一见阿衣嫫叫我们吃冷洋芋,就责备开了:“小孩不懂事!怎么能给客人冷的吃呢?”一边说,一边把热洋芋递到我们手里。原来,这位婆婆姓周,我们刚进村时,她也来接了我们,因为人多,没挤到前面来摆谈,她从给我们带路的番族青年小张那里,打听到我们要到支部书记家去借宿,就急忙忙地回家专门给我们煮了一大锅洋芋送来。吃着周婆婆的洋芋,坐在阿衣嫫家温暖的火塘边,疲劳和饥饿早赶走了。
团结友好 助人为乐
支部书记周阿呷同志和她的爱人张有富,正在热情地招待我们吃饭。一位走路有点摇晃的汉族老妈妈,拄着拐杖送来了一钵豆泥。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不好,而且是冒雨送来,我们既感动又觉得不好意思收下。可是老妈妈不依,她说这是“团结豆泥”,非吃不可。
这位汉族老妈妈姓魏,大家都叫她魏奶奶,已经六十七岁了。她原来住在梨花汉族聚居区,儿女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是一个孤人。民主改革时她搬到这里来落户。成立新桥合作社后,她是社里的“五保户”。她感激地告诉我们说:“要不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周阿呷书记与番族同胞从各方面照顾,我的骨头早就打得鼓了!”怎么不是呢?新桥高级社只有魏奶奶一个汉族,她所需要的一切,全由番族社员负担。每年除了集体分给她足够的口粮,还由大家给她轮流种自留地,砍柴,担水,推磨。今年5月份,魏奶奶病了,不能起床做饭,番族社员就轮流做了好饭好菜给她送到床边,并且一口口地喂她,当她病情加重时,支部书记周阿呷和社干部,还轮流守护。魏奶奶讲完了这些动人的故事以后,眼里含着感激的泪花说:“今天端来的‘豆泥’,也是社员帮助种的,由周阿呷书记帮助推的,我只煮了一下。你们要谢,就该谢周阿呷和社员;你们不吃,就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心呵!”
火塘夜话 丰富多彩
吃完晚饭,社员们都到周阿呷的家里陪客来了。天虽然还下着雨,但来的人还是挤了一屋子。按番族的习惯,来了客本来要唱歌跳舞,因屋里太窄,只好随便摆摆龙门阵。从晚上八点钟一直玩到十二点,主人给油灯添了三次油,大家都没尽兴,要不是周阿呷同志说我们第二天还有工作,社员们真要陪着摆一个通宵。摆谈的话题又多又杂,他们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牛马生活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又从红白喜事各方面介绍了番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谈得最高兴的时候,还唱了几首番族的民歌,并且给我们讲了一个番、彝、汉自古以来都是亲兄弟的传说。
据说,在很久以前,洪水滔天,天地间只剩下兄妹二人。后来他们成了亲,生下三个儿子,长大后分家时,大儿子在平坝,安石头作界,以后成为汉族;二儿子在半山,钉木桩作界,以后成为彝族;三儿子在高山,结草作界,以后成为番族。三兄弟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魔鬼,从中挑拨是非,并把作分界标志的石头搬了、木桩拔了、结草烧了,挑拨三兄弟打冤家……刚讲到这里,人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这个魔鬼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就是汉族的地主、官僚和番族、彝族的奴隶主,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番、彝、汉三族人民哪能手拉手地成为亲兄弟呢?我们番族人民哪能回到祖国大家庭,过着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附:勤劳和善的民族——番族
番族,亦作蕃族,又叫西蕃族,是彝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分布在越西、甘洛等地,约二千三百人。
相传,番族是古“吐蕃”人的后裔。吐蕃人,是古藏族人的自称,吐蕃即今西藏地区。据说,现在的拉萨,就是唐时吐蕃的建牙之所。另外,还有一个说法:番系指外族。如清时把川、甘、云、贵等省边境之各族,编入户籍,称为番户。
据《越西厅志》记载:“西蕃,即唐吐蕃之遗。性驯,业耕种;前西山一带较多。”又载:“国朝(指清朝)川陕总督岳钟琪,疏通大道,剿抚兼用,均各纳粮应役。”《越西厅志》编于清末,而越西以前叫“卫”,清乾隆年间改为“厅”,民国初年才改为“县”。把这个情况与上面说的互相印证,番族是“吐蕃”之后,即藏族的一个分支,是比较可信的。
番族人民十分勤劳和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仿效汉族。他们居住在彝族聚居区中,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受到彝、汉族的巨大影响,但仍然保持着许多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有完整的番族语言,特殊的婚丧仪礼,别致的服饰等。《越西厅志》说:“西蕃尚勤俭,男女均劳,穿中衣、穿鞋”,又说:“男爱烟酒,女爱红线,好盐茶布帛,重牲畜。有三四分近汉俗处”。
注:文中的“西蕃”,是民主改革前后一段时间的称谓。现在,西蕃属于藏族分布在凉山的一个支系。这种情况在凉山并非只此一例。如四川凉山同云南宁浪交界处,现在已经是旅游风景民俗胜地,称“男不娶,女不嫁”的“东方女儿国”的泸沽湖,居住在属于四川管的这一边的少数民族,已经归入纳西族;而居住在云南管的那一边的少数民族,保留了原来的称谓“摩梭”,叫“摩梭人”。实际上住在泸沽湖畔的“纳西族”和“摩梭人”,原本就是一个整体,民风民俗,语言习惯,婚姻形态等等,完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