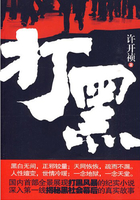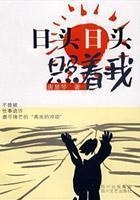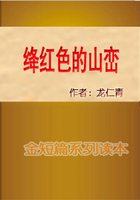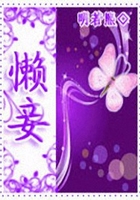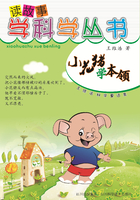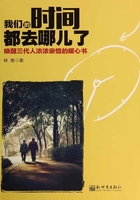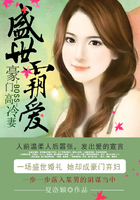不能被遗忘,旨意在创造
——梁平《汶川故事》阅读印象
薛梅
从“人的文学”的确立,再到“爱,是不能忘记的”,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标志性转折意义:作家与诗人自觉以“人性”作为审美构思的重心。“不能”二字,既强调了人性开掘中的意识形态,又达成了人道主义理性向度上的诉求。也许,梁平的诗报告《汶川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位诗人自觉立场上,不能忘记的人性之爱与理性之思。
一、灾难与记忆:
不能被遗忘,正显示了诗人梁平的一种野心。他想用诗歌的形式记录时间,感受到时间长度所产生的重量,并为历史留存记忆,为时代作证。
三年,我们看着时间经过,时间也穿越了我们。一方面时间以连绵的流逝给予我们遗忘,既然逝者不能复生,那就遗忘灾难,以此来减缓悲痛所挟裹的心灵伤害,让生者赢得更多活下去的理由。另一方面,时间的灾难瞬间所呈现的停止或打断,是改变方向的紧要点,它使时间的桌布滑过去,又打开另一张桌布,生者在灾难的废墟上重建着一切,焕然一新。可见,时间流逝所表现出的颜色的削减和改变,都是无可回避的。
然而,人类的记忆具有摆渡作用,它能赋予现今的存在以意义,也能复制和定格过往。因之,任何生命的消失以及灾难的发生,便因记忆而具有了价值。或者说,当我们不能改变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够做到的,唯有用记忆的良知来老老实实复制时间,用良知的记忆来真真切切使时间定格。让逝者永生,让生者永爱。如果说,遗忘,是活着的本能,那么,记忆,则是活下去的自觉。
这或者正是诗人梁平在诗歌创作中的自觉。梁平在为我们奉献了“时代良知”的《三十年河东》、“城市良知”的《重庆书》、“地震良知”的《默哀:为汶川地震罹难的生命》之后,在纪念“5·12”汶川大地震三周年来临之际,又倾情为我们奉献上了这部力作,“汶川地震诗报告”《汶川故事》,显然具有了一种客观面对灾难的品性与力量。
两千多行的《汶川故事》,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中浇铸着诗人血脉的跳动和奔涌,气势磅礴,悲歌慷慨中又焕发着人性的光芒、时代的养素。当“序曲”在岷的地理时空流转中,打开了一幅和谐、创造和美丽的四川画卷,生命的意义便已在无形中得以确立,历史正与时间相适应。然而,自然的破坏力量,就像突如其来的致命匕首,不留情面也不留余地,用时间的刻痕,蕴蓄且昭示人类潜在的隐患和不屈的抗争,“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灾难的瞬间刻度,让记忆从此纠结、缠绕、唤醒,诗人诚实的抒写了其时,以及其后,中国的悲痛、悲悯、悲壮:“梦断五月”不堪回首又不能遗忘的汶川,“在十三亿中国人心里,/铺开撕人心肺的长篇悼词”;“梦醒四川”废墟上的死亡阴影,在汶川人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大爱中,收获了“大地上的生机,精神与灵魂的涅槃”;“梦想成真”是灾后重建的奉献者的歌谣,“人类灾难史上,救援。赈灾。重建,/一部复杂而浩瀚的中国书,/每个章节酣畅淋漓,都是华章”;“尾声,或梦的飞翔”中,我们又看到了历史与时间相适应,“十三亿炎黄子孙的精神认同,/已经植入民族的肌体,生生不息”,“把蜀道天堑变成康庄大道”的中国的四川,“在祖国腹地大西南的方向,/——江山如此多娇。”
时间是承重的,灾难的存在便在它自己的摆渡之中,我们死去,我们又活过。《汶川故事》如是倾诉,“一万年以后,/这里生长的坚忍与顽强,/成为一种精神,成为时间的重量”。无疑,梁平的诗歌记忆,为我们带来抵制时间和遗忘的,正是心灵深处的慰藉和安妥。
不能被遗忘,同时又显示了梁平诗人的一种担当。他自觉诗人与社会的“瓜葛”,呈现出一位优秀诗人对中国文学传统中“诗史意识”的回归。
“诗史”的概念,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主要用来指杜甫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当时社会面貌、人民疾苦,以及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情怀,是对杜甫诗歌社会价值的高度评价。此后,“诗史”情结便成为历代诗人关注、记载或反映一个时期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自觉意识。“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的“诗史意识”,不仅成为诗歌批评的一个范畴,更是一种文学精神。
作为中国当代一名出色的诗人,梁平始终固守着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认为,“主旋律题材”或者“政治抒情诗”的抒写,“绝对是介入中国社会或者见证中国变化的一种方式。优秀的诗人一定要和社会有‘瓜葛’,即是要具备理解、分析、把握这个社会的能力”。这便是他灵魂中的“诗史”情怀。
面对灾难,面对心灵,诗人何为?我们毫不费力地从网上检索梁平,且不说从地震到来时,梁平第一时间呼吁国家为罹难者下半旗志哀的诗写,到什邡穿心店地震诗歌墙的选址;且不说从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四川省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协举办的《铭记》、两周年举办的《春回天府》、三周年举办的《四川开满鲜花》几个大型诗歌朗诵会,以及《瞬间与永恒》《春回天府》大型诗画册的出版发行,单是在三年时间流逝之后的今天,长诗《汶川故事》的问世,足以看到诗人梁平勇于文学担当的可贵品质。
《汶川故事》是平凡而又出类拔萃的,普通又超乎寻常的,它像所有抒写地震的诗歌一样,奉献一颗赤子之心;但它又是梁平自己的,独一的心灵镜像。一首诗,无论是抒写个体生活的私处,还是人类生存的宽度,其人生深邃处的开掘,生命精神的俯仰,皆会因诗人心灵感知的差异和观念的取舍而有所不同。诗歌担当决定了梁平诗歌的价值取向,他的《汶川故事》所承载的并非一时事件的局限,而是地震的具时事件所带来的无限心灵震波。他以形象和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最生动最具认识价值的灾难现场、领导核心、社会群体、地理面貌、民族气度,是由来已久的自然和人类的抗争与挑战,是文明进程中命运和时代的涌动与思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汶川故事》还是一部与苦难抗争的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和情感史。
二、诗体与反思:
毫无疑问,梁平是一位具有优秀素质的成熟诗人。他深知,如果只会一味地让文字具有时间复制和还原的能力,那么这种诚实就势必丧失掉一个诗人应有的诗意情怀。因此,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尝试着跳开假、大、空的“政治抒情诗”或“主旋律诗歌”(如果“政治”这个词汇,也要在与时俱进的新与变中成长,我倒是非常愿意接受“时代抒情诗”和“新抒情诗”的提法)的误区,改变“集体言说”的方式,并以诗人自己的最大限度保持诗歌应有的艺术品质。
旨意在创造,主要体现在诗人梁平的文本探索上。《汶川故事》显示了梁平渴望将新闻报道、评论、官方发言、传记、影视剧本、抒情诗与叙事诗等各种文体整合于诗歌的先锋意识。
《汶川故事》的副标题中,明确指出了本诗的诗体特征:“诗报告”。“诗报告”并不是梁平的首创,这是近年来诗人回归社会现实,回归人的普遍认同,融入时代精神,在自我真切感受之上作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重要成果。尽管概念的提出时间较短,但是文化根基却相当深远。从百年诗史的“纪实以诗鸣”的文学传统,到解放战争中元帅诗中的新闻报告内容,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本自觉,特别是张永枚反映南越入侵我国西沙群岛、我国军民英勇自卫反击的《西沙之战》,将“诗报告”这一题材广泛引入了人们的视野。此后,依然不乏这一诗歌文体的自觉探索者。他们的作品,“便是敏感的他们关注社会现实的结果,是重大社会新闻事件触动了诗人的诗思与诗情,他们将诗歌艺术与新闻报道有机融合起来,呈献给我们。”(西篱《人民的生存和天、地是歌唱的源泉,是唯一的真诗》)。
在《汶川故事》中,梁平进一步完善和锻造了“诗报告”的熔铸成分,以先锋性和创新性显示了一个成熟诗人非同凡响的整合能力。他吸取和发扬了叙事诗的审美特征,不仅特别关注诗歌结构的创设,“序诗”和“尾声”既构成了整个“诗报告”的圆融汇通的整体感,同时也营造了浓烈的情绪场和清晰的评判,中间三章则在一个时间的起始点,呈线性观照,震时、震后,过去,现在;又呈放射性扫描,拓展情感空间,个体、群体,具象、全貌。他还关注现代性内涵与古典元素、民间意蕴的并融和光合,比如:
有一个记忆叫汉旺时间。
那是北京时间、伦敦时间、纽约时间,
甚至世界上所有移动排列的时差,
一统在钟楼上那个永远的定格。
汉旺是汉王的谐音。
时间是东汉光武帝用过的时间。
时间是灵魂叩问过的时间。
一个小镇镶嵌在四川盆地的边缘,
与汶川、北川、青川有关,
与德阳、绵阳、阿坝有关,
与藏有关,与羌有关,
与四川有关,与中国有关,
与人类那场劫难有关。
——《第一章 梦断五月·5》
《汶川故事》中,仅以第二章“梦醒四川”第10节为例,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和逻辑性、事件的突出重点和对受众的温情导向,影视剧本镜头推拉式的视觉效果和共鸣感应、追光式的细节刻画和真切的对话意味,官方发言的客观判断和公信高度、自觉的身份意识和积极的家国姿态,评论的细微处见精神、宏观的梳理与概括、传记的翔实和厚重、人与事的彼此映衬和烘托,都被梁平十分巧妙的安插在诗句中,似是而非,又神形兼备,颇具文体家的素养和风范:
青川满目疮痍,
石坝乡党委书记在崇山中,
站起另一座峰峦,他是这块土地上的脊梁。
父母受伤、去世、到最后下葬,
每个消息都带给他了,
每个消息都似霹雳,搅动他五脏六腑。
没时间回家看,没有时间悲伤,
他只能在心里哭喊“孩儿不孝啊”,
只能背过身悄悄抹去泪水,
石坝废墟上所有的乱石压在心上。
灾民转移、安置,
小麦、油菜该抢收了,
水稻该插秧了,玉米该下种了……
他穿行在层叠的废墟上、田野里,
身后一个、两个,一个个村民跟上来,
跟出五月石坝农耕的一片繁忙。
已经破碎的石坝的梦,开始缝合,
每一根针线都从他笔直的腰身穿过,
穿过乱石,穿过扭曲的道路,
老百姓心里,留下一条闪光的路标。
——《第二章 梦醒四川·10》
然而,叙事、新闻报道、官方发言等题材的吸取和整合,仍然是作为诗歌的表达手段,这些最终都是要为诗歌的抒情服务,以描写抒情,以叙事抒情,以议论抒情,有悼亡的哀婉、沧海桑田的悲叹、化悲痛为力量的深切、雅歌忠诚的礼赞、敬畏的生命信仰、悲悯的人间大爱。《汶川故事》的抒情是从心灵流淌的河流,涓涓汩汩,浸润人心,自然而不失浓郁,奔放又不失内敛,完全打破此类题材中概念化的局限,不作“口号”式、“标语”式传声,也不作绝望状、冷漠状宣泄,更不作大而无当、空而无益的牢骚,一切诗句皆“感于哀乐”,随心而抒,随情而发,浇灌出的人性之花、民族之花,在汶川地震的废墟上迎风绽放。
旨意在创造,还体现在梁平诗人的理性之美。这意味着,《汶川故事》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爱,是悲悯,更重要的还是痛定之后理性的反思和超越。
一个地震,震醒了一人,还是一群人,或者一个民族的人?《汶川故事》在时隔三年后的回望和反观中,以伤情和真情、悲歌和颂歌铺陈、点染和勾画出一个五味俱全的丰富表情,诗歌的表情,给以探寻和回答。
废墟上的重建并不艰难,难的是灾难后精神的重建。诗人梁平以浩然之气,仰望人类精神的峰顶。首先,梁平思考了人及其生命的尊重。梁平在《两个层面:我们的尊重与期待——关于抗震救灾诗歌的思考》中说:“从‘5·12’到现在,所有关于灾难的人和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万众一心也罢,众志成城也罢,其存在的价值最根本的衡量尺度只有一个,就是高于一切的人及其生命。这是足以让世界仰视的光芒。”《汶川故事》紧紧围绕灾难前后的人心、人性、人情这一条主脉,以多种笔法生动而鲜活地塑造出老人、孩子、妇女、领袖、战士、幸免者、志愿者等众多形象,甚至有名有姓的平民式英雄就多达十几人,透视他们的灵魂,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人性的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诚如诗人王干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其次,梁平思考了公民社会核心价值如何有效地保持和强化。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必然产生悲悯和大爱,这是可贵的精神收获。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对灾难的追问和反思:“一部别处无法复制的大书,页码正在散落,/以怎样的方式装订成籍?/以怎样的路径让它走出遮蔽?”不仅体现了诗人真挚、成熟和经验表现上的活力,也凸现了深层次的人类意义,是那种超越“生死的泰然与淡定”、“灵魂的干净与安宁”、“精神的崇高与超越”、“坚强”和“承担”的公共意识,以及“后援建时代”、“对口支援”、“对口合作”、“工业、产业园区”、“绿色生态环境”的现实情怀,这为诗歌的纵深拓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空间和精神想象。
爱在其中,美在其中,《汶川故事》为我们守护了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密。
2011年4月9日于河北承德魁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