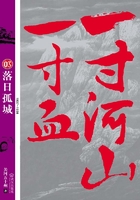雪落下来了。夜幕中不需要色调的雪粒,被缩着一团的宫灯一照,在空中就遍体鳞伤了。
该回去了。大地用来铭记意义的树枝们朝不保夕,形同言语恍惚的那书,随羊群的天色,归还给一堵墙最后老迈。
谁见过从天而降的兽,种植着眼神一茬茬开始黯然的光芒。
挂在壁上的鼓声,把衣衫的空洞放进仍在行走的姿势中。
让鸣叫回到那只娇小的鸟飞翔过的绸,让鹅黄回到春天无法再轻的枝头。
让北方回到冰雪的冬天里无法移动的北方,言语沉重的北方。
一叶戴着墨镜的舟,泊在那书遗落了页码的纸中,风中摇曳的声音,站在牛皮鼓面,行将凋零的树叶上,一波三折,在坠落的水中,淋浴那些用光影走动的鱼。
谁在一夜成名博览群书,一群逐水草而居的书,驮在白马斯文的长鬃里,要那人彻夜无言地读着。
谁在一鸣惊人遍插菊花,黄金们蜂拥而至的菊,在手指苍白的柔弱中,越渐细微。要那人用黄昏焙制出来的凉一生一世地掌握。
该回去了。天空用来普降雨露的节气,裹在树枝们凭空描绘出的祥和与静谧中。傍着最后一滴无法可走的雨,坐在红色褪尽的门槛。
所有的鼓声都藏匿在庙宇高处那风最后的清里。在天上的北方,敛尽她们雪一样与生俱来的白和言语枝繁叶茂的青花瓷中,些许仅存的缅怀。
让所有的春天,弱不禁风,收拢紫色的光芒,回到雪中生长的人用一千年的敬畏默认的那参,那品那座在鼓声中可以云开见日的山。
让所有的雪,冰封天地之间还在唯一穿行的那鼓,然后等着那些已经消失殆尽的春天,偶尔雄鹰展翅,偶尔插翅,在雪样白净的鼓里,和她们花朵般灿烂的声音一道一动不动。
他们说:
关上吧。一切的一切,就这样轻轻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