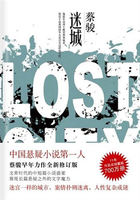可怜的沃尔特。他先是认为自己有义务让父母有经济保障,于是将他的演员和导演梦搁置一旁;之后,他爸爸刚刚用自己的死解放了他,他又和帕蒂结成一队,将自己拯救地球的雄心大志搁置一旁,跑去为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工作——这样一来,帕蒂就可以拥有她那栋漂亮的老房子,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了。这一切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发生了。他为所有让帕蒂感到激动的计划而激动,全力翻修老房子,全力帮助帕蒂对抗家人。直到多年以后,直到帕蒂开始令他失望,他才变得更为谅解爱默生家的其他人,坚持认为她是他们当中最幸运的那个,是唯一一个从遇难的爱默生号船上逃脱的人,是活下来讲述故事的那个人。他说阿比盖尔被困在一个极度荒凉的岛上(曼哈顿!)到处寻觅感情的食粮,她垄断对话的行为不过是为了努力喂饱自己的空虚,应该得到原谅。他说帕蒂应该怜悯她的弟弟妹妹——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饥渴——而不是为他们没有逃脱的力量和运气而指责他们。不过,这些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在婚后的头几年里,他对帕蒂是如此着迷,所以她不可能出任何错。那些日子多美好呀。
沃尔特本人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他的家人。到她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赢了那场比赛。在伯格伦德家的牌桌上,或许除了英俊的外表和对女人游刃有余(这张牌在他哥哥手上,他目前和年轻的第三任妻子生活在一起,后者正在努力工作养着他)之外,他拿到了几乎所有的王牌。沃尔特不仅知道罗马俱乐部,阅读艰深的严肃小说,欣赏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还会熔焊铜管接头,做细木工,从叫声猜出鸟儿的名字,并照顾生病的女人。作为家庭竞赛中的大赢家,他有余力时常回头去帮助其他人。
“我猜你现在不得不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了。”当帕蒂中断与理查德的公路之旅后,沃尔特在希宾的巴士站外对她说。他们坐在他父亲那辆维多利亚皇冠车中,两人灼热而激动的呼吸给车窗玻璃蒙上了一层雾。
“我想看看你的房间,”帕蒂说,“我想看看和你有关的一切。我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听到这番话,他不得不再次长时间地亲吻她,随后才又回到焦虑的状态。“话虽如此,”他说,“我还是不好意思带你回家。”
“别不好意思。你该去看看我家,简直就是怪胎展览。”
“也许吧,不过,我家可没那么有趣。这只会是你肮脏的铁矿带之旅。”
“那咱们走吧。我想去看看。我想和你睡在一起。”
“听上去棒极了,”沃尔特说,“不过,我估计我妈妈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
“那我想睡在靠近你的地方。然后,我想和你一起吃早餐。”
“这个倒是不难安排。”
事实上,松语汽车旅馆的景象让帕蒂冷静下来了,她开始怀疑起这趟希宾之行;投奔沃尔特时抱有的那种自足的心态被动摇了,毕竟,她在他的好朋友那里感受到的性吸引力要更强烈些。从外面看,汽车旅馆并没有那么糟糕,停车场上的车辆数目也不至让人沮丧,但是接待处后面的住宿区则确实和韦斯特切斯特相差甚远。它们让她看出了她之前不曾注意到的那个世界的优越性,她这个郊区富家女的优越性;一阵出乎意料的思乡之情向她袭来。地板上铺着海绵地垫,明显地向屋后的那条小河倾斜着。在起居兼就餐区,有个毂盖大小的锯齿状陶瓷烟灰缸,近旁放着一张长沙发,吉恩?伯格伦德平日就坐在上面,阅读钓鱼和打猎杂志,收看旅馆天线(第二天早上她才发现,天线草草地架在化粪池后面一株被斩首的松树上)能够从双子城和德卢斯的各个电视台接收到的随便什么电视节目。沃尔特和弟弟共享的那间狭小卧室位于向下倾斜的走道尽头,因靠近小河而终年潮湿。地板中央,沃尔特小时候为划出他的私人空间而贴的那道宽幅胶带留下了黏黏的印迹。他童年时代用过的东西还摆在墙边:童子军手册和奖状,全套的简写版总统传记,几册零落不全的《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小动物的骨架,一个空鱼缸,邮票、硬币收藏,以及一个接线伸出窗外的精密温度计或气压计。卧室那扇变形的门上挂着一个自制的黄色标牌:禁止吸烟,字是用红蜡笔写的,其中的N和S写得颤颤巍巍,个头却很高,显示出作者的愤怒。
“我的第一次反叛行为。”沃尔特说。
“那时你多大?”帕蒂问。
“不记得了。十岁吧。我弟弟曾患有严重的哮喘。”
外面暴雨如注。多萝西在她的房间睡觉,沃尔特和帕蒂都还处于欲望的兴奋之中。他带她去看了他爸爸之前经营的那间“休息室”,以及挂在墙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鼓眼鱼标本,还有那张他帮爸爸做的桦木吧台。直到最近,到他不得不住院前为止,吉恩每天下午还都站在这个吧台后面抽烟、喝酒,等着他的朋友们下班,来光顾他的生意。
“这就是我,”沃尔特说,“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我喜欢你是在这里长大的。”
“我不确定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接受了。”
“我喜欢,因为我是如此地仰慕你。”
“这是件好事。我猜。”他走到前台,看着一堆钥匙说,“你觉得二十一号房听起来怎么样?”
“是一间条件特别好的房吗?”
“和其他所有的房间都差不多。”
“我二十一岁。所以,完美极了。”
二十一号房里处处可见褪色磨损的物品表面,原本一早就该重新油漆或更换的,却被经年累月地用力擦洗。河流的潮气依旧明显,不过还可以忍受。床很低,标准尺寸,不是皇后床。
“如果不喜欢,你不必非得留下来,”沃尔特说着,将帕蒂的背包放在了地上,“明早我可以送你回汽车站。”
“不!这里很好。我又不是来度假的。我是来看你,帮你忙的。”
“好吧。我只是担心我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哦,那么,不要再担心了。”
“可我还是很担心。”
她让他在一张床上躺下,试着用自己的身体来让他安心。然而,很快,他的担忧就又爆发了。他坐起身,问她为什么要和理查德一起回纽约。这是一个她允许自己希望他不会问起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说,“我猜我想看看公路旅行是怎么回事。”
“嗯。”
“有些事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只能这样解释。有些事我一定要去弄弄清楚。而现在我弄清楚了,所以我来了这里。”
“你弄清楚了什么?”
“我弄清楚了我想待在哪里,和谁在一起。”
“哦,速度还真快。”
“那是个愚蠢的错误,”她说,“他总是用那样一种方式看人,我相信这你是知道的。一个人需要花点时间去弄清楚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请你不要因为这个责怪我。”
“我只是对你弄清楚的速度感到惊讶。”
她有种想哭的冲动,也终于哭了起来,而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沃尔特展现出他最擅长安慰人的那部分自我。
“他对我不好,”她含着眼泪说,“你刚好是他的反面。而我现在是如此,如此,如此地需要这个反面。你能对我好一些吗?”
“当然可以。”他边说边摸着她的头。
“我发誓,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这一字不差是她的原话,自述人满怀歉意地回忆着。
而下面的这一幕也同样让自述人记忆犹新:沃尔特猛地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推倒在床上,然后向她逼过来,重重地压在了她的两腿之间,脸上是一副令帕蒂感到全然陌生的表情。那是一种愤怒的表情,愤怒控制了他。就好像幕布突然分开,露出某种美好而男子气的东西。
“这不关你的事,”他说,“你明白吗?我爱你的一切。你的每一寸。每一寸。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你明白吗?”
“明白,”她说,“我是说,谢谢你。我多少感觉到了,不过还是很高兴听到你说出来。”
然而,他还没有说完。
“你知道我有个……有个……”他搜寻着词语,“有个问题。和理查德。我和他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不信任他。我爱他,但我不信任他。”
“哦,老天,”帕蒂说,“你绝对应该信任他。他显然也非常关心你。
他令人不可思议地保护着你。”
“并不总是这样。”
“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你知道他有多佩服你吗?”
沃尔特头向下,生气地盯着她:“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去纽约?
他又为什么和你一起待在芝加哥?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我无法理解!”
听到沃尔特说粗话,看到他似乎因他自己的愤怒而感到震惊,帕蒂又一次哭了起来。“老天,不要这样,老天,不要这样,老天,不要这样,”她说,“我在这里,不是吗?我为了你才来了这里!我们在芝加哥没发生任何事。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她将他拉近,用力抓着他的屁股。但沃尔特并没有去碰她的乳房或是把她的牛仔裤脱掉,就像理查德肯定会做的那样,相反,他站起身来,开始在二十一号房里走来走去。
“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他说,“因为,你知道的,我不傻。我有眼睛,有耳朵,我不傻。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听到他说关于理查德他并不傻,帕蒂松了一口气;但她觉得她已经想不出办法来安慰他了。她只好就那么躺在床上,听着雨水打在屋顶的声音,意识到如果她没有上理查德的车,眼前的这一幕就不会发生;意识到她活该受此惩罚。不过,她还是忍不住去想象,事情或许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发展。这一切是如此准确地预示了他们后来度过的很多个深夜的场景——沃尔特美好的愤怒被白白浪费了,而她在一旁哭泣,他惩罚她,然后又为他的惩罚道歉,说他们俩都累了,时间也很晚了,确实如此:太晚了,天都快要亮了。
“我要去洗个澡。”最终她开口道。
他坐在另一张床上,双手捂着脸。“很抱歉,”他说,“这一切真的不关你的事。”
“呃,其实,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听你不停地这样说。”
“对不起。信不信由你,但我是为了表示好意。”
“此刻,我也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他问她洗澡时需不需要帮忙,脸依旧埋在手心里。
“不用了。”她说,尽管要在保持她上了夹板、缠着绷带的膝盖露出水面的情况下洗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半小时之后,当她穿着睡衣从浴室出来时,发现沃尔特似乎一动未动。她站在他面前,俯视着他金色的鬈发和窄窄的肩膀。“听我说,沃尔特,”她说,“如果你希望我离开,我可以明早就走。可现在我要睡一会儿。你也该去睡了。”
他点点头。
“很抱歉我和理查德一起去了芝加哥。这是我的主意,不是他的。你该怪的人是我,不是他。可现在呢?你让我觉得自己很差劲。”
他又点了点头,站起身来。
“晚安吻?”她说。
他吻了她,这个可比吵架感觉好多了,如此之好,他们很快就钻进被子里,熄了灯。晨光从窗帘周围透了进来——北方的五月,天亮得很早。
“我对性基本上一无所知。”沃尔特坦白说。
“哦,这个嘛,”她说,“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尤其对沃尔特,那真是一段让他头晕目眩的时光。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女孩,原本可以跟理查德走、最终却选择了他的女孩,接着,三天后,在那家信义会医院,他和父亲之间的长期对抗也终因父亲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死亡是一位父亲所能遭受的最大失败。)那天早上,帕蒂跟着沃尔特和多萝西一起去了医院,被他们的眼泪感染,她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然后,在他们近乎沉默地开车返回汽车旅馆的路上,她觉得她已经是伯格伦德家的一员了。
多萝西回房间躺下后,在旅馆的停车场上,帕蒂看着沃尔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从停车场的一头疾冲到另一头,边跑边跳,转弯前弹跳起来,接着又跑。那是个晴朗明媚的早晨,大风从北方持续地刮过来,河岸边的松树真的在飒飒低语。疾冲了几个来回之后,沃尔特又单脚上下跳了几次,然后转身背对帕蒂,开始沿着七十三号公路向前跑,一直跑到转弯的地方,接着就不见了人影,一小时后才回来。
第二天下午,在二十一号房,光天化日,窗户开着,褪色的窗帘随风飘动,他们笑着,哭着,做着爱,那是一种沉甸甸、天真无邪的快乐,每每回首,自述人不由黯然心碎。他们哭一会儿,做一会儿爱,然后心满意足地贴着对方汗湿的身体躺在那里,聆听松树的叹息。帕蒂感觉她好像服用了某种药效永远不会消退的厉害毒品,或者好像在做一个生动无比的梦,一个不会醒来的梦,然而,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毒品,也不是梦,而是她真实的人生,一种没有过去、只有当下的人生,一种不同于她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爱情的爱情。全都是因为二十一号房!她怎么能想象到这样一间二十一号房呢?这是一个如此干净、老式的可爱房间,沃尔特又是一个如此干净、老式的可爱男人。而她正值二十一岁,在从加拿大吹来的清新的、生机勃勃的北风中,她能感受到她的二十一岁。她小小地体会到永恒的滋味。
超过四百人参加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虽然不怎么认识吉恩,这个数字也还是让帕蒂为他感到骄傲。(如果你想有个盛大的葬礼,死得早不无小补。)吉恩生前是个殷勤好客的家伙,喜欢钓鱼、打猎,喜欢和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他们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但不幸的是,他是个酒鬼,没受过什么教育,娶了一个将全部的希望和梦想以及最好的爱都寄托在自己的二儿子而非他身上的老婆。沃尔特永远都不会原谅吉恩让多萝西在汽车旅馆那么辛苦地工作,不过,在自述人看来,尽管多萝西令人难以置信地和善,但她也毫无疑问属于那种殉道者的类型。葬礼之后的招待会上,在一间信义会宴会厅,帕蒂像上速成班一样认识了沃尔特的所有家人和亲戚,那就如同一个大伙儿吃着环状面包、决心去发现任何事物光明面的节日。多萝西尚在人世的五个兄弟姐妹都来了,还有沃尔特刚被放出监狱的哥哥、他风骚标致的(第一任)老婆和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穿着军装、沉默寡言的弟弟。唯一缺席的一位重要人士,其实,是理查德。
沃尔特当然给理查德打了电话,尽管颇费周折,因为要先打去明尼阿波利斯,找到理查德那个从来都行踪不定的贝司手赫雷拉。理查德刚刚到达新泽西的霍博肯。在电话上表达了哀悼之后,他说自己把钱花光了,很抱歉没法去参加葬礼。沃尔特向他保证说这完全没有关系,然而,接连好几年,他都一直为此抱怨理查德,说他没有努力想想办法——这么说并不完全公平,因为沃尔特早就在暗中恼火他的老友,甚至不想在葬礼上看见他。不过,帕蒂可不会糊涂到去做那个挑明这点的人。
一年后,他们去纽约旅行时,帕蒂建议沃尔特去找找理查德,和他待上一个下午,但沃尔特说,最近几个月他给理查德打过两次电话,而理查德却从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帕蒂说:“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则说:“不,你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帕蒂又说:“好吧,那么他是你最好的男性朋友,你应该去找找他。”但沃尔特坚持说从来都是这样——他觉得总是他在追着理查德跑;他们之间有一种类似边缘战术的东西,一种比谁会先眨眼,先表现出需要的比赛——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套。他说理查德不是第一次玩消失这个把戏。如果他还想继续做朋友,沃尔特说,那么这一次或许该轮到他主动打个电话了。帕蒂怀疑,理查德可能还在因芝加哥小插曲而感到不安,努力不来打搅沃尔特的幸福家庭,因此,或许应该由沃尔特去找理查德,让他知道他仍然是受欢迎的,不过,她再次明智地没有去催促沃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