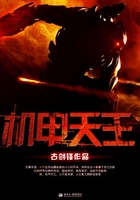他宇文烈,绝对不会任由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第二日天刚亮,任乃意便被宇文烈的两个手下抬着回到了洗衣院。此时洗衣院的军姬们都出去各司其职,偌大的洗衣院中,只有任乃意一个人趴在角落的简陋床榻上。
任乃意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像是被车轮碾过一般的疼痛难当,喉咙也像是被烈火灼烧一般的干涸。她想要起身去倒一杯水,可是身子稍稍一动,背后就感觉到撕心裂肺的彻骨疼痛。她紧紧地咬着牙齿,死死地忍着不让自己呼痛出声。
恍惚间,她感觉到一个瘦细的身影缓缓向她走来,任乃意以为是青芽,于是有些吃力地开口道:“水……”
那人听到任乃意的话,脚步微微停顿了一会儿,不一会儿才又重新进来,慢慢走到任乃意身前站定。
“被人杖刑的滋味如何?”任乃意听到来人语带讥讽的声音,费力地定睛,这才发现原来是身穿着一身艳丽美服的云自姗。
任乃意费力地扯动嘴角,轻喘着气道:“托你的福,我好得很,朱琐琐。”
朱锁锁半倚在墙边,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俯看着满身伤痕的任乃意,嘴角泛着满是嘲笑的弧度,“我说过,下一次,我一定会杀了你。”
她缓缓蹲下身子,伸手抚上任乃意侧在一旁的脸庞,“不过,你还真是好本事,不但让珏爷爱上你,连残暴好色成性的宇文烈也对你如此特别。”
任乃意懒得费精神去应酬她,索性闭上眼睛养神。
朱琐琐被她一脸平静的态度彻底地惹恼,又看到任乃意脖颈间挂着那一块黑玉,当下便伸手想要将那块黑玉扯下来。
任乃意一把抓住她的手,使出浑身所有的力气护住那块黑玉,睁开双眸直直地望着朱琐琐,“滚。”
朱琐琐一巴掌甩在任乃意的脸上,冷笑道:“你觉得,你如今还有与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她说着,手更加用力地扯着那块黑玉上的绳子,甚至将任乃意的脖子都勒出了一个个极深的勒痕,“放手!”
任乃意因为身上剧烈的疼痛已经开始觉得头晕目眩,甚至连呼气和吸气都开始觉得疼痛,可是双手却依旧下意识地紧紧握住脖子间的那块黑玉。
这一刻,她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块黑玉是宇文珏给她的,绝对不能丢!尤其是绝对不能落在面前这个女人的手里!
朱琐琐见她竟然死都不愿意放开手中的那块黑玉,心中的怒意和嫉妒也渐渐将她的理智湮没,她的脑海中不断地叫嚣着,杀了她,杀了这个女人!杀了她,宇文珏才会真正属于自己!
如此想着,朱琐琐从衣袖中取出一把匕首,对准任乃意的脖子处微弱跳动的青筋就要狠狠地割下去。
“咣当!”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朱琐琐已经瘫倒在了地上。不一会儿,洗衣院中落下了一深一红两个人影。
依旧是一身红衣的钱焕,手中拿着一块小石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抛着,他转头有些幸灾乐祸地望着表情难明的宇文珏,“啧啧,那女人被打成这样,不死也残了吧?你确定你还要她?”
宇文珏淡淡地望了他一眼,“若是她身上留下半条伤疤,那五万万两的货物我就让给轩。”
钱焕一听,顿时急了,连忙直了直身子,望着宇文珏,一脸狗腿地讨好道:“别啊……”
宇文珏眉眼轻扫过他的脸,钱焕瞬间垂头,然后不情不愿地从衣袖中取出一个药瓶,“你女人,你自己去上药去!”钱焕一脸舍不得地将药瓶递到宇文珏面前,嘴里还不忘叮嘱他道:“省着点用啊,这药可贵着呢。”
宇文珏接过药瓶,指了指瘫倒在地上的朱琐琐,“处理掉。”
钱焕咋舌,憋了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小声嘀咕道:“珏爷,为什么每次这种事都是我做?”
“别将她弄死了。”宇文珏随即又加了一句。
钱焕有些意外地转头看了他一眼,“哟,怜香惜玉啊?珏爷,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宇文珏笑着看了他一眼,“你以为我的女人,真的会这么笨中了她的计?留着她,让我女人玩。”
钱焕听了他的话,不停眨巴着一双桃花眼,一脸苦相地思考着,究竟要怎么样处理,才能将朱琐琐整得半死不活。
宇文珏则快步走到任乃意的床榻边坐下,在看到她满身触目惊心的伤痕和满头的冷汗后,顿时心疼地几乎想要立即灭了整个靖国军营。
迷迷糊糊间,任乃意感觉到背上传来一阵冰凉舒服的感觉,带着温暖的触感,一点点地拂过她背上的每一寸肌肤。原本彻骨的疼痛顿时缓解了不少,她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手依旧下意识地紧握着脖子处的那块黑玉,她甚至仿佛闻到了空气之中竟然浮起了一阵浅淡的药草香味。
看到昏睡之中的任乃意唇角渐渐泛起一个满足的弧度,宇文珏满是心疼地吻上她苍白而干涸的樱唇,将口中的温水一点点地过渡到她的嘴里,又用钱焕给他的药酒为任乃意擦拭了全身,直到确定她不会因为伤口感染而发烧之后,才转身离开了洗衣院。
他刚走出洗衣院,正好看到满脸得意的钱焕迎面走来,笑得十分得瑟地对着宇文珏道:“我为那女人找到个极好的归宿。”
宇文珏根本不关心朱琐琐的下场,他望了一眼宁王的营帐方向,开口道:“将司马佑找出来。”
钱焕撇撇嘴,有些不满地道:“珏爷,您能少差遣差遣我吗?”
宇文珏挑眉笑看了他一眼,闲闲道:“可以,我差遣轩去。”
钱焕一听,连忙道:“别,别啊!您差遣,尽管差遣,往死里差遣我。”
宇文珏浅笑开口道:“宁王有个地下的兵器库,你知道吧?”
钱焕心中开始默默为宁王哀悼,“珏爷,您又想怎么毁人家,说吧。”
宇文珏转眸望了他一眼,笑道:“只是想拿回一点原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钱焕见他一脸云淡风轻的模样,右眼皮就开始莫名其妙地狂跳,他在心中默默告诫自己,以后无论得罪天,得罪地,得罪神还是得罪佛,就是千万别得罪此时躺在洗衣院里面的那位任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