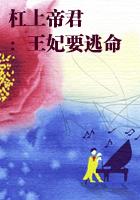而那只小白狐正是被倒栓了四爪挂在他的马背上,正徒劳的挣扎着。
那个手下过来,粗声道:“小丫头,你拦住我们作甚。”
雪雁暗骂了一声残忍,便仰脸道:“我家姑娘喜欢这只小白狐,拿十倍的银子跟你们买了这只白狐,如何。”
那手下先是一怔,旋即笑道:“这可不行,我家主子费了好多心思才抓着的,还有用。姑娘喜欢,别处买去。”
雪雁俐齿伶牙,毫不示弱:“哎,可是我们家姑娘就看上这一只了,你们卖是不卖,左右你们又不吃亏,别处再打一只就是了。”
“好刁蛮的小丫头!”另一个人不耐烦的拉出半截直刀来:“滚,滚,滚,小心爷手里的剑不长眼!”
“光天化日,难道要在百姓家门外就动粗么。”一个冷冷声音响起,并不高,却透着清傲,如碎落一地的冰棱。
所有人都愣了愣,黑衣男子终于缓缓的转过身来,墨发之下的面容绝艳惊人,正是宇文祯。
宇文祯黑黝黝的眸子透着慑人的冷芒,可是这冷芒却在触及那抹纤纤素影,慢慢暖了起来。
浅素裙裳,披着风帽,带着面纱,只见娉婷袅袅的身姿,却不见玉人芳容几何。
男子怔了片刻才沉声开口:“这位姑娘,有何见教。”
黛玉不再向前,保持着一射的距离道:“不敢当。实不相瞒,却才这只小狐误闯寒舍,殷殷有求护之意,十分可怜,小女不忍,所以才令小婢来问一声,愿以十倍之价将它买回。小婢无知,出言冲撞,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声音如涓涓流水,软风拂面,毫无羞赧造作,每一个字都轻轻楚楚,不卑不亢,轻纱下眸子,始终平静如斯,那种高贵,不属于寻常所见的贵族女子,而是飘渺于云端,遥不可及。
好像,世外的仙子?
宇文祯对这个一瞬间进入心底的想法有些意外,便眯了眯眼眸:“是我的人不懂事,粗鲁冲撞。不过,姑娘若想买这只白狐,恐怕不行,我拿它有用。”
他的声音,如漠漠玄冰,不带一丝温度。
“冒昧一问,所谓的有用,可是要取它的皮毛?”黛玉淡淡道。
“是又如何。”
“若是拿来做救命之用,倒也罢了。若只因要取其皮毛,以餍奢欲,以娱耳目,便伤它性命,岂非不仁!”
“大胆!”一个手下跳出来,怒喝道,还未说完便被宇文祯以目止住。
宇文祯目光冷峻,缓缓的开口:“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么?”声音沙哑而低沉。
“京城内外,非富即贵,这我当然知道。”黛玉眸中不无鄙夷,冷声道:“以势压人,我一弱女子尚不屑,况贵胄者乎?我要说的是,前不久,宫中贵太妃刚刚薨,宫中谕命凡有爵之家,一年之内不得筵宴,不得闻乐声,三月之内不得有屠宰腥血之事,而这个时候,贵府要杀狐取皮么?”
语气,仍是淡淡柔柔,其中的意味却是凌厉。
宇文祯不觉换了种目光打量着眼前的纤弱的女子,怎么看也不像是这么大胆的人,可是,她偏偏就是这么的言辞犀利,一番话,滴水不漏,更兼句句都点中要害——“唔,好伶俐的口齿。”
宇文祯的手忽然毫无征兆的压在佩剑上,气氛陡然紧张,风声静默间,银光肆意流泻,晃的黛玉也不禁眯了眯眼睛,而那把剑却在挑断马背上拴着白狐的绳子后滑回了剑鞘,他示意手下:“这只白狐送给这位姑娘。”
几个手下彼此相觑,却还是应声。
“多谢。”黛玉微微一颔首:“不过——是买,不是送。无功不受禄,我不喜欢欠了别人的——取银票。”
雪雁答应一声,拿出一卷银票,无论好歹,拍在那人手里,便将白狐抱了过来,放到地上。小狐狸撒开短短的四爪跑到黛玉身边,挨着蹭着,跟着黛玉回去,尾巴还晃啊晃的,憨态可掬。
宇文祯静静的望着那纤巧素衣身影没入门内,再也不见。
她,便是那位一曲琴音名扬京城,直压第一才女司徒娬儿的女子?
南府之宴,水溶便是以箫和了她的琴?
水溶受伤的那夜,便是留在了这里?
是巧合,还是……
眸中一丝异样的光芒闪过。
那个手下擎着银票,傻眼了,手足无措道:“殿下,这……”
“人家给了,就收着。”
“是,可是……”
“嗯?”
“殿下,没了那只狐狸,皇后娘娘问起这两天一夜去了哪里怎么说,回去怎么跟皇后娘娘还有十公主交代。”
“交代就是——父皇之命,不能伤生。”黑衣如鹰的男子眸中隐隐一点轻嘲,狠狠一夹马腹,拨马回转。
马长嘶一声,马蹄腾起。扬起的烟尘里,宇文祯却不由自主的回身,望了一眼那沐浴在青山秀水之间的庄园。
林氏,黛玉。
本殿,记住你了。
“魏王,见过她了?”
这句话,说是问,不若说是自语。所以一身夜行衣的暗卫只是稍稍低了低头,没有接话。
对面,宝椅上的男子坐姿带了些懒散,一身白衣覆了半张长椅,若天际铺开的云片。
书房内,灯火飘曳,俊美的面容笼在扑朔的灯影下,薄薄的菱唇微微抿着,一双若夜的瞳眸潋着寒意莫测。
魏王果然找到了那里,而且还见到了她!
他想要做什么。
水溶面无表情,修长手指不紧不慢的敲打着几案。
一场暴风骤雨已然在眉睫之间。
这一盘棋,本来并没有她。可是现在,恐怕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如果让人察觉了自己的心思,她要面对的,恐怕就更加复杂了。
“听着,继续暗中保护,不管发生什么,要保她无虞。”水溶声音一顿,眸中冷芒慑人:“不—惜—代—价!”
“是。”
暗卫应着,无声隐去。
水溶长长的吁了口气:“祁寒,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