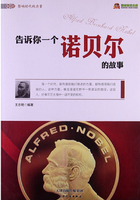其后不多久,在十六铺做瘪三的杜月笙被小东门的“大阿姐”(一个小有名气的烟花间老鸨)相中,做了一段烟花间的杂役,日常时间替妓女拉皮条,给嫖客跑腿。就在这一时期,他结交了一个臭味相投的兄弟,这就是以后成为他死党的顾嘉棠,也是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入了青帮,正式成了“在帮”的白相人。
青帮,论其源流,原是漕船水手的帮会组织。有清一代,虽然禁止民间结社,但民间的秘密结社却也一直未曾完全根绝,其中青帮算一大统系,维系着游离于乡村与城市正常治理秩序之外的大量“异常分子”。清末河工废弛,运河堵塞,政府无钱疏浚,只好发展海运,尤其是“洪杨”事起,漕运只得改成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顿失作用,原来以运河漕运为生的水手纷纷另谋出路,于是“青帮”组织离开江淮流域,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活动。其中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水陆交通方便,就成了“转业”
青帮新的立足点了。然而,“转业”谈何容易,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另一方面,原来在街上做“孤胆英雄”的地痞瘪三,也终于“找到组织”了,纷纷加入青帮。于是青帮渐渐转化成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和流氓的结合,使得青帮变了味,然而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青帮势力大涨。
民国初年以来,上海青帮中辈分最高的是“大”字辈的“老头子”(对帮中前辈的称呼),如此辈分的“老头子”加起来也就十几位,如张仁奎、高士奎、樊瑾成、袁克文、张树声、汪禹丞、步章武、徐朗西、陈其美等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很难说是“流氓头子”,如袁克文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名士”,文采风流一时无两,张树声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著名将领,徐朗西和陈其美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做了几十年的通海镇守使,官望很是不错,为人也算正派。但自从“大”字辈以下,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上海滩上诸如烟、赌、娼、盗、绑、杀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通”字辈的青帮成员在掌管。当时叫得响名号的“通”字辈有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马祥生、严九龄、季云卿、张啸林等人。
杜月笙是“通”字辈以下的“悟”字辈,按辈分得称上面这些人为爷叔。
可是,这些“通”字辈的狠硬角色,后来却全都是杜月笙帐下的左膀右臂,他们“辅佐”杜月笙,甘愿为杜月笙所用,根本顾不上什么辈分不辈分,这是杜月笙之为杜月笙的特殊之处。
与杜月笙后来的地位不相称的是,杜月笙的“老头子”(师傅)却是个街头行骗的不大不小的混混,绰号“套签子福生”(套签子是一种骗术)的陈世昌。陈世昌自己混来混去并没混出多大名堂,却因有了这“了不得”的徒弟杜月笙而得以名满上海滩。杜月笙发达后,更把他养起来,“以报师恩”。杜月笙开馆了,有了自己的“杜公馆”,每年供给陈世昌用度,他再也不用出去套签子了,而且每年过年杜月笙会请陈世昌到杜家聚赌,所得抽头全部归陈世昌,陈世昌也受之不却,洋洋得意。陈世昌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迫,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话不说,问要多少钱才能了断,陈说大洋二万五千。杜毫不在意地说:“准明天如数奉上。”结果不多会儿这两万五千大洋又败光了。陈世昌爱子心切,又包羞忍辱来求杜月笙,杜毫不犹豫又给了两万。然而,这陈世昌的儿子实在会败家,不多久,这些钱又胡花海花个精光。从此以后,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上杜家的门,活活给这个儿子气死了。
从杜月笙对陈世昌一事来看,他待人有个常人难及之处,那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对不嫌弃自己和他人出身低。凡是曾经对杜月笙有恩的,他后来都一一报答。
后来杜月笙进了黄金荣家,给黄金荣拎皮包做跟班,有次代黄金荣老婆桂生姐叉麻将赢了两千四百元大洋,桂生姐赏了他两千元。这是迄今为止杜月笙生平见到的最大一笔横财了,他如何处置这一笔意外之财?这是林桂生颇感好奇的问题。他揣着这两千大洋,找到原来在十六铺落魄时的一帮兄弟,每人几十上百个白花花的银元送了出去,他还特意找到原来当差的水果店,将原来自己弄下的亏空金额两倍补上,请这些老哥们一起下馆子海吃了几顿。
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生路的黄和祥,他后来的回报可以说惠及黄家的子孙后代了。杜月笙开祠的时候,他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正是最风光的时候,这时候黄和祥也来参加典礼。杜月笙见了,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黄和祥,一星期后到华格臬路他的公馆,有要事相商。黄和祥依约前去,杜就当场叫原来管账的杨渔笙把钥匙全部交给黄和祥,要黄立即任他的总账房,这个重要的心腹位置,黄一直做到中风而死。黄死后,这个总账房的位子,又传给了黄和祥的儿子黄国栋,由黄国栋一直做到上海解放。
杜月笙念旧。虽然他后来成了体面的“绅士”,但绝对不敢看不起像他当年一样在街头晃荡的白相人和瘪三。
当初杜月笙还混在十六铺的时候,别人总叫他“莱阳梨”,他对自己这个叫得响的诨名很是得意,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从不回绝。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少有人当面再这么叫。不过当年和他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现在向他要钱时,还是不免怀着快乐而戏谑的心态,当面向他大叫这个人人皆知的外号。常常是这样:杜月笙和几个很有身份的朋友去四马路一带妓院吃花酒,他的汽车刚一停下(杜的车牌号77777,上海滩上最风光的一个号),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候钱给得少,这些人便扯开了嗓子大叫:“莱阳梨,多给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这样才能把这些瘪三打发走。
杜月笙削水果这一绝艺一直保留着。四川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范绍增和杜月笙交情极密,当只有范绍增、杜月笙、顾嘉棠几个贴心朋友时,顾嘉棠便常常打趣杜月笙,随手拿起一只水果送到杜月笙面前,叫他削,杜月笙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没有丝毫不快的表示,似乎很是享受给人家削水果的感觉。他也取笑顾嘉棠,往往看到顾嘉棠进来,就笑着呵斥他,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了。因为顾嘉棠原来是个花匠,两人出身一般的低贱。
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家财万贯了,这种小打小闹的玩笑,多少带着点温馨的回忆,回忆当年一起度过的穷苦日子。
在杜月笙成为“海上闻人”后,杜月笙和顾嘉棠表面上是主仆关系,但他们其实是介乎兄弟和朋友之间的生死之交,两人相互依赖,彼此捧场。
在外人面前,顾总是装出对杜恭恭敬敬、十分听话十分服帖的样子,而两人私下里则无话不谈,情同鱼水。杜也绝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对顾说一句重话。据说,蒋介石对杜月笙,有时候也如同杜月笙待顾嘉棠。在正式场合和有外人在场,蒋介石绝对不苟言笑,对杜月笙这些出身底层的帮会人物少有亲昵神色,但私下里,三两个人的时候,对杜月笙则“月生哥”叫得亲热。而杜月笙呢,表面上对蒋介石奉若神明,毕恭毕敬,但背了蒋介石则对蒋也不那么恭谨了。
在十六铺,杜月笙没有积攒下任何家财,但他积累了足够的混江湖的智慧,和人人皆知的义气。
4.黄公馆是黄金荣的公馆,在上海法租界麦高包禄路钧培里(今龙门路)1号。杜公馆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216号。杜公馆的这栋豪宅,其地皮是黄金荣赠送的,地面上起了两座公馆,西边的一座属于杜月笙,东面一座属于张啸林,两座公馆一墙之隔,有门相通。
从黄公馆到杜公馆,路程不到一刻钟。但杜月笙从黄公馆走到杜公馆,却足足走了十多年。从黄公馆到杜公馆的这条路,就是杜月笙演绎旧上海传奇的大舞台。
约在辛亥前,经陈世昌介绍,由陈世昌的同辈兄弟,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乙接引,杜月笙到了当时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门下当跟班,年岁在二十岁左右,做的是“黄门小厮”。
黄金荣(1868-1953)是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远及江浙一带,在当时是有名的“大亨”,后来更成为“闻人”:上海滩的“大亨”多得很,哪怕是做“粪霸”——垄断收粪的行业——也可装模作样当“大亨”,但“闻人”则又比“大亨”分量要重得多了,沪上“闻人”,寥寥可数。
他因破了几桩轰动一时的大案,深为法租界当局看重,职务一升再升,担任法租界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二十多年,直到六十大寿之后,才退下来做顾问。凭着自己在租界的声势,他经营戏院、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当时,法租界内的游艺场、戏院,如大世界、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差不多都有他插手其中,或者就是他开办的。他是个横跨黑白两道的人物,正式身份是法租界的督察长,但实际上还是上海滩上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之一。
杜月笙初进黄公馆,每走一步都踏着小心。他最初只能混在佣人中间,干些杂务,住在与灶披间相连的小房间里,进出都得走后门。生活虽然安定些,用不着每天为找吃的发愁,但他也不可能每天睡懒觉了。他既然下了从黄公馆出头的决心,这些暂时的拘束倒也能忍受。他收敛起原来的种种浪荡习惯,处处谨慎,事事巴结,尤其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和个人嗜好,然后投其所好,交结各色人等。用后来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很快,他就赢得了黄公馆上上下下的好感,众人都说他“蛮灵格”(上海方言,即很灵活,很不错之意)。一个“浪子”,一辈子浪荡无行,这不会有人吃惊,但忽然之间居然换了个人似的变得行事谨慎、稳重而缜密,这就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杜月笙口齿虽不大伶俐,但察言观色非常老道,加上身手敏捷,动作利落,给黄金荣提皮包久了,渐渐地深得黄金荣的赏识,开始接近黄金荣权力圈子的核心了。他不仅得到黄金荣的看重,更得到黄公馆的半边天,黄金荣老婆桂生姐的青眼。旧上海人都知道,黄公馆虽然姓黄,但真正的主人是桂生姐。桂生姐叫林桂生,本人虽长得矮小,却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是所谓“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臂上跑得起马”的人物,在很多事情上,黄金荣对桂生姐一般都是言听计从的。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黄公馆内迷信,老板娘病了,便要选派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守护。这是桩苦差事,日夜不能离身,事事需要经心,没人愿干,所谓久病床头无孝子,就是这个道理。但杜月笙担起了这个担子,并竭尽全力把它干好了。旁人陪伴老板娘,也只不过是守在身边不离开,随叫随到。杜月笙却不然,他不但牢牢地守着,而且全神贯注,耳到、眼到、手到、脚到、心到。只要老板娘有什么需要,口一张他就跑去替她办好,甚至还不用开口,就想到了,为此真正做到了“衣不解带,食不甘味”。
久而久之,桂生姐对杜月笙刮目相看,既看重他手脚伶俐,又感于他的一片忠心,决心好生拉他一把。
如果光是靠伺候人来收买人心,那么杜月笙终其一生恐怕也不过是个大管家式的人物,不会有什么自立门户的机会了。然而,通过处理一桩意外的“抢土”事件,杜月笙显露出其不同一般的魄力和机智,从此在黄公馆成为独当一面的人。
何谓“抢土”?这就得说起旧上海最著名的一桩“生意”了。
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势力建立在一个巨大的三角贸易循环上——英国从中国购进丝茶等物品,印度从英国购进纱布等产品,中国则从印度购进鸦片。其中鸦片在英国这个奴隶和毒品贩子的帝国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凭着它,英国一方面可以平衡在与中国贸易中产生的巨额逆差,另一方面其高额利润有力支持着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机构和军队(印度殖民地是鸦片的最大输出地和得益者)以及本土鼓吹殖民扩张的势力,所以英国为此不惜发动两次对华战争。经过两次鸦片战争,鸦片成了世界各列强公开合法向中国出口的大宗物品。同样,鸦片始终是现代上海这座巨大城市运转的润滑剂。“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上海崛起于鸦片贸易。”(魏斐德语)1843年11月,怡和洋行——英国在华最大的洋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其中就有一个买办专门负责洋行的鸦片贸易。到1860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两年,上海已经占到鸦片贸易额的60%,鸦片在上海几乎可以代替真金白银成为“硬通货”,商人们可以拿着鸦片购货。二十世纪初的中国,16.8%的人口吸毒,超过一半的人口,其生活、生计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
上海不仅是鸦片贸易的转口站,也是鸦片最大的最终消费地,它的租界、华界散布着上千家鸦片烟馆。这些鸦片烟馆从郑洽记、郭裕记和李伟记三家批发商进货,而这三家批发商则从沙逊、新沙逊、台维和新康四家洋行购进来自印度和波斯的鸦片。这是鸦片正常贸易的时代。1906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决心十年内在中国逐渐禁绝鸦片,英国同意从1908年起十年内,将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逐渐从61900箱削减到零。英国之所以此时“同意”放弃以两次战争获得的特权,有几个考虑因素。
首先,此时鸦片已经在英国对华贸易中不再具有十九世纪时那般重要地位,中国本土产出的鸦片(产自云贵川、陕甘与东北、外蒙等地)已经超过了进口鸦片(这可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进口替代战略”产品),进入民国以后,日本更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向中国出口毒品的国家。
其次,外国在华传教士向来大力反对列强向中国输入毒品。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份报刊像在华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那样,连续几十年持续不断地谴责鸦片和鸦片贸易,也没有任何其他刊物像《万国公报》那样详尽地控诉了鸦片对中国及其人民带来的伤害。他们认为,中国人吸食鸦片是灵魂的堕落,不利于他们皈依上帝。这种来自宗教与伦理的国际压力进入二十世纪后越来越大,使得英国“尖头鳗”(gentleman)也不得不圆滑了其脑袋。
此外,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认识禁烟的重要性。中国全国性的禁烟,先后有1906年到1917年清末民初的禁烟(这正是袁世凯执政的时候),以及从1935年开始民国政府推行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这时蒋介石的权力基本巩固了)。
后来由于北洋军阀的勒种,和日本侵略者对华推行毒品政策(日本人在华北大肆走私毒品),才使这两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功败垂成,烟毒不久又死灰复燃。外国租界是鸦片贸易的基地,中国政府以此为理由之一要求收回租界,而为了挡回中国政府收回利权的要求,列强也不得不做出姿态表示禁烟,以表明他们的治理能力高于中国人,作为维护外国在华特权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