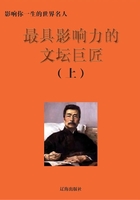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当时,在“左”倾分子那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已变成他们用以排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帮派性,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则被用来对待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凌辱、迫害以至虐杀,无所不用其极。二元矛盾运行的结果,是手段绞杀了理想,人性无法不听命于帮派性。瞿秋白不能摆脱二元矛盾的藩篱,即使走到生命尽头他也无法忘情于理想与手段、人性与党性的互相调和,于是就有了隐含厚重二元结构的《多余的话》。王明一伙把持的临时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正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痛斥过蒋介石及其同伙,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以前不畏刑讯,讴歌苏区;在写《多余的话》以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全部斗争实践中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一个环节。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专门写了《告别》一章,一再向同志们亲切地告别;一再说他写的是“最后的话”,这都只能说明他决心舍生赴死,而没有“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消极动摇,叛变投敌”的意图。《多余的话》的基本内容是自我解剖,这个行动说明他并非绝望地“消极等死”。他最后英勇牺牲同他就义前夕总结自己一生,这两者之间没有无法解释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善于思索,追求真理这一特点和优点,瞿秋白一直保持到他被捕就义;临终之际,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更加强烈突出了。《多余的话》和《未成稿目录》,是他在这时高度思索的结晶。《未成稿目录》,是他准备写的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的题目。除了总名为《痕迹》的三十篇自传性作品外,还有十篇《读者言》,包括对《阿Q正传》、《水浒》、《野叟曝言》等今古文学作品的研究札记。他如果不牺牲得那么早,以他的天赋,勤奋和多思,他写出的作品,应该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写要多得多。这四十个题目,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它未免是“多余”的。我却以为,这一纸目录,凝结着多么美好的向往,多么执著的追求呵!在临危的严峻时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计,而是以日以时计,他却抱定宗旨,排除俗念,开列了那么长长的准备著述的目录。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可以被理解为“多余”的吗?
击破劝降阴谋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京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做说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加派王傲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陈建中,当年二十四五岁,中等个,瘦长脸,说一口陕西话。他原是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1933年被捕立即叛变。他与另一个叛徒、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杜蘅(杜甘棠)在西安“表演”两个月,中共在西安及陕西的党团地下组织,多被破坏。中统特务机关以陈建中“表现突出”,于1934年初将其调往南京,派他到宪兵司令部对被捕中共人员进行“说服”(即策反)工作,又在中统南京“实验区”协同敌特对中共地下机关进行“侦破”工作。不久,即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专门负责“指导”对西北苏区的“特情工作和检查工作”,并在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中讲授《说服工作》。但是,陈建中毕竟是新近“转变”的中共叛徒,匹马单枪对付瞿秋白,论才学、阅历、身份都嫌大大不足。所以,陈立夫随后又增派了中统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傲夫。
王傲夫,又名王书生,王杰夫。此人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五六岁。北平燕大毕业后曾经研究过一段宗教哲学。在商震军中以清洗进步人士深得陈立夫的青睐,先后充当中统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王杰夫出马,陈建中就成了他的助手。
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中共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陈途经福州、厦门时,又拉上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同行,于6月13日或14日抵达长汀。
在与瞿秋白谈话前,王杰夫等人商定了一个劝降的方案,据朱培璜后来交待: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干部中的叛徒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证(如顾顺章)来对他进行“攻心”。王杰夫傲慢地对这一群特务说:“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作成功的例子很多。他(指瞿秋白)很顽固,很坚决,动摇不了。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认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好好干,作出成绩给他们看!”
谈话,进行了多次。除了王、陈、钱、朱四人,国民党军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先启等也在场。
一张长方形的桌子,瞿秋白坐在一端,几个特务围拢着,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他。王杰夫戴着一副金丝架的眼镜,一对细小的眼珠紧紧地盯着瞿秋白,又极力装出一副斯文的姿态,细声细气地对瞿秋白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的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坚定地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戚友代劳。”
王杰夫说:“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译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
瞿秋白打断了他的话说:
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瞿秋白软中带硬,把王杰夫顶了回去。王杰夫这时有点恼火,然而还是假惺惺地对瞿秋白说:“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到同你谈了好几天,你无动于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