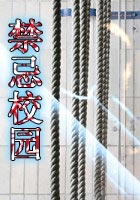在前面膜翅目昆虫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蜇针的蜇入点,帮我们解开了这个秘密。可是问题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还差得远呢。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暂时把昆虫刚刚告诉我们的事儿放到一边,开始想一下节腹泥蜂的问题吧。问题就是:节腹泥蜂是如何在地下的一个蜂房里储存足够的猎物,然后在上面产卵,使新生的幼虫吃这些食物的。
为幼虫供应食物的问题,乍一看似乎很简单,可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其实是困难重重的。比如,我们人类打猎是靠猎枪,捕到的猎物总是鲜血淋漓、伤痕累累的。膜翅目昆虫对猎物比人类要挑剔无数倍,它要求猎物完好无损,保持好的形状和色泽,薄膜没有破裂,更没有裂开的伤口和恐怖丑陋的死相。它的猎物也果然像活昆虫一样新鲜,蝶翅上精细的彩色鳞片一片不少,可那翅膀如果我们的手指轻轻一碰,就会使上面的彩色花纹坏掉、脱落。想想看吧,即使是昆虫已经死了,已经成了死尸一具,要做到这一点也很难啊!用脚踩死一只昆虫,人人都能做到,可是要把昆虫干净利落地杀死又丝毫看不出任何伤痕,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一只生命力顽强的小动物,即使头被砍下来,也会扑腾一阵子,可是假如在不弄坏它身体的前提下把它杀死,怕是人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也只有实验昆虫学家才会想到用麻痹的手段。但是即使采用最基本的方法,用苯或二氧化硫的蒸气来麻痹,也不一定成功。因为在中毒的情况下,昆虫挣扎的时间反而会太长,挣扎得太久,它的蝶翅就会失去光彩。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更强烈的方法,比如让浸着氰化钾的纸带慢慢地散发出氢氰酸,或者更好一些也可以使用硫化碳的蒸气,这种化学物质对捕猎昆虫的人没有伤害。
可见,即使节腹泥蜂将它的猎物变成了一具真正的尸体,而我们要想杀死一只昆虫,并达到节腹泥蜂在很短时间、很灵活的动作下就达到的效果,也要利用一系列的化学手段才能办到!
一具尸体!可这根本不是幼虫的日常食物,因为幼虫只吃鲜肉,如果它的野味有哪怕一点点臭味,它都会感到恶心,无法忍受。幼虫需要的是一点也没有腐烂的鲜肉,变味就是腐烂的开始。可是,不能把活蹦乱跳的猎物贮藏在蜂房里,就像我们的船上和列车上要为旅客提供新鲜食物一样,是不能把牲畜养在船里的。把娇嫩的卵产在活的猎物中间会有什么后果?幼虫如此娇弱,轻轻一碰都有可能害死它,如果它整整几个星期都处于那些挥舞着带铁刺的长腿的鞘翅目昆虫中间会怎么样?膜翅目幼虫需要的是既像死亡时一样安静又像有生命时一样新鲜的内脏,这似乎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面对这样的食物难题,即使人类拥有最广博的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验昆虫学家也会承认束手无策。而节腹泥蜂的食橱告诉我们,这一切对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假设有一所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科学院,设想在一次大会上,像弗卢朗、玛让迪、贝尔纳这样一些人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做到食物长时间一动不动,同时又长时间不腐烂变质,人们头一个想法,最自然、最简单的想法,那就是食物罐头。人们会提出使用防腐液,就像著名的朗德学者在它的吉丁问题上所设想的那样;人们会设想,膜翅目昆虫的毒液具有卓绝的杀菌防腐效力,但这些奇特的效力还有待证明。用不知为何物的防腐液来代替不知如何进行的鲜肉保存,这也许就是这个学者会议的结论,就像朗德博物学家所做的结论一样。
如果人们强调并明确指出,幼虫需要的不是罐头,因为罐头肉没有鲜肉那种可以颤动的特性,它们要的是一种尽管已了无生机却仍然活着的猎物,那么这个学者会议就会认定它是采用了麻痹的办法。“没错,就是这办法!必须把昆虫麻痹,必须使它既不能活动又没有死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合适而精准的某个或某些部位上动手,损坏、折断昆虫的神经器官。
即使这个办法可以,那么如果让一个对深奥的解剖学知之甚少的人做,也未必能成功。能使昆虫麻痹却不会让它死掉的神经器官是如何排列的呢?首先,这神经器官在哪里?当然是从头部开始排布下来的,就像高级动物的脑子和脊髓一样。“这简直大错特错,”我们的同行们会这么说,“昆虫就像是一个翻转过来的动物,它用背部走路,也就是说,它的脊髓不是在背部,而是在腹部,顺着肺和肚子分列排布。
所以神经器官在它的腹部,要麻痹昆虫只能在那里动手。”
这个困难解决了,又一个更严重的困难出现了。对于解剖学家来说,他手握解剖刀,想插到哪里就插到哪里,即使遇到障碍,他也能排除。可膜翅目昆虫没有选择的余地,它的猎物鞘翅目昆虫披挂着坚硬的甲胄,它的手术刀就是纤细而脆弱的蜇针,甲胄是完全能够抵挡这个武器的。因此,它的手术刀只有几个可供选择的部位,就是那些只覆盖着一层薄膜的关节,那些薄膜是毫无抵抗力的。但是,蜇针虽然能刺进猎物的肢体关节,却完全达不到目的,因为蜇到这些部位,最多就是局部麻醉,无法使它全身麻醉进而抑制它的全部运动器官。
如果有可能的话,膜翅目昆虫需要的是一蜇致命,使对方立刻失去活动能力,不作长久的挣扎,可是这样对它自己会有致命危害;它也不能连续蜇好几下,因为蜇的次数太多,就会危及猎物的性命。因为它的神经中枢是运动官能的枢纽,神经就是从那儿分布到各个运动器官上去的,所以它一定要刺在神经中枢上。可是,这个神经中枢形成了很多的核或神经节,幼虫的神经节较多,成虫的较少,这些神经节分布于腹部的中轴线上,彼此距离不等,被神经髓质的双重饰带串联成了一个念珠串。在所有已发育完全的昆虫身上,胸部神经节也就是支配翅膀和腿部运动的神经节,共有三个。捕猎者需要刺的就是这些点,用某种方式摧毁这些点的动作,这样猎物也就无法存活了。
膜翅目昆虫的蜇针如此软弱,以至于它能蜇入的只有两个地方:
一处是猎物的颈与前胸之间的关节;另一处是猎物的前胸和胸部其余部位之间的关节,也就是第一对腿和第二对腿之间的关节。颈关节不太合适,它离腿根附近的支配腿部活动的神经节太远。因此,它能刺入的部位就只剩一处了,并且只有这一处。有着高深学识的克劳德 · 贝尔纳等人在法兰西科学院阐述这个问题时,就是这么说的。膜翅目昆虫蜇针的刺入点就在位于腹部中线上的第一对腿和第二对腿之间。那么昆虫是得到怎样高明的指引而知道这个问题的呢?
在众多部位中选择一个最脆弱刺入的部位,只有熟知昆虫解剖学结构的生理学家才能做到。可是,只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膜翅目昆虫还要克服一个更大的困难,然而它竟然做到了,它那超群绝伦的本领真是令人震惊。我们说过,发育完全的昆虫的运动器官是由三处神经节支配的,它们通常是彼此分隔的,尽管也有聚在一处的情况,但十分罕见。不仅如此,这些中心节各自独立地支配着相应部位的运动,所以从立即麻痹的效果来说,如果一个中心点受损,只会导致它所支配的相应的肢体部位瘫痪,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神经节,更不会使受其他神经节所支配的肢体瘫痪。如果用蜇针一个接一个地攻击这三个逐渐靠后的运动中枢,而且只通过第一对腿和第二对腿之间的那一个关节点,似乎是办不到的。因为蜇针很短,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难把针刺入。是的,某些鞘翅目昆虫胸部的三个神经节靠得很近,可还有些鞘翅目昆虫的最后两个神经节是完全联结、粘连、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些神经节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集中,所引起的运动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和谐,同时,也就更易于受到攻击。
而这样的猎物正是节腹泥蜂所需要的。这些鞘翅目昆虫的运动神经中枢挨得太近了,几乎挤到了一起,甚至黏成了一团,最终牢不可分,所以只要一针刺入就能使它立即瘫痪;即使需要多刺几下,所要刺的神经节也都是聚集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完全集中在蜇针的针尖下面了。
问题的关键是,哪些鞘翅目昆虫容易被刺瘫呢?克劳德 · 贝尔纳关于生命和器官的杰出理论只是泛泛而谈,已经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无法引导我们辨别这些昆虫。我向每一个有可能读过相关资料的生理学家请教,如果他不去查找资料,他是否能说出哪些鞘翅目昆虫的神经节点是集中在一起的呢?即使查找资料,他能否立即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呢?现在我们所涉猎的已经是专家们详尽研究的细节了,我们已经离开了大多数人走的大路,走上只有少数人熟悉的小路上来了。
相关资料,我在 E. 布朗夏尔先生《关于鞘翅目昆虫的神经系统》的杰作中找到了。我在该书中看到,符合神经器官集中这种特性的昆虫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金龟子。但是它不是节腹泥蜂的猎物,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金龟子都体形较大,节腹泥蜂无法向它们展开进攻,也搬不动;加上许多金龟子都以粪便为生,而膜翅目昆虫十分爱洁净,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到粪便里寻找金龟子的。另外,阎虫科昆虫也是属于运动神经中枢靠得比较近的,但是它们也十分肮脏,寄生在臭气熏天的死尸中,所以也应弃而不谈。至于棘胫小蠢,个子又太小了,所以最后只剩下吉丁和象虫是符合条件的。
在这个漆黑一片的疑团中,忽然现出了一缕光线,实在太令人惊喜了!在无数鞘翅目昆虫中,节腹泥蜂可以捕猎的似乎只有象虫和吉丁这两类,它们每一个条件都十分吻合。挑剔的狩猎者讨厌恶臭和污秽的环境,而它们正生活在远离恶臭和污秽的地方;它们种类繁多,形态千差万别,体态与捕猎者差不多大,捕猎者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与其他鞘翅目昆虫相比,它们支配腿和翅膀运动的神经中枢集中在一处,对膜翅目昆虫来说能够一刺即中。象虫胸部的三个神经节紧挨在一起,后两个神经节几乎融为一体了。在这相同的部位,吉丁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神经节混成一团,又离第一个神经节很近。节腹泥蜂以鞘翅目昆虫为食物是早已得到证实的,同时,有 8 种节腹泥蜂是从不捕捉别的野味,只捕猎吉丁和象虫的!所以,各种节腹泥蜂的洞穴里堆放着的猎物,虽然表面看毫无相似之处,其实在内部结构上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它们的神经器官都是集中在一处的。
即使拥有再广博的知识,也不能作出比这更高明的选择了,虽然这种选择的背后困难重重,但都被灵活巧妙地战胜了,以至于人们不由地思考起来:自己是否被一己之见蒙骗了?是不是先人的理论概念掩藏了事实的真相?是不是原本自己在异想天开却用生花的妙笔把幻想出来的东西写得跟真的一样?一个科学成果只有在经过各种方式的反复实验和证实后,才能真正确立。所以,让我们通过实验来证实节腹泥蜂生理学手术的真实性吧!如果能用人工的方法得到一只昆虫,使它像被膜翅目昆虫的蜇针刺过一样,一动不动并长时间保持着鲜活的状态;如果用节腹泥蜂捕捉到的鞘翅目昆虫,或者用别的神经节也十分集中的鞘翅目昆虫,都能制造出这种奇迹,而用神经节彼此独立分开的鞘翅目昆虫却办不到,那么无论取证有多难,我们都会承认,膜翅目昆虫在其本能的无意识的支配下,确实显示出了卓越的科学本领。好吧,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是怎样的。
动手术的办法十分简单:用一根针,如果要更合适些就用一支锋利的金属笔尖,在笔尖上蘸一小滴腐蚀性液体,然后轻轻刺入昆虫的第一对腿与前胸的连接点上,把液体注入它前胸的运动神经中心。我使用的液体是氨水,别的液体只要具有同样强而有力的作用也可以。
金笔尖上的氨水好像一小滴墨水一样。我把笔刺进去以后,出现了不同的效果,而这完全是由昆虫的胸部神经节是彼此靠近还是彼此隔开所决定的。对于胸部神经节彼此靠近的昆虫,我所用的实验对象是金龟子科昆虫,即圣甲虫和宽颈金龟子;吉丁科昆虫棕色吉丁;还有象虫,尤其是那些我亲眼看到捕猎者所追捕的方喙象。对于胸部神经节彼此隔开的昆虫,我选择的试验对象是步甲科昆虫,分别是小红夜蛾、步甲、强步甲、心步甲等;天牛科昆虫,包括楔天牛、沟胫天牛;还有杨树叶甲科昆虫,主要是琵琶甲、盗虻。
在金龟子、吉丁和象虫身上,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致命的药滴刚碰到神经中枢,昆虫戛然而止了任何行动,并且没有抽搐一下。这种颇具毁灭性的后果产生得如此神速,甚至比节腹泥蜂的蜇刺都要快。
没有什么比顽强有力的圣甲虫突然一动不动更令人惊异的了。蘸着氨水的有毒的金属笔尖在这方面与膜翅目昆虫蜇针的作用相似。被人工戳刺的金龟子、吉丁和象虫不只是一动不动了,还在三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内都像被蜇针刺过一样,所有的关节都能弯曲,内脏也十分新鲜。在开始的几天,这些昆虫仍能像活着时一样正常排便,在电流的刺激下会动起来。总之,它们的表现跟被节腹泥蜂谋杀的鞘翅目昆虫的表现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被节腹泥蜂蜇刺的猎物所产生的状态,与用氨水故意破坏昆虫的胸部神经中枢所造成的状态完全相同。可是,因为不能把昆虫保存得完好无损的原因归于氨水,所以必须抛弃任何注射防腐剂的想法,而应当承认,昆虫虽然一动不动,却并没有真正死去,它还有一线生机,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各个器官仍像活着时一样新鲜,然后才逐渐腐化直至最后腐烂。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氨水只能麻痹昆虫的腿部,这时,液体的毒性并没有蔓延得很远,昆虫的触角还能轻微地动,甚至在注射了氨水一个多月后,只要轻轻碰碰它,昆虫也还会迅速地把触角缩回去,这显然证明了在没有活力的躯体上,生命还没有消失。被节腹泥蜂蜇伤的象虫,也常常有触角抖动的情况。
注射氨水能使金龟子、象虫和吉丁立即终止运动,可是并不是都能使它们昏迷休克。如果刺入得太深,或者注入的氨水滴毒性太强,昆虫就会当即死掉,两三天后,就只剩下一具散发着臭气的尸体了。相反,如果刺得太浅,昆虫在昏迷了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还会苏醒过来,还会恢复某些运动功能。就连那个掠夺者有时也会像人一样出错,因为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只被膜翅目掘地虫蜇过的猎物又活了过来。我们在下面即将讲到黄翅飞蝗泥蜂的故事。它的洞里堆放着中了它的毒针的小蟋蟀。我取出了 3 只可怜的蟋蟀,它们的肌肉十分松弛,种种迹象都表明它们已经死了,其实它还活着。
我把这些蟋蟀放在一个瓶子里,好好地保存起来,在大约 3 个星期内,它们都从未动过。后来,有两只发霉了,而第 3 只的某些部位,比如它的触角和嘴巴的某些部位则逐渐恢复了活力,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第一对腿又能运动了。既然灵巧的膜翅目昆虫也偶尔会出错,使它的猎物死而复生,我们又怎能要求笨拙的人类所做的实验永远万无一失呢?
在第二类鞘翅目昆虫中,也就是胸部神经节彼此隔开的昆虫身上,氨水所产生的效果则完全不同。步甲科昆虫似乎最不容易受到伤害。一只粗壮的圣甲虫被刺一针后,会立即无法动弹,可如果是个头比它小的步甲科昆虫受到这一刺,也顶多会引起一阵剧烈而无规则的抽搐。然后,它会慢慢平静下来,休息几小时后,又恢复了正常的运动功能,就像从来也没受过什么刺激似的。即使对同一只昆虫再做二次、三次或四次实验,结果也还是一样,直到它伤得太重而真正死掉了;因为不久它就干瘪、腐烂了。
氨水在杨树叶甲和天牛的身上产生的效果最明显。只在它们体内注了一小滴腐蚀性液体,它们就立刻一动不动了,抽搐了几下后好像就彻底死了。但是像金龟子、象虫和吉丁的那种持续很久的麻醉状态,在它们身上只是暂时的,到了第二天它们就又能活动了,而且比原来更有活力;只有当氨水的分量足够大时,才会使它们彻底不能动弹,可是这时候昆虫已经真正死亡了,因为它的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能使神经节彼此接近的鞘翅目昆虫持久麻醉的办法,在神经节彼此隔开的鞘翅目昆虫身上却毫无效果,对于后一类昆虫来说,麻醉只是暂时现象,到第二天就会完全消失。
论证已经够清楚的了。捕捉鞘翅目昆虫的节腹泥蜂在选择猎物时所应用的理论,只有知识最渊博的生理学家和技术最高超的解剖学家才能领悟出来。不能说这只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因为这样的一致已经不是用一句偶然性所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