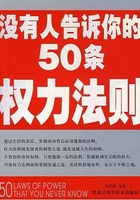《西方的没落》,作者:斯宾格勒。
这是一本西方人写的让大多数西方人倍感失落的书,很“哲学”,但并不乏味。
《当心村上春树》,作者:(日)内田树。
内田说要“用身体阅读村上”。书中以咖啡、酒吧、女人和玄而又玄的对白,去和“假如鸡蛋与石头相撞,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村上春树较劲,有趣,好玩,娱乐价值大于思考意义。
前两天,刚刚和宏甲兄(作家王宏甲)以及师学军为村上春树调侃过。他们俩是坚决要站在村上春树一方的,也就是和那些撞石头或撞墙的鸡蛋们,坚定地站在一起。我说,那也要看看鸡蛋想要干嘛,一律以“强弱”作为是非正邪的判断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恐怕也很“后道德”。他们骂我是机会主义者。
声明一点:本人也是“鸡蛋”队伍里的一员,也绝不喜欢那些恃强凌弱的“石头”!
《特蕾莎修女》,作者:(美)克鲁卡斯。
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不仅仅因为她几十年坚持为贫困者募捐服务,更重要的,是她那颗平等博爱的心灵,充满对人世的精神关怀,引领人们不断升华自己的精神品质,号召人们尽可能多地担当社会公义。她所有的努力,都旨在“让贫困的人有尊严地活着”。她以自己博大的爱,很好地消解了上世纪人们对康德的怀疑,让人们重新认识康德的“人是美与崇高的最后根源(康德《判断力批判》)”所具有的理性魅力。
§§§2.曾经风雅
《曾经风雅》,作者:张昌华。
读完后,自会有一种“唯大英雄方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唏嘘感慨,会想起李叔同崇尚老子的“能婴儿乎”,为明心志而改名“李婴”的率性与笃行。李叔同因为亲近佛典,深谙因缘,故而能够性情本色,敢于迥异时流,为无数后辈仰慕。然仰慕可,践行则难。世俗生活,既厌烦,也难舍呀!
而我却由“风雅”联想起黄炎培的妙语:“哭不出笑不出的在那里挣扎着”。
这,也许就是《蜗居》生活的非典型世相,无奈窘迫中,依然可以“努力”风雅。
§§§3.湖南人是天下人的胆
《湖南人是天下人的胆》。
说起湖南,湖南是我很喜欢的地方,为什么喜欢,很难说清。也许因为“破天荒”典出湖南,湘军,湘女,湘菜,湘绣,名扬海外;也许因为潇湘多情、岳麓内敛、马王堆深沉,八百里洞庭气吞山河;也许因为湖南人综合了南北特质,既有南方人的理性思维,又兼得北方人的性情豪迈,文学史学,思想哲学,样样居先;文胆武将,骚人墨客,土匪政要,个个不凡。真个是雄踞中南,横行天下!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大话一番“天下人的胆”,狂吹一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
感觉很牛吧?去读读吧。
《中国不高兴》,读起来很过瘾。过瘾之后,有认同,有共识,也有些许耿介。书中的一些主张,我很赞同,尤其赞同少些解构,多些建构。但是,解构往往是建构的前提,不能一味把解构者都认定为汉奸误国,大肆剿杀。
我不敢苟同的,是书中的某种“态度”或“情绪”。
分析“中国”这般庞然大物,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作者驾驭材料的功夫不错,观点也多有切中。但是,一面批评“精英”们以高等华人自居,傲慢浅薄,把西方垃圾学问贩卖回中国,祸国殃民,一面自己也以同样的傲慢姿态,指指点点,出言不逊,尖酸刻薄,并不讲究“普罗”的厚道宽容,学者的理性严谨,精英的优雅风度。看不出他们与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的王小波及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之间,有什么更大区别。
如果说,钱钟书是拿着放大镜去找中国和中国人的丑陋,那么,也有人恰恰相反。我曾戏言王宏甲是殚精竭虑、满怀虔诚地拿着显微镜去寻觅去挖掘国家干部的闪光之处。艰难寻觅中,偶有发现,必如获珍宝,欣喜若狂。他的口头语常常是:“看看,我们还有这么好的干部!”
“要珍惜好人啊。”当然,略加反思,不难体察出其中的些许无奈和深重悲哀。
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寻找丑陋,还是寻找“隐忧”,他们大都向往朗朗乾坤,向往普世之光,都是太爱这个国家和民族,太希望中国健康强大而活力四射了!只是,他们的观察视角和话语方式不同而已。
近些年,各种主张、主义横生,各种风潮、思潮泛滥,搅得周天轮番寒热。云里雾里,我们难以确认自己和自己国家的真实定位。一会儿,是“中国强大论”,说我们已经荣登列强三甲,军事排名世界第二,经济名列世界前十,至于金融领域,则说我们是美国的大股东,云云。言下之意,我们俨然是美国的老板,美国是我们的长工,拯救美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肩上。一会儿,又是“中国经济崩溃论”,说我们是新一轮西方列强经济瓜分的砧板之鱼,西方不但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当今的资源悉数掠夺,就是子孙万代的活命资源,也被提前透支殆尽,今后,我们除了当西方的加工厂,靠廉价出卖劳动力苟活,别无出路。“新左派”怀念毛泽东时代,理由是即使穷,也要傲骨铮铮,堂堂大国,腰杆笔挺,不受窝囊气,而且均贫富,等身份,苦乐同当,颇有水泊梁山的痛快豪气,不似眼下这般的折腾百姓,败家卖国,以至于两极分化日甚一日,贫富悬殊愈演愈烈,同为地球人,冰炭两重天。
“激进派”则认为,这个国家,败得不够刺激,卖得不够大胆,当务之急是要全速开足马力,赶上西方的过山车,挤进“核心圈,共同体”,就可以手执牛耳,参与分成,主宰(至少是部分主宰)世界了。
而《中国不高兴》告诉我们,这些学说统统混蛋透顶,忽悠百姓,忽悠当政,靠贩卖西方思想垃圾来干预中国未来走向,把中国引向混沌,简直罪大恶极。
在这一部分的表述中,他们“愤懑”得忘记了自己刚刚咒骂别人“愤懑”的话,泼妇骂街式的精彩话语,在书中随处可见。
比如:“当年他(指王朔)鼓吹‘我是流氓我怕谁’下的蛋,如今孵出了‘真流氓(指郭敬明)’。对比之下,原来自己也只是‘伪小人’、‘打折流氓’。”
再比如:说钱钟书“只是个戴着镣铐跳舞的才子”,“津津乐道于小世界的鸡飞狗跳”,为了卖弄学问“没完没了的连类比喻,跟爱打扮的娘们一天换八套衣服没什么两样”。
至于那些新闻眼式的标题:《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极为跳跃抢眼。骂完王朔骂郭敬明,鄙夷罢钱钟书讽刺王小波,最后捎带上王蒙。意到笔随,潇洒无比。
好一锅乱炖!
我不是说不该、不能批评,甚至我以为有些批评极有见地,但是,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作者既然说别人以“愤懑”代替理性,以谩骂代替批评,自己却也落此俗套,“镜像”比照,为之尤甚,总不免有些街头帮闲打罗圈的意味。我以为,分析批评,还是应该以客观理性为要,至少,要有起码的尊重。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肃本清源,才是正道;从源头解决问题,方为根本。
学术也好,理论也罢,都不过是源流之中的“流”,是本末之中的“末”,既非源也非本,何至遭此围歼?文人学人的各色主义,如市场叫卖,王婆卖瓜式的忽悠,本属正常,不让叫卖,反而是市场之病态。问题的根本在于,买不买账,由拿银子的人说了算。往大处说,一个国家,是自己做主,还是听信忽悠,决定因素不在于忽悠者。不管谁在忽悠,怎样忽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决策能力和水准如何。假如决策层缺乏正确判断,轻信忽悠,并跟着忽东忽西地“调度”,那就“后果很严重”。更有甚者,这严重的后果,还要大家跟着扛,这巨大的代价,还要全民“学费公摊”,然后,先知先觉者一边马后放炮,一边鞭打“忽悠”。实在搞不清楚,到底是被忽悠者智障低能,还是忽悠者太过神性魅力,果真能魅惑天下?
权力好恶,权力导向,权力话语,决定着国家大的发展方向和全民族的价值选择,关系着国计民生。如此大政、大作、大手笔,取决于某种文化自觉,更取决于特定的利益本位,绝不是“形而上”的忽悠们力所能及的事。
“楚王爱细腰,宫娥皆饿死”的典故,大概都还记得吧?骂宫娥可以,要是规劝规劝楚王,使他不要那么审美病态,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