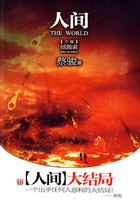一连阴了几天,到底是下雪了。雪不大,是细细的雪粒子,纷纷落落的,还没有到地面就化了。大街上湿漉漉的。汽车鸣着喇叭,脾气很大的样子。人们呢,急匆匆地赶路,偶尔抬头望一望天,皱着眉头,自言自语,这雪下得——也不知道是在批评,还是在赞美。可是无论如何,簌簌的雪粒子落下来,给这一冬无雪的城市带来一些新鲜的躁动。毕竟,快要过年了。这点小雪,来得倒是时候。过大年,怎么能没有雪呢。这是芳村人的话。也不知道,这会子,芳村下雪了没有。芳村的雪,那才叫雪。纷纷扬扬的,真的是白鹅毛一般。整个村庄都被这大雪催眠了,还有树木,田野,河套,果园。大红的春联,窗花,灯笼,彩,衬了白皑皑的雪,真是好看。小让很记得,那一年,她刚嫁到芳村。也是大雪。她坐在炕头上,看石宽在地下忙个不停。炉子烧得旺旺的。金红的火苗,勾着淡蓝的边,突突地跳跃着,舔着壶底。水壶吱吱响着,白色的水蒸气不断冒出来。花生在炉口周围排着队,偶尔发出轻微的爆裂声。还有红枣,弥漫着微甜的焦香。大雪天,又是新人,她用不着出门。石宽也不出门,在家守着她。人们都说,石宽是个媳妇迷。石宽也不恼,嘿嘿傻笑。她却臊了。赶石宽出去,却总不成。少不得反倒又被他乘机欺负了。雪粒子落下来,落在她发烫的脸上,凉沁沁的。她也不去擦一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陈年旧事,她以为早都忘记了。如今,在北京,在这个雪纷纷的清晨,倒都又想起来了。
甄姐迟到了一会,进门就抱怨这坏天气。抱怨了一会儿,看小让不大热心,就把话题换了。小让听她说起年底单位发奖金的事。三六九等,那是肯定的。年年如此。甄姐又抱怨了一会儿头儿。说这个冯社长,也不是等闲人物。才几年,把报社整治得,火炭一般。一个字,红。那一句话怎么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小让说噢,可不。甄姐压低嗓门说,听说,今年动静挺大。小让知道她说的是竞聘的事,正不知道怎么开口,看见甄姐朝她使了个眼色,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司机小马从旁走过。甄姐笑眯眯地说,今天领银子,下刀子也得来啊,这点儿雪!甄姐说这点儿雪算什么!
午休的时候,小让收到老隋的短信。老隋在短信里东拉西扯,顾左右而言他。老隋说,吃饭了吗?在做什么?老隋说,郁闷。争来斗去的,没意思。老隋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呢?老隋说,牢笼。一只鸟困在牢笼里,什么感受你知道吗,小让? 老隋说,人生有很多时候,不得已。老隋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小让把这些短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有的话,她看不懂。老隋这个人,就这毛病。酸文假醋的。小让没有回复。
下午到财务室领奖金。年终奖。前面有两个人排队。桃花眼坐在办公桌后面,沙拉沙拉地点钞票,一面腾出一张嘴来,跟旁边的男同事调笑。看上去,桃花眼总有三十多岁了吧,是那种很丰腴的女人。一双眼睛,水波荡漾。老隋是什么时候溺在里面的呢?房间里到处都是盆栽,绿森森的,树林一般。桃花眼那火红的披肩,仿佛一簇火苗,把整个树林都灼烧了。空调很热。小让感觉手掌心里湿漉漉地出了汗。
火车站乱糟糟的。快过年了,外面的人们辛苦了一年,都急着往家赶。小让拉着拉杆箱,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费了半天劲,总算在候车室找到一个立脚的地方。她给石宽发了一条短信,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石宽读过高中,石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小让不知道。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