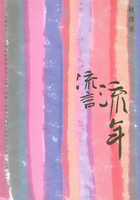周末,父亲照常地回家。我和哥哥受母亲的委派,在村口迎他。夕阳在天边慢慢融化了,绯红的霞光一片热烈,简直就要燃烧起来了。远处的树啊庄稼啊都被染上一层薄薄的金红。远远地,有一个黑点渐渐移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是父亲。我们欢呼起来。暮色一点一点笼罩下来,黄昏降临了。我们跟在父亲身旁,雀跃着,回家。淡紫色的炊烟在树梢上缠绕,同向晚的天色融在一起,很快就模糊了。至今,我老是想起那样的场景。黄昏,我们同父亲回家。家里,有温暖的灯光,可口的饭菜,还有,忙碌的母亲,她似乎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永远在等。
一家人静静地吃饭。父亲和母亲,照常说说闲话。我和哥哥,为了什么争执起来,打着嘴仗,手里的筷子也成了兵器,说着说着就纠缠在一起。父亲呵斥着我们,骂我们不懂事。你们两个,能不能让你娘少操些心?我们都住了口,默默地吃饭。母亲却忽然扭过头去,我惊讶地发现,她的眼里,分明有泪光。父亲不说话。他的半边脸隐在灯影里,灯光跳跃,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那一天,晚上,我半夜里醒来,听见母亲低低的啜泣,压抑地,却汹涌,仿佛从很深的地方,一点点升上来。父亲也例外地没有了鼾声。夜色空明,我想挣扎着睁开眼睛,然而,一不小心,又一脚跌入夜和梦的深渊。我实在是太困了。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父亲和母亲,或许正在经历着一生当中最致命的一场危机。他们在人前若无其事,尤其是,在我和哥哥面前,几乎从来没有流露过什么。然而,可以想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正在经受着怎样的海浪,潮汐,以及飓风。他们站在岁月的风口处,听任那些袭击降临,一次又一次。当然,平日里,他们也吃饭,睡觉。逢红白喜事,一起出礼。他们端正,平和,像天下大多数夫妇一样,昵近,亲厚,也淡然, 也家常。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欲言又止的话,不待开口,全都心领神会了。人们见了,非常诧异了。当然,这里面,也有隐隐的失望和释然。因笑道,怎么样——我早说过的——
对这件事,母亲一直保持沉默。她没有像大多数女人一样,找上那个狐狸精的门,撒泼,示威,直唾到她的脸上,出净胸中的那一口恶气。在家里,也没有跟父亲闹。母亲照常把家里家外收拾得清清爽爽,然后,把自己打扮整齐,等父亲回家。我记得,母亲甚至托人买了雪花膏。在那个年代,在芳村,雪花膏简直是天大的奢侈。一种精巧的小瓶子里,盛了如玉如脂的东西。我曾经趁母亲不注意,偷偷地尝试过,那一种香气,芬芳馥郁,令人想起所有跟美好有关的一切。后来,只要想到爱情,我总是想起多年前的那一种香气,穿越时光的尘埃,它扑面而来,让人莫名的心疼,黯然神伤。
四婶子,几乎再也不来我家串门了。不是万不得已,总是绕开我家的门口,宁愿多走一段冤枉路。有时候,在街上遇见,也是赶忙把眼睛转向别处,只作没有看见了。有一回,是个傍晚吧,我们几个孩子捉迷藏,绕来绕去,我看见一个麦秸垛。在乡间,到处都是这样的麦秸垛。麦秸垛已经被人掏走一块,留下一个窝,正可以容身。经了一天的日晒,麦秸垛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夹杂着麦子的香味,热烈,干燥,烘烘的,把人紧紧包围。小伙伴的声音由远而近,看到了,早看到你了——妮妮——我躲在麦秸垛里,一颗心怦怦直跳,紧张,不安,还有模模糊糊的兴奋,我的心简直要蹦出来了。忽然,我听见一阵脚步声,很轻,但是很急。在麦秸垛前面,停住了。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一定是三三,他识破我了。可是,却迟迟没有动静。许久,一个女人说,天,黑了。是四婶子。这个时候,四婶子是来抽麦秸吧。可不是,天都黑了。父亲!竟然是父亲!我记得,下午,母亲派父亲去姥姥家了。姥姥家在邻村。这个时候,父亲,和四婶子,在这麦秸垛后面,他们要做什么呢?我支起耳朵,却再也听不见什么。沉默。沉默之外,还是沉默。然而,在这黏稠的沉默里,却分明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它潮湿,危险,也妩媚,也疯狂,像林间有毒的蘑菇,在雨夜里潜滋暗长。也不知过了多久,脚步声,一前一后,渐渐地远了,远了,再也听不见了。我躲在麦秸垛里,一动不动。心头忽然涌上一种莫名的忧伤,还有迷茫。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暮色越来越浓了,四下里一片寂静。一个孩子,她无知,懵懂,仿佛一只小兽,尘世的风霜,还没有来得及在她身上留下痕迹。然而,在那一天,苍茫的暮色中,她却生平第一次,识破了一桩秘密。这是真的。父亲和四婶子,几乎是沉默的,可即便是片言只语,也能够使一些隐秘一泻千里。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那一年,我只是个孩子,五岁。那一年,我什么都不懂。
想来,那一天,一定是个周末。我回到家的时候,夜色已经把芳村淹没了。屋子里,灯光明亮,一家人坐在桌前,桌上,是热腾腾的饭菜。看见我回来,父亲微笑了,说,来,吃饭了。母亲骂道,又去哪里疯了,看这一身的土。我坐在灯影里,静静地吃饭。父亲和母亲,偶尔说上两句。哥哥呢,始终不怎么开口。我忘了说了,从小,哥哥就是一个寡言的人。然而,长大以后,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他忽然就变了。变得——怎么说——甚而有些油嘴滑舌了。他风趣,灵活,会说很多俏皮话。跟他相熟的人,谁不知道他那张嘴呢。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哥哥一直是沉默的。我无论如何努力,都听不见他的声音。当然,我们总有吵架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不算。父亲和母亲说着话,不知说到了什么,父亲先自笑起来。我疑惑地看了一眼他的脸,平静,坦然,笑的时候,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鱼尾纹。英俊倒还是英俊的。也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到了父亲的不平常。他在掩饰。那些从容后面,全是惊慌。他微笑着,有些艰难,有些吃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慢慢地喝了一口汤,强自镇定。母亲也笑着。她正把一筷子菜夹到父亲碗里。我停下来,看着父亲,忽然跑到他的身后,把一根麦秸屑从他的头发上择下来。父亲惊诧地看着饭桌上的麦秸屑,它无辜地躺在那里,细,而且小,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我分明感觉到父亲刹那间的震颤。我是说,父亲的内心,剧烈地摇晃了一下。灯光也倏忽间亮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一根麦秸屑,衬了乌沉沉的饭桌,变得是那么的触目。那一刻,似乎一切都昭然若揭了。母亲抬眼看了一下电灯,咕哝道,这电压,不稳。一只蛾子在灯前跌跌撞撞,显得既悲壮,也让人感到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