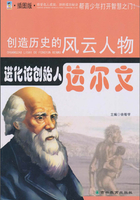人们先都愣了一下,稍停,台下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并有人高呼:“欢迎邢司令归来!”“欢迎邢司令领导我们抗战!”“消灭日本狗强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口号声中邢仁甫情绪大振:“可是有些人不欢迎我回来,他们说我是‘边区的毒瘤’,是革命队伍里的‘蠹虫’,污蔑我,攻击我,不欢迎我回来。什么人攻击我?什么人怕我回来?”他说到这里将拳头挥起来高声说:“只有敌人!”这时,全场又一片愕然,台上台下都鸦雀无声。人们惊讶司令员的讲话,不知他这样说的意思。这时周贯五给他端来一茶缸水放下,对他小声说:“老邢,别激动,注意场合、分寸。”
邢仁甫喝了一口水,好像清醒了一些,委婉地说了一句:“只有敌人不愿意我回来,我回来就是打击敌人的。”又接着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统一战线形成,美英法俄和世界爱好平的人们都是团结一致,攥成一个拳头,打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是股强大的抗击力量,必然能战胜日本***。”
讲到这里他还想多讲些,但是激动的情绪使他不知再讲些什么了,“行了,让大家知道我回来了就行了。”想到这里,他又提高了声音说:“乡亲们,同志们,都行动起来,在山东分局的领导下积极地投入到抗战斗争中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没有讲“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心想:“哼!就凭你们?”讲完后,他转身时看了李启华一眼便回到了座位。李启华则泰然地坐在那里,并没有理会他。台下又响起了持续的口号声。
大会后,周贯五陷入了沉思,他敏锐地听出了会上那微妙的不和谐并为之忧虑。
会上出现的情况,别人不了解,他却很清楚。邢仁甫和边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原来就很紧张。这在以枪杆子为中心的时期,部队自主性大,许多事情都不同地方商量,原也难免。边区党组织长期没有正式书记,经常是宣传委员李启华或者是组织委员张晔代理书记,这更使邢仁甫不把地方组织放在眼里,更何况他俩都是“外乡人”呢。他往往是大权独揽,盛气凌人,有事从不和他们商量,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军队和地方党是两层皮,两方面往往欠缺沟通。对于邢仁甫的专横跋扈,独断专行,李启华就直斥之为军阀主义。
为此,周贯五没有少做工作。常常是主动地同地方组织说明情况,然后再回过头来提醒邢仁甫。他知道边区党委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这件事同他打过招呼。向上级反映情况是地方组织的权利,他怎好干涉。后来黄骅来了,情况完全改观。可见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责任在军队方面。
本来以为邢仁甫经过党校学习,思想觉悟应有所提高,对自己原来的毛病应有所觉察、改正哪怕是收敛呢,实则不然。前不久分局党委和师部就他回边区的事来征求意见时,自己同边区党委的同志都议论过,认为一要看大节,二要相信这些毛病他经过学习应该好转,所以表态同意他回来。现在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看来自己这个政委还要同邢仁甫同志多谈谈。然而一想到这里,自己也是憷头。以前这类事情跟他谈得还少吗?可是他仍然我行我素,他把我也没有放在眼里,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开大会时,黄骅负责警戒和保卫,他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军情。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这样的集会原不宜组织,但为了表示对司令员和巡视团的欢迎,也为了激发在敌人“扫荡”中受到重大损失的军民的革命情绪,鼓舞他们的抗战热情,仍然组织了这样的大会。黄骅为此付出了巨大精力。派出了侦察员、岗哨,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安排了警戒部队,随时可以迎击可能进犯的敌人。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全部疏散完毕后,他来到周贯五这里。一推门见他正在叹气,便说道:“哎,大政委,大白天的,又叹什么气呢?”说着自己倒了一碗水坐了下来。
“咳。”周贯五又叹了一口气,然后把邢司令同地方党和政府的团结问题说了,介绍了其前因后果,并讲了自己的忧虑。
黄骅听了,好一会儿没有做声。
“老黄,你说该怎么办?”周贯五看着黄骅,有些无奈地问道。
“以前你们两个之间呢?”黄骅喝完水,点起了一锅烟抽了起来,烟草味立即弥漫了全屋。
“咳,怎么说呢?这里本来就有个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倒是一直注意这件事,不过经常是迁就。很多事就是他自己做主干了,先斩后奏,弄得你也没有办法。就说他擅自离开边区这件事,那以前我已经调走了,为了坚持边区的斗争,又把我调回来,让我和他共同坚守这块阵地。可是他,擅自离岗,不仅不向上级请示,就是连我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带着部分干部就走了。”提起邢仁甫,周贯五也是一肚子委屈和埋怨。
“老周,你是政委呀。这我可要批评你了。部队和党的关系,也就是枪杆子和党的关系,这是个原则问题,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有过多次阐述。这样的问题,怎么能迁就呢?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不可以拿到桌面上来,不拿到党的会议上来呢?事情就怕迁就,一次迁就两次迁就,久而久之,就会酿成大错。有什么问题还是在党的会议上大家摊开来解决。如果谁有缺点错误,其他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嘛!”
“邢仁甫同志是司令员,是边区最高军事长官。他有缺点,咱们作为他的同志就应该帮助他。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关乎到全局。我建议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在党的会议上解决。”
“另外,向上级赶紧打报告,给边区配置书记。这样长期缺位不是个办法;再说,再来个人也好缓冲矛盾。正好巡视团也在这里,给他们说说情况,让他们也向分局反映一下。总之咱们的人手还是缺。”
“我有机会也找邢仁甫同志谈谈,我想,大家都是同志,只要是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心中都有这个大的目标,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你说呢?”黄骅还真的给周贯五出了主意。
“哎呀,老黄啊,你还真是政委出身,连我这个现任政委也得佩服你,可是也得看对象啊!好吧,找个机会,咱们把有些事都拿到会上来共同解决,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唉,现在咱们部队和地方要是一个班子就好了。要真是能大家坐在一起把问题摊开解决就好了。确实,都是革命同志,有一个共同目标,什么都好办。老黄,你干过多年政委,在这方面你还得真给我搭把手。”周贯五经过黄骅一说,心中豁然开朗起来。
刚回来的那天,邢仁甫回到边区一下马就直接到司令部,洗了把脸就对周贯五和黄骅说,立即开会把边区的情况都沟通一下。周贯五说:“老邢,你真是个急性子,先把住处安顿好,休息一下,至少吃完饭再说嘛。”
邢仁甫立即说:“不,政委,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憋坏了,做梦都想立即回到边区来,同你们一起战斗。出去两年多许多情况都生疏了。你们都说说,介绍一下情况,我好马上开展工作,再说陆成道同志还有其他同志更是两眼一抹黑,路上就问了我许多,也是急于了解情况。刚才在船上时我还有些晕,现在一到家,一见了你们,什么事都没了。安排住处还用咱当司令的老爷们儿去管吗?哈哈哈。”
因为欢迎邢仁甫,大多数领导都在这里,到会的人还比较齐全,既然新到的司令坚持开会就开吧,也是个小型的欢迎会。参加会议的有周贯五、邢仁甫、黄骅、陆成道以及几个在场的分军区司令和团长,巡视团的全体同志参加,屋里坐不开又移至院中。周贯五说:“邢司令急于了解情况,咱们就都说说吧,给邢司令汇报一下工作,一会儿吃午饭就在这里了。一边吃一边说。邢司令真是工作第一呀。”
邢仁甫雷厉风行的做派深为黄骅赞许,心想,在鲁西时还看不出来,这一经过学习回来立即就是两个样,党校也是个炼炉啊。他首先把当前情势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汇报。这都是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在心里装着呢,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本来,邢仁甫一见到黄骅还有些见到老上级的局蹐,在船上见面时,看到黄骅的热情谦虚,完全没有以老上级自居的情态,就也释然了。现在听他这样一丝不苟地给自己汇报工作,心中不由也是一种滋味,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就在黄骅汇报结束时,他颇为赞叹地说:“黄骅同志自来边区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很突出。我在师部时就听说了。”顿了一下接着又讲:“黄副司令员,很有水平,这一段时间也很劳累。我刚一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又黑又瘦,显见辛劳。黄副司令辛苦了。以后不要这样拼命了,我和陆成道同志也来了,还有其他同志呢,以后你要多注意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啊,哈哈哈……”
这时,警卫员又来催促吃饭了,“饭已经热了两回了,吃完饭再开吧。”
此时邢仁甫精神振作,说:“别来啰唆!咱们‘灭此朝食’,开完会再吃,怎么样?”全场一片赞同声。本来周贯五还想说吃完饭接着开,一见邢仁甫如此说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又继续下去。
邢仁甫一边听一边记录,有的地方还几次问询,一直到听完所有的汇报。所有人都为他的认真和干练所折服。都汇报完了太阳已经偏西,他并没有理会,最后说:“为了尽快掌握情况,我还要下去走走。这几天的工作还是由政委和黄骅副司令员具体安排,别打乱正常工作。”
本来这次会议给了黄骅很好的印象:“邢司令是个精明能干,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但是,第二天,司令员在欢迎大会上的表现却给了他非常糟糕的印象,不过也只是想:“这样不分地点场合,没有分寸地讲话,实在有失身份。”此时,他听了周贯五的介绍,不由也产生了许多焦虑,甚至心急如焚。他产生了和司令员谈心的想法。
这一天,黄骅同陆成道谈完了反“扫荡”有关工作之后就去找邢仁甫,想商量一下下一步反“扫荡”的事。到指挥部一看不在,一问,值班参谋说他到军分区去检查工作了,骑马走的,警卫员跟着呢;再问去哪个军分区了,却说不知道;又问什么时候回来,又答不知道。黄骅不满地批评了那个参谋一句,“你为什么不问清楚?”心想,老邢这是去哪里了呢?司令员出去应该告诉其他领导同志一声,这要是有急事该怎么办?又想道,只带了几个警卫员出去,肯定是不会走太远,那应该是去三军分区了。
邢仁甫一回来看到家乡辽阔的土地和在这块土地上兢兢业业、不辍劳作的人们,既有熟稔亲切之情,又有陌生隔离之感,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情绪。心中想道:我这才出去两年多就这样,再长些时间那将如何?决定回来是对的,什么时候也不能没有根据地。革命需要根据地,个人又何尝不需要呢?没有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任你干什么都不行,谁看得上你呀!
他接过警卫员给他的缰绳,一纵身便骑了上去。两腿一夹,那马就颠起了小步,警卫员也立即纵马跟了上来。
他果然去了第三军分区。三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是他当初起事时的老部下,也是盟兄弟。上一次他派邢朝兴和孙长江从鲁南回来活动,组织人给分局和师部写信,要邢仁甫回边区的事,杨铮侯是很卖了一把子力气的。今天,邢仁甫通知了几个人到他那里集合。
通知的人有:军区后勤部长潘特、军区卫生部长刘永生、军区作战股长解玉山,还有行政委员会秘书长邢朝兴。这一天上午都陆陆续续到了。杨铮侯是东道主,自然是尽地主之谊。
几个人见邢仁甫进来,立即都立正敬礼,邢仁甫还礼后笑着让大家坐下。接着就开宗明义,说:“战事纷乱,许久没有和兄弟们一起坐下来聊聊了。其他人是同志,咱们是亲人,今天得多聊聊。之所以到铮侯这里来,是因为这里安静些,省得人多眼杂的。都说说情况吧。”
一看到场的人都是自家兄弟,就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潘特说:“大哥,你回来了,太好了,可把兄弟们盼死了。那天大会上,你第一句话一说,‘我邢仁甫回来了!’我听了那个痛快,就像三伏天喝了井水一样!我是满腔激动,热血沸腾。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回来了,我们都扬眉吐气。”
解玉山也抢着说:“邢司令,大哥!我就觉得咱们在一块儿干痛快,大块儿吃肉大碗喝酒,痛快呀。这一年多,鬼子扫荡,连粮食都紧张,就是有了机会和条件了,那个南蛮子黄骅也不让好好吃一顿,他妈的,那个别扭!”
刘永生接上说:“大哥,也不知怎的,你回来当司令,我们听着挨骂都舒服,听着他们那啰里啰唆的,一见就烦。”
邢仁甫只是微笑着听,并不接茬,好像不愿意听又愿意听。邢朝兴看了一下邢仁甫的脸色,他明白邢仁甫今天召集这个聚会的意思,咧咧嘴角说道:“诸位,司令回来了,是要吐吐苦水,可是当下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边区变化这么大,我大叔出去了两年,现在回来当司令了,真正能听他老人家的还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真正是咱们自己的人?咱们这几位大小都有个帽翅,都管着一摊,可是手中握着兵权的有几个?就杨铮侯二哥一个是分区司令,手中还只掌握些地方武装,主力团一个也没有。要是有什么事,光杆司令怎么行?”
经邢朝兴这么一说,几个人都有些傻眼了,都看了看邢仁甫,邢仁甫仍没有说话,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情,但是,后来又好像是深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解玉山又看了看邢仁甫,说:“秘书长说得对,没有实权不行。军队里面就是统兵!手里没有能统的兵,当什么也白说。我在司令部里当作战股长,一个小股长,凡是领导说的都得听,可这是表面,到了关键时刻,听谁的不听谁的,那可是最重要的。”
杨铮侯沉了一会儿,也说:“是啊,大哥刚回来,虽说是情况并不陌生,但是这两年来变化很大,对于现下边区的情况,特别是各支部队的情况并不完全熟悉。各个县的县大队、独立大队都是新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那几个主力团,一时恐怕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手里。这里关键是谁是领导人。领导人是咱的,部队就是咱的。”接着,他分析了三个主力团、回民支队、警卫营、海上特务团、以及各个县大队等的情况。
邢仁甫没有说话,但他听得很仔细。一会儿他插话问:“主力团先不去说他,我是司令,我当司令就得听我的。我领着他去打日本人,他敢不上去?慢一点儿老子也毙了他!刚才玉山说得对,看这支队伍是谁的,不是说光看谁当头,那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到了关键时刻听谁的。就说你们吧,到什么时候我说了你们不听?咱们都是铁哥们。为什么说‘打虎亲兄弟,战场父子兵’?就是这个道理。拿上枪杆子这玩意儿,就是提着脑袋瓜子!不是闹着玩的。”
邢仁甫一说话,全场都静静地听着,都眼睁睁地看着他。邢仁甫说完了又问了一句:“刘震寰、王连芳这两个人怎么样?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怎么听说过这俩人。”
杨铮侯回答说:“都是回子,革命很坚决,可是脾气倔得很,不好说话。这两年他们发展很快,打了不少仗,那南蛮子们没少夸他们,跟他们很近乎的,恐怕不好说。”
邢仁甫有些不快,又问:“陈二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