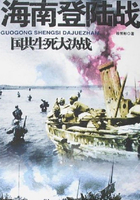小孩子们最盼过年,过节、过年可以吃饺子、穿新衣裳、扎红灯笼、放鞭炮、逛庙会……拜年的来来往往挺热闹。
我盼过年是可以休息几天,过新年了,我就可以不到蒲阳河边拾小木片、小树枝了,也不用纺线或做针线活儿了。可以高高兴兴地和小伙伴们玩几天,踢毽子、打旦儿等。那时候老百姓对旧历年可重视了,从腊月初八这天开始,早早起来,把难煮软的豇豆、黄豆、青豆、绿豆和红枣洗净倒入锅里煮软了,再下小米、稷米,慢火把粥煮熟了,叫腊八粥。先用大盆盛出一盆来,锅里剩下当天早上吃的。盛出的一盆在此后八天每天早晨做的熟白粥里,挖一勺子腊八粥放进去一块吃,到第八天吃完为止。
中午饭要吃腊八饺子,不知道是什么风俗。也问过母亲,她回答说:谁知道为什么?还不是找个理由吃顿饺子。
正月(阴历一月)里,锅台上不能见白,所以这一月不能吃烙饼:一是怕扬撒在锅台上薄面,二是说正月吃烙饼就烙住运了(命运不好)。
整个正月里都要在锅里放上两块渣饼子或是年糕,说是压锅底的,其他的风俗也很多。比如说:一鸡、二鸭、猫三、狗四、五羊、六马、七人、八谷、九菜、十果。意思是说新年的头十天,哪天天气好、阳光明媚,哪种动物或者植物的收获就好,一鸡是说大年初一天气好就收鸡,即鸡的成活率高、生蛋多;天气若不好,鸡的收获不会好,就少养或不养。初八天气好,象征丰收,那天还不让姑娘、媳妇、老娘儿们做针线活儿,说这天做针线活儿会扎谷心,谷心都扎死就没有好收成了。我也不知真假,妈说:“管他扎不扎谷心,叫人们歇一天是真的!”妈妈不太相信迷信,思想比较开通。她说:“烧香磕头是给活人看的,也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我小的时候因为天冷冻得流鼻涕,就用棉袄袖头抹一下。一上冬穿着妈妈拆洗干净的旧棉袄,到腊月天最冷的时候,妈怕我手冷,冻裂手背,就给我在棉袄袖上绷上一对窝袖,比原来的棉袄袖长三寸,能把手背盖上,拾柴火时就暖和一些,干活碍事时可以把它挽起来,冷了捋下来,很方便。由于干活儿、擦鼻涕、擦汗,这袖头一冬下来像铁打的一样光亮亮的。过年了,妈把袖头拆下来洗干净,翻新一下,再绷到旧棉袄袖子上就过年了。
十三百家年饭有一年过年,大伯母家的三媳妇从北京回家看婆婆,也来我们家看我妈,送了我一条手绢和一块绿颜色的香皂。我不知道什么叫手绢,也从来没有用过,拿它当宝贝,放在我妈衣柜上的箱子里,从来没舍得用过。经过了八年抗战,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每年破五(初五)这天家家户户放鞭炮,叫“崩穷”,传说初五放鞭炮能把穷气崩跑。我们家穷买不起鞭炮,所以穷气老跟着我们。有一年,二哥打扫院子,捡到一个没放响的小红炮,因为捻短窝在里头,二哥用小棍把炮捻拨弄得能看见了。知道里头有火药,就用个豆粒大小的香头点着了,搁在炮上,赶紧站到一旁,等香火烧到炮捻上时只听“嘭”的一声响,又清脆又好听,我高兴极了,拍手笑着:“这下可把穷气崩跑了!”全家人都笑了。这是劳作了一年的全家人难得的轻松一笑,这笑声让全家人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母亲和姐姐劳作了一年,终于有个喘息的机会可以歇几天了。她们不像平常那样起五更睡半夜了,母亲也不用走东家、串西家地干活儿了。但母亲仍不闲着,拜过年,大年初三就串筚子。过了破五趁没有外活儿,就抓紧空闲把我们兄妹的衣裳、袜子、鞋都收拾妥当,即把大的衣服改小,哪儿不合适就改一改、补一补。过年以后就要给外人做活儿了,或者纺线,或者卖煎饼赚钱。
妈妈平时也想方设法攒点儿钱,从各方面省钱,到过年让我们全家能吃上顿饺子,也让我们高兴高兴,有点儿过节的气氛。有些年太困难了,虽然没能吃上饺子,但我们也熬过来了。天下穷人是一家,都知道苦日子难过,乡亲们只要有碗饭吃也要分给我们一点儿。好心的街访邻居、婶子大娘们看我们生活得可怜,过年过节都给我们送点儿年货。
首先是大伯母,她比我们家也强不了多少,只是二儿子大了能多干活儿,又只养活她一个人,租人家三四亩地种,收获的粮食也刚够他们生活的。儿子有时再给别人打打短工,挣点儿买油盐的钱。每逢过年,大伯母总是最早给我们送过年的东西。快七十岁的人了,到了腊月二十八九,她就会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挎个篮子,两只小脚摇摇摆摆、慢慢地蹭着地来到我们家,一进门就连声呼唤我:“凤菊,凤菊!”我连忙上前接过篮子,搀扶着老人家上台阶,把她迎进屋里。她边走边念叨着:“咱们都是亲骨肉啊!日子多了不看你们,我不放心哪,但凡日子过得好点儿,也不叫你们这么受野(受穷),我也是穷啊!”每当大娘说这些话时,我就想:大娘这么大年纪了,还老惦记着我们,叫我们做小辈儿的过意不去,将来我若能挣钱,一定好好孝敬她老人家。心里边默念着边说:“大娘,叫您费心了,年年都来看我们,给我们送年货。”大娘是个心地善良、忠厚老实的农家妇女,不大会过日子,也不大会做针线活儿。她的针线活儿都是我妈有大小空时,捎带着给她做了。大娘走进屋里先坐到炕沿上喘喘气儿,再在屋里这儿看看,那儿瞧瞧。看见酸菜缸里、水缸里的水都冻成了一个冰窝窝,上面有点儿带冰碴子的水,就心疼地说:“可怜见的,一年到头不使闲(不闲着),这大过年的你妈还给谁家赶装裹(装裹是指给死人做的衣服。实际上,我妈去给人家赶做过节穿的衣服了,大娘生气用气话诅咒人家)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在家给孩子们弄点儿吃的!”我说:“大娘,我们没有什么好做的,等二哥卖了猪(自己养的二槽子猪),我妈拿下工钱,才能买米、买面。能买多少,还要看拿回多少钱呢,叫大娘费心了!”“大娘心疼你们哪!这屋里连点子热乎气儿都没有。哎,可有什么法子呀,穷啊!哪辈子作的孽!”她说着老泪纵横:“我比你们好不了多少,可还有个火盆烤。可怜的孩子,有什么法子改了这穷字……”说着就向外走。我把她送走了,回到家里觉得冷清清的,心里酸酸的。
远房二伯母、七伯母两家的生活较好,当时就有一百五六十亩地,都是财主了。她们履行着家族的礼仪,过年过节送点渣饼子或血糕、灌肠(用猪的下水、肉加上荞麦面做成的),有时也有少量的猪肉,送的较多的是豆渣饼子。这对我们来说是帮了大忙了,能让我们过年不挨饿。这些食物比我们家的饭好多了,母亲和我们兄妹真诚地感激她们。
我们远当家子六爷爷是族里的长辈,那时候爷爷辈儿的就他一个了。他生活好,看我们孤儿寡母挺艰难,一到秋天收下红薯就给我们两兜红薯,收完萝卜还让我们去剜萝卜缨子腌酸菜,还给几个萝卜擦成丝,放在淹酸菜的上面,防止菜烂。六爷爷对妈讲:“实在困难,可以来我这儿拿钱,不要利息。”
六爷爷还懂医,我姐姐腋下长个肿块,六爷爷用自己配的药给姐姐治好了。凡是过年过节,他都送吃食给我们。
我有个干弟弟叫赵金声,比我小三岁多,他的养父叫赵老镇,因为夫人生了三个女儿,他就想娶小老婆生儿子。他夫人赶紧到外村抱了个小男孩。那时因为我母亲生了个妹妹死了,有点儿奶水,我在吃“接奶”,他来了就不让我吃了,以后就把他奶大成人了,因此他认我妈做干娘,跟我妈很亲。
他们家的地位比我家高多了,他养父有一百多亩地,使着二套车,用着长短工,他养父还在西韩童村大地主谭魁武家的毡房(指做毡子买卖)里当“掌柜的”,每月能挣不少钱。干弟弟虽然是抱养的,但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人长得好,也乖巧听话,所以家里人都把他当成亲儿子。养父对他的学业要求挺严格,养母把他当宝贝。干弟弟对我们家很亲,尤其是对干娘好,六七岁时就知道孝敬干娘。一到过年过节就说:“给我干娘送点儿东西去。”
我大哥也有个干爹叫孙老金,也是穷人,老伴早逝,留下一男二女,以后他没钱续娶。他整年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个圆形的小柜子,里头装着熟肉,上面放着一把切肉的刀,一个干净的长方形案板,用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白粗布盖着;另一头是装着生肉的筐和一把斧子,走街串巷以卖肉为业。立秋后,他也卖牛羊肉,只要听见他在村里扯着大粗嗓门叫着“肥羊肉!肥牛肉!”就知道今儿立秋,可以吃牛羊肉了。有时他和二哥结伴去外村叫卖,到过年时给二哥一块肉,让他拿回家包顿饺子吃,但从未登过我家门。穷人帮穷人,他儿子结亲时也请我妈过去帮忙。
很多乡亲们自己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过年过节也礼节性地给我们送东西,让我们过个好年。由于乡亲们的帮助,过年时我们比平时吃得好多了。妈妈风趣地说:“咱们这是吃百家饭了!”
到了正月二十几,妈妈就对我们讲:“二十堂堂没得想,该上套拉磨了!”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牛马般的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