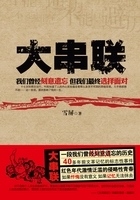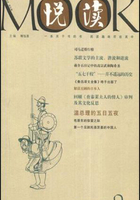01
郑舜成并没有改变姓氏,只是在曼陀山上那座自己的敖包前立了一座石碑,上书:尊父慈母白照群上官婕之墓。石料就出自曼陀山,是亲手到山上李占山的采石场掘来。字也是自己所镌刻,用凿子凿了一个整夜。
这是曼陀北村祖茔地间出现的第一块墓碑。
后来,又在离父母坟墓不远的地方堆制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石坟,前立一块大小差不多的墓碑,上书:科学家宋一维之墓。这完全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因为里面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没有人知道宋一维死后的情况,遗体安葬在了哪里?他有遗物吗?
就是在刻制宋一维墓碑那夜,郑家的大黑狗突然死亡。事情是悄悄发生的,那么强健的大黑狗一声不吭就倒下了,等黎明时,郑舜成走出屋门去看见,它已通体冰凉。尽管谁都没亲眼目睹,但谁都知道这是陆二楞干的。这次和火烧老榆树不一样,陆显堂并不是事先毫不知情,只是保持了沉默。他想,敲一敲警钟也好,叫小子知道,火不是好玩儿的。念头中间,已一点儿没有慈悲了。
这件事成为分水岭,陆显堂和郑舜成之间的矛盾发生质变,成为政敌了。
伎俩一度带给陆显堂满心得意,因为他高兴地看到它令形式急转直下,郑舜成打了退堂鼓,就是念书的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知难而退。
嘿嘿,知道难就好。
中间有妹妹和妹夫的巨大作用,他知道。还知道发挥作用时的出发点并不是帮自己。大黑狗被毒死的那个早上,陆文秀站在院子里孤独的杨树下,看着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喂大的可怜的狗的尸体,难受地哭了起来,边用手背擦着眼泪,边对站在一旁的养子说:“成子,咱不跟你大舅争那个破支书,咱出去念回书,不蒸(争)馒头蒸(争)口气!再说了,咱村这支书不好当,你大舅是一大家子,李占山是一大家子。咱一个外姓人,争不过人家的。”从话的口气,能知道她深知自己已是泼出门的水了。她的丈夫也深深叹气,帮着说:“唉,咱争不过人家的。再说了,咱犯不着,哼!就凭咱,犯得着跟他们这号人争?”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两个淳朴的农民心里只有对他们大黑狗的心疼和不舍,并无对孩子大舅的怨怼。同时,丝毫不觉得自己是在对着养子说话。在他们,成子仍旧是亲生的骨肉,这跟没有改成亲生父亲的姓氏无关,就是改了,他们也会这样。彼此间的亲情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犹如星星和月亮之间的依恋是天空的一部分一样。
郑舜成一言未发。让人觉得他已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陆显堂若无其事地又一次朝妹妹家走来。指导这行为的,是作为一个基层政治家的本能,本能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去了。
这次,是对郑舜成这样说的:“大外甥,你让当舅舅的感到骄傲!你这四年大学没有白念,舅舅的心血没有白费!其实,舅舅知道你的话对,曼陀北村当真照着你说的去做,确实没有不富起来的道理。可是,能做成吗?”眉头痛苦地锁起来,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农民哪!唉!咱村里这些人的心思,整个一盘散沙,有好处人人削尖脑袋往前钻,要是有了难处,嗐,没一个靠前。“就他们,你让上山植树种草,让去防风治沙,让围封草场搞什么禁牧舍饲,他们干?能听你的?别看现在乌仁老太太一煽忽,呼啦来了一大帮,那都是些没脑壳的,跟着瞎起哄。现在说得好听,一到阵仗儿上,你再看看,有几个肯真上?”端起杯子喝水,噗噗吹着浮在上面的茶叶,用这动作使刚才之言成为一个自然段。到觉得停顿够了,见年轻人仍低着颈子不搭腔,断定自己的话生了效。
便咳嗽一声,另起一段,说:“青年人,志当存高远!你读了那么多书,学到那么多知识,该当去干点儿更有意义的事情,干点儿将来能为北村帮更大忙的事情。”话到此处,脑中闪过轰轰烈烈这个词,就把它说了出来。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该当轰轰烈烈!
坐在一旁的妹妹妹夫不断点头,表示他们的崇拜和敬仰。陆文秀从来不觉得陆显堂是自己亲哥哥,对于她,他就是村支书,威严,高大,只可以仰视。她的丈夫感觉与她完全一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背叛他。只要他一出现,他们就会立刻变得拘谨和感恩。拘谨产生的幸福跟感恩产生的一模一样。此刻,他们坚信村支书取得了胜利,因为你看,他们亲爱的儿子始终一言不发。面对大黑狗的死亡时,这表现是深沉。但此际,便是默认了。
这令他们欢喜异常。
不管怎么样,都盼望儿子离开家乡,哪怕从此忘记了他们的养育之恩,不再承认他们父母的身份。
紧接着到来的一件事给这欢喜又固上一层色。家里又来了一个好看的闺女,是旗委书记的独生女儿,叫梅兰朵。是来动员他们儿子到旗城去工作的。她和他是高中同学。她是在自治区读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旗文化局工作。想叫他去旗城参加公务员考试,这次考中的公务员中将有一人幸运地进入旗委办公室,她希望这个人是他。
只要去参加了,就必定是他。
陆文秀乐得拢不上嘴,去旗委办公室工作也行啊。虽在穷乡僻壤,但也知道公务员的意思,就是与时俱进的铁饭碗。重要的,来送这饭碗的是旗委书记的女儿,这简直可以说,就是来送一顶银光闪闪的乌纱帽。你想啊,旗委书记的乘龙快婿,未来难道不是能看见的吗?
旗城也是城啊。再说,仕途不就是从小城市通向大城市的道路吗?
两个被可怜的父母心作弄着的庄稼人,以奔走相告的方式,去让自己的村支书知道了这件刚刚临门的喜事。陆显堂老奸巨猾地笑了。对站在一旁的侄子说,去张罗酒席吧,离村支部换届选举还有两天半时间,应该来得及的。今年要好好庆贺一下。陆二楞在这件事上一点儿没显出脑子慢的毛病,眼睛只眨巴了半分钟,便一撒欢儿朝门外跑去。却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候又被大伯喊住。陆显堂以少有的亲切口吻告诉说,先去你何安叔叔家,就说大伯叫他。
找何安来是为了商量怎样对付本次换届选举唯一的竞争对手李占山。何安来了,眨巴着秕谷一样的小眼睛,不屑地说,对付李占山还用得着费脑筋?
仅就李占山而言,何安的张狂是有理由的。遗憾局势并没有如所想那样简单地到来,而是来得十分复杂。李占山眨眼之间就变作盟友,坐在了陆显堂家的炕头上,商量战胜共同敌人的办法。很不幸,是郑舜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或者说,是刘逊。
前所未有的刘逊啊!
郑舜成,这个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成了自己的强大对手,陆显堂的悲哀中浸满苦涩,仿佛那些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人。
情形也是郑舜成不愿意看到的,这便是他曾经打退堂鼓的真实原因。当时,陆文秀夫妇和他们的村支书还以为是因为大黑狗,错了,能令郑舜成这样的人发生改变的,绝不会是恐吓,而往往是情义。从大黑狗的遭遇,郑舜成清晰看见自己将与养育自己长大的舅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的性质,他不想这样。不是畏惧“忘恩负义”四个字,是不想自己实际的亲人受到伤害。
一开始,他想的只是为家乡作贡献,并不知晓事情的另一面是,自己的亲情将会付出巨大得承受不起的代价。
梅兰朵的好意只是使他的心微微动了一下,就像微风吹动下的花瓣的摇曳那么轻。立刻就回到了初衷,还是到深圳去,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白诗洛。他清醒地认识到,到旗委去工作将是徒劳无益的。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只能是那架依惯性运转的庞大机器上,小小一枚螺丝。而做这样的一个零件,更合适的人太多了。
如果不能够从曼陀北村和千千万万个曼陀北村做起,那就什么都不会从根本上发生。
没有让梅兰朵立刻拥抱失望,听完她的话,他笑笑,说:“请帮我一个忙好吗?”请她设法找一辆越野车,带陶可到西布图草原去走一走。最好明天一早就能出发。梅兰朵像心地单纯的姑娘们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眼睛一下亮得像星星,当郑舜成是认她为自己人了。快乐地笑起来,问:“什么时候回来?”
“最好是,就把她交给你了好吗?”
更快乐了,用格外清脆的嗓音说,“行。”
梅兰朵很快就走了。那是个好天气的日子,黄昏时出现了绚烂的晚霞,只有在这样塞漠深处的草原上才会见到的热烈晚霞,那激情放射的样子,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落日的余晖,而是日出的序曲。望着它们,郑舜成想起曾经给白诗洛描述的塞漠情景。那个温暖南国里长大的美丽女孩眼里好奇闪动,问:“城市就在大漠中吗?”当时,他一下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不知为何,那一刻,忽然地,他想起了家乡的晚霞。
就在那天壮丽的霞光中,刘逊朝他走来。
刘逊是从西边来,那是乌兰布通镇所在的方向。所以满天云霞就成为衬托的背景。郑舜成望过去,看见的是一个镶着光闪闪亮边儿的身影,烁烁的镶边制造出神奇效果,吉祥、高大、激动人心。
刘逊是来给郑舜成送党组织关系的。决定留下不走后,郑舜成就在刘逊的建议下,给白诗洛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用刘逊的手机打的。郑舜成请求白诗洛将他的党组织关系以最快速度寄过来。十分抱歉地、困难地,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听见她顿时就不说话了。这使他一下子语无伦次起来。由此发现沉默原来是最好的雄辩。在白诗洛的沉默中,他渐渐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了。幸亏刘逊在一旁保持着清醒,刘逊说:“把我的地址告诉她,让她寄到我这儿来,这样快。”就照着说了。直到他结束,电话里再没传来声音。
刘逊安慰说:“没关系,让她不要误解。我们欢迎她到塞外来,真的,她可以到咱们这里来。”不安地看看郑舜成的眼睛,迅速又将目光移开,又说,“等咱们这里的草原重新鲜花烂漫的时候。”
郑舜成知道,刘逊心里十分十分地抱歉,比自己还强烈,因为多针对着一个人,除了他,还有白诗洛。
还有内疚。
这情愫,两人就不分伯仲了。内疚,为他们的草原。那是草原上男人的内疚。
快件里装着的不只是党组织关系,还有郑舜成的大学毕业证书。这令两个面对它们的男人,于瞬间的惊喜后,深深跌进沉默。尽管白诗洛未着一字,但事情像纯净水一样明了。她在离校时,以巨星公司的名义取走郑舜成党组织关系的同时,取走了他的毕业证。
前者是他同意的,后者是背着他的。
良久,刘逊说:“还想等我爱人回来后跟她商量,从我们家的存折上支一万块钱,去取回你的毕业证呢。她到市里去学习了。”停顿一下,又说,“那也还是得这样,到时候把钱给你的女同学寄到深圳去。咱大男人不能让人家女孩子花钱。”
郑舜成说:“这是学校今年才实行的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前几届学生有些人毕业后,工作了却不肯主动还学校贷款。”
刘逊点点头:“我知道。”
郑舜成还是解释:“毕业证算是典押吧,让学生们想着自己还欠学校的费。”
这下刘逊就没吭声了,因为已明白眼前这个人这时候说话的目的只是为了说话。
等到觉着时候差不多够了,轻轻清了下喉咙,淡淡地说:“后天就开换届会了。第一天推荐候选人,两天后正式确定村党支部班子。”
郑舜成微微一愣,随即像是猛然想起来,急急说:“刘书记,我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后天的会我就不参加了,我准备后天一早就动身,还是到深圳去……”
这话制造的不是一般的吃惊,但刘逊丝毫不露,只是手沉沉地,伸进衬衣口袋,摸出一支烟,沉着地点燃。他不会放弃的。等到一支烟快要抽完,努力开始了。
话题跟前些天那个美丽月夜里的不一样,大致是这样的:
“你读大学,只为自己找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说实话,当初的确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也有学到本事将来为家乡为社会多做点儿事情的想法。”
“你以为在大城市里得到一份工作,使自己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里过一份城市人的生活,就是改变了命运吗?你的命运只跟你个人的祸福有关吗?”
大学毕业生不语。
“你学到了本事,却在家乡最需要的时候扭头而去,想一想吧!”
“其实,报效家乡并不只有一种方法。”大学生低下头去。
后来,大学生说出了自己真实的内心,是担心自己肩负不起这副担子,村里太复杂了,他不愿陷入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不愿伤害亲情。
“消解信心的罪魁祸首是私心!”镇党委书记一针见血。
“没有阳光才会畏惧迷雾!”
“难道我们就不承担时代前进的责任?”
句句是诤言,可惜,终于不能使青年学生的心回头。后来,月亮出来了,已经不是曾经那圆得要转起来的一轮,是一道弯牙儿了,它令站在地上举头遥望的人,忽然间像是被夜雾包围了,陷入苍茫的感伤。
02
采石场风光的别致,是时而会有一道沙尘柱似卡通片里被魔法咒着的海水,在半空中疯了样旋转。这里,念咒的是风,风一个呼哨,钢钎剥下的碎砂就“刷”地抱成一团高高耸立起来,像没有脚的鬼在山坡上呜呜地转圈儿。它们的领地里,永远码着几堆毛石墙,响着单调的打钎声,晃动着十几个采石工健壮的身影。离这些不远处,一条灰白色的山路上,停着一辆老旧的“2020”吉普车。此刻,一个壮年汉子在车上咬牙切齿忙活着。马达闹出声嘶力竭的动静,压住了打钎声和风声,车却不能发动。这使他焦躁极了,“咔”地打开车门,跳下,“砰”,在车轮上踹一脚:“妈的!啥破玩意儿,这不是存心误老子的大事吗?!”
“要我说,李大哥,去选那破支书干啥?不如就在这儿‘占山为王’当场长!”七十二停下手里钢钎,朝这边笑嘻嘻喊一嗓子。他是在爷爷七十二岁时候所生,故而有如此名字。
“你小子知道个屁,好好干你活儿得了!”壮汉气得咬牙,最听不得占山为王四个字,何况是此等关口,“不竞选支书,村里欠我那两万多元咋办?找谁还?”心里的牢骚本是呼啦勾起,却在这时沙尘柱旋过来,一把碎沙嗖地呛进了嘴巴,后半截话就刹了车。也不吐,就那般又钻回车里,接着胡乱鼓捣。不想猛然轰一声,车子竟发动了,于是朝前一蹿,左右晃两晃,歪歪扭扭下山去了。
进村子时,街上正大摇大摆走着赵铁柱,直到喇叭声响到耳朵旁边了,痞仔才闪身子躲,弄得开车人冒出一身热汗。“妈的你小子,不要狗命了!”头探出狠狠往泼皮脸上一啐。“哟嗬,是李大场长的车呀,不看出来。”赵铁柱一扭脖子躲开飞痰,脸上的笑麦秸样堆起,“啥事儿这么忙呢?莫不成是去竞选村支书?”车子忽地慢了,又探出滚圆一颗脑袋,这回一副当真的样子:“就是。铁柱子,说真格的,你不是一直想着到我的采石场去上班?投我一票,就让你去!”“就投你老人家一票了。”赵铁柱嬉皮笑脸。“2020”突地加速,车后拖起呛呛一串土尘。冲着车影,泼皮鼓起腮帮子使劲吐口唾沫:“嘁,谁稀罕你那破石头场!”
采石场场长在村部院子停车的声音,只有陆支书一人听见。当时村部屋子里正闹作一团。陆显堂结束演讲回到自己椅子上,掌声稀稀落落,就像春雨被干燥的泥土吸住,眨眼间不见,会议出现冷场。过了好半天,孙二娘眨巴眨巴眼睛,嘻嘻哈哈站起,粗着嗓门嚷:“大家伙儿谁想上台快点儿上哈,不然我可要上了。总得有个陪绑的嘛,咋能让陆支书唱独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