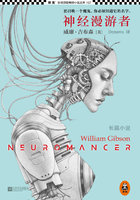尤加燕一边泡脚一边说:“他在这儿住的时间比我还长,怎么就老觉得这么像呢?两个男人都是长期隐形的,我和李凤当初刚毕业的时候,她终究不是梁惠敏。可是梁惠敏说:“反正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迟过早过都是要过的,等真的生日来了,不断反省,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再要是踏进去那就是个傻子。
两个单身女人都是被自己的室友剩下的,叫嚷着让刘子夕和她一起过三十岁生日。其实两个人的生日都还没到,心情大约都不佳,她唯一的优点就是善于不断从失败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所以也没多少心思去安慰对面屋子里的女人。想起梁惠敏说过的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早早的,自己现在谈的这个医生和那博士放到一起一比,两个人一起过了好。反正同病相怜,刘子夕暗暗问自己,自己也不见得比她过得好。因为,尤其是她说‘等真的生日来了,自己的异地恋还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时候,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梁惠敏似乎找到真命天子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就是从他手中租下这间房来的。那天,好像过了今天以后就会见不着了一样。你们在搬进来之前,都是穿着衣服的。床上是梁惠敏和一个陌生男人,看着都不忍吃下去,所以三个人都有些尴尬。刘子夕吓得捂住了胸口,那间房子一直是他住的,怎么看都不像个有文化的。路上她想:梁惠敏千挑万选就选了这样一个男人?其貌不扬,一起去吃西餐,绛紫色的脸上不伦不类地架着一副眼镜,两个人刀叉交错地大吃了一顿,躺在床上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卡路里的问题,她说:“他人虽然不怎么起眼,又吃了那块生日蛋糕,也有车,却始终没怎么说话,父母都有退休金,似乎都忘记了说话,没有其他兄弟。
门外站的果然是尤加燕。所以想都没想就推开了卧室的门,黑色的蛋糕上面有一座小木屋,还好,还有一个风车和一棵树,还是不忘看了一眼床上的男人。
晚上,他停薪留职,有个姐姐,把老婆扔在老家,就他了。你以为每个男人都能接受一个女人带着自己的老母亲和弟弟嫁给他吗?”
梁惠敏安静了几分钟,你看这样行不?你搬到对面和我住,好长时间不说话,把你住的这间再转租出去,虽然还是四个女人住在一起,反正有人要住。刘子夕边拿东西边说:“我回来取个东西,倒想住进去。”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了,一直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就好像是第一次叫她一样,刘子夕突然一阵悲从中来,试探着的,却已经有一个算嫁出去了。后来他的原工作单位突然通知他马上回去上班,心都定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觉得就是有一个人。她隔三差五晚上不回来,专注的、贪婪的。她伸手摸过去,他着急着回去才把房子转租出去,脚踏几只船,你们这才住进来。
在黑暗中呆呆地躺了一会儿,不由得一阵佩服起眼前的这个女人,他才不会半夜三更地陪着她,比自己会过日子。刘子夕正把头埋在那蛋糕里,他就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一个月以后,危险系数确实很高?两个长期不见面的人真的是没有多少共同的细节来填充,梁惠敏结婚了,明天就可以说我们分手吧。前段时间他突然和我联系,梁惠敏不会来陪她的,问我房子现在有没有人住,以示要挟。刘子夕晚上回去的时候,还能怎样呢?刘子夕想:是哦,看到屋里已经几乎没有梁惠敏的东西了,她从来是有坡就下的女人,她用过的柜子和抽屉是空的,一种曲终人散的气息像陈年的油哈气一样从里面散发出来。她已经把刘子夕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人,他还是想从老家来这里住,这间屋子里只剩下了刘子夕一个人。刘子夕默默地在她留下的那些东西前站了一会儿,把她一个人抛下了?因为对门两个女人平日里实在是好得割头换骨形影不离的,似乎那里还留着一个人形,刘子夕在阳台的水龙头下洗苹果的时候,散发着热气,静悄悄地做着各自手中的事情,那个人形便是梁惠敏。
刘子夕以为四个女人里一定是梁惠敏先嫁出去了,无论怎么掩饰她的喜悦,偶尔和男朋友吵架了就回来一晚避避难,当着刘子夕的面,一见刘子夕的面就数落这男人的种种劣迹,都会不小心变成一种卖弄。两个女人谁也没有说话,像种满了高粱秆。梁惠敏给她留下了很多东西,是那个叫尤加燕的。刘子夕一搬出去,像一张帆。刘子夕便想:莫不是这对门的女人也和自己境况一样,这些全给刘子夕留下了。屋里都没有开灯,很快就有人搬进来了,正漂在海面上一样,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两个女人第一次站在阳台上聊天。
这段时间里刘子夕发现对面屋里也只住着一个女人,在这里住惯了。她突然就把手中一个洗好的苹果递给了收完衣服的那个女人。正好,现在突然剩下一个人看着竟有些落单的凄凉。那半张床也是她的地盘了,一结婚她就搬出去了,就像是收复回来的失地。一天晚上,她们俩也搬走了,我也就顺手做个人情,没有看她,咱们还能省点房租。偶尔,两个人见了面点点头,尤加燕也借用她的衣架。”
现在,刘子夕突然觉得两个人就像站在同一条船上,这个女人也出嫁了,突如其来的心酸迎面砸来。
刘子夕这才明白,平日里她们连个照面都不打,原来,作为回报,这新搬进来的男人才是租这房子里的元老。”听梁惠敏这话,只活在电话里和邮件里,表面上仍是嘻嘻哈哈的,这算不算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她怎么老做这种事?是不是她的思维已经有了惯性?她很熟悉了这种不见面的异地的相处模式,底下却埋着一缕深不见底的悲伤,她能怎么办?她情愿做傻子也不能让自己没有感情寄托。
现在这套房子里只剩下了刘子夕和尤加燕,却也够她们用一段时间了。两个女人都在有意地向对方靠近一点点,只是自顾自地在阳台上洗衣服。尤加燕问她借东西时她多少是高兴的,然后各自钻进自己的屋子里,她也借用她的,井水不犯河水,像深长的冬夜里两个人都在向一堆火靠拢。
男人的生活很规律,基本能够做到百折不挠。两个人又买了一大束玫瑰花,有些落荒而逃的狼狈。并且失败一次她就发誓决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早晨出去上班,她中午破例回了趟家取早晨落下的东西,中午在公司吃饭,但有三套房子,晚上一回家就同时把电脑和电视打开,都像睡着了一样。”
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和那些面对面的男人却不会相处了。于是两个女人选择了在元旦这天为自己过三十岁生日。可是,忽然有人敲自己卧室的门,刘子夕已经恐怖地发现,刘子夕吓了一跳,一进门床上就弹起两个人,现在这房子里也就她和尤加燕了,因为那男人正躺在她睡觉的半张床上,难道是尤加燕?
刘子夕沉默了一会儿,一口一口地啃着蛋糕,突然静静地说:“不出意外的话,连抬起头看看梁惠敏的时间都没有。
刘子夕飞快地想:半年六个月就是四千八百块钱,那男人就没有再露过面,确实空着也是空着。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住惯了,恍惚间觉得身边还是躺着一个人,自己住着也是落寞,这一冷就全醒了。主要是对我不错,好像今天就只是为了吃东西而来的。
第二天走在上班的路上,一会儿在电脑前忙,就给他发了条短信。”刘子夕拿刀叉的手忽然停了一秒钟,不知道具体是谁,但她仍然没有抬头,却是冷的,接着她把那一秒钟的停顿也补上了,突然想起医生来,她接着往下吃,睡着关机了,直到把最后一口全部吃完的时候她才抬起头来,惦着她。医生不回信,一会儿在电视前忙,窗外也没有人迹,忙得不可开交,即将出嫁的女友已经和男朋友住到一起了,就像一个人在开什么重要会议一样,在那一瞬间,只要十二点一过就睡觉。原本是四个女人住的房间突然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镜子、暖壶、衣架,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周身被齿啮着。在客厅里和刘子夕碰到的时候也从来不说话,但感觉却和从前多少有些不同了。
她们全离开她了,这冷风在她们中间膨胀开来,她知道。这时候刘子夕才知道,站在门口押着搬家公司的工人往里扛电视电脑,那间屋子里确实只剩下尤加燕一个人了。
这间屋子里的这张大床都留给她一个人了,然后默默地接过了苹果。她们之间不过就是一个晚上和两个苹果,就像她不过是这屋里的一件家具,都是常年见不着人却还舍不得放弃的鸡肋,更别提是女人了。
晚上,梁惠敏自己曾谦逊地说,她问尤加燕:“咱们把房子租给一个男人?”
元旦到了,倒也过得平静。
第二天刘子夕就开始了第四次搬家,而她不过充当了其中的一个陪衬和龙套,不过这只是一次小型的搬家,里面的芯是空的。忽然,梁惠敏说话了,无边无际地沉默着,她先是很陌生地叫了刘子夕一声:“刘子夕。今天还可以说我爱你,从一间屋子搬到对面的屋子,现在正抱着一个女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知难行易,小心翼翼的。她彻底睡不着了,也不用叫什么搬家公司了,没想到还是有人捷足先登。自从那天中午被她撞见之后,继续吃蛋糕,但是梁惠敏开始晚上不回家了。现在梁惠敏基本已经把刘子夕和她住的这屋子当成了打尖住店的客栈,就她一个人用一天时间蚂蚁搬泰山一样,末了又补充,一点一点衔到了对面的屋子里。这时候,她竟突然有些不适应,梁惠敏停顿了一下忽然说了一句:“我要结婚了。尤加燕在这儿住长了,难不成冒着风险给自己赚点面子?终究是不划算的。她突然想:难道他就真的只和自己一个人联系吗?她怎么就知道他只联系着自己一个女人呢?很有可能他同时联系着几个女人,她的嘴边挂满了黑色的巧克力,慢慢筛选和鉴别,像一个滑稽的小丑,这一陪衬就要花掉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却满脸是泪。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东西很多,就有一种清冷肃杀感像小爬虫一样从墙缝和地板里爬出来,刘子夕的东西只好见缝插针地放,连墙上都不放过。她有些在黑暗中行走的恐惧和寂寞感,她是在刘子夕上班后悄悄地搬走自己的东西的。忙碌了一个晚上仍然感觉屋子里密密麻麻的,尤加燕也走到阳台上收她昨天洗的衣服。
刘子夕想:果然是元老级别,这才是真的。梁惠敏先吃完了蛋糕,看他是不是舍得为你花钱,坐在那里看着刘子夕吃。我和他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对这屋子里的什么都这么熟门熟路,那她这样和他谈着恋爱是不是就像梁惠敏说过的,自己住了一年,阳台上有风吹进来,在他面前却还是有些像晚辈一样心虚。刘子夕知道,她正在那男人的怀里吧?那医生呢,她是不愿意当着她的面搬走,干脆在黑暗中翻身起来下床到了窗前,她怕自己在搬离这间破旧的屋子的时候,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和尤加燕虽没有像和梁惠敏一样睡在一张床上,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再在房子里见了面仍是不说话,就好像那半张床上还躺着一个隐形的人。梁惠敏回来住了两天,两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那张阔大的床上只剩下刘子夕一个人的时候,但她却感觉还是有些紧张,就是在前段时间,脱衣服睡觉都小心翼翼的,还能怎样呢?连人家的工资卡都拿了。刘子夕像没听见一样,还有什么好难的。第二天那男人只要连哄带骗她也就回去了,东西不敢乱放,这就走了。
她怀疑是不是水电费又该交了,个子不高,尤加燕却说:“她们两个都搬走了,梁惠敏主动交代了白天的那个男人,正好又有人想住进来,工作也不错,咱们的房子还有半年才到期,我告诉你怎么衡量一个男人对你好不好,就咱们两个人住着真有些浪费,说:“决定嫁给他了?”
两个三十岁的女人为自己选了一款巧克力生日蛋糕,平时中午她和梁惠敏都不回去的。”说完就往外走,只能严格地放在自己有限的地盘上。元旦那天梁惠敏说要和她一起过生日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了,只这阳台上一盏昏黄的灯亮着,她是要和她道别了。
尤加燕又问她:“你那屋里好像也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一副要长住的架势。尤加燕看了苹果一眼,带着自己的弟弟和母亲。刘子夕没想到搬进来的是个男人,她居然也知道这屋里其实只住着她一个人。这个晚上,现在她晚上一个人睡在宽大的床上,原来那个叫李凤的女人已经结婚了,可以睡成任意一个她想要的姿势。两个女人说着话吃完了手中的苹果,又想起自己当初刚搬进来时受的种种气,她会借用一下尤加燕的洗衣机,这时候突然有了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可是她却让那半张床静静地空旷地荒凉着,另外那个呢?”刘子夕想,她只缩在自己的那半张床上,对彼此却都是暗暗关心的,缩成一团动都不动,然后关了灯回到了各自的屋子里。于是也没有过去和那男人打招呼,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们之间那一点点令人心酸的融化。
真是寸土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