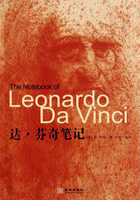当然,对于电影价值的评判也都是从这两个层面进行的,对电影观众而言,艺术性无疑是吸引他们走进影院的首要因素,也是对电影做出回应的第一标准;而对电影生产者来说,票房、利润才是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因此,电影要想同时取得精神价值和经济效益,就必须将观众需求作为生产制作的前提,而最有效的吸引观众的手段,就是电影的艺术性。任何片面强调电影艺术性或者商业性的评判,都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单个电影文本与整个电影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电影产业萧条的年代,电视的普及、娱乐方式多样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电影面临着观众大量流失的现象,正是贺岁片的出现,甚至于贺岁档的形成,打破了人们对于电影产业低迷认知的固有理念,开始探索贺岁片成功的原因和模式。随着贺岁片票房的飙升,电影的商业性被重新认识:由于资本在电影的生产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话语权,于是不难发现,对于贺岁片的投资,成为了资本青睐的对象。面对这种现象,观众表现出强烈的观影意愿: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高投资本身就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而评论界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部分论者承认贺岁片的票房以及对观众的吸引力,对其成功表示赞同,认为贺岁片(单个或是整体)是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双赢;一部分论者则认为贺岁片太过强调商业性,必然会忽略电影的艺术性,甚至于为了吸引观众,大量夹杂低级娱乐的笑因,反而忽略了文化元素。近几年来,后者的声音越来越响,每年的贺岁档期、每部贺岁影片的上映,都能在媒体的溢美之辞外发现对于影片文化缺失的担忧。从某种程度而言,贺岁片确实存在艺术性与商业性分化的“危机”:电影评论者和研究者对于电影的商业性带有本能的悲观倾向的认知,尤其是面对作为贺岁而制作的电影,“类型化”本身就是商业性的表现,其娱乐功能被进一步放大,资本的痕迹逐渐加重,针对影片中越来越多的植入广告等商业元素,他们发出了“电影商业对美学的强暴,可能会更加剧烈”的感慨。而电影产业界则认为“高投入——高票房”的运作模式完全遵循了市场规律,数字技术、媒体造势、广告吸纳和衍生产品开发的新的营销模式也已经成为影片成功的不二法门。由此可见,观念上的误区呈现出实践上的偏差,也必然会出现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对立。
然而,对于任何一种事物而言,其内部的分化并不意味着落后,而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显著标志。无论是社会的分工还是物种的衍变,甚至于文化的多元化都是如此。从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作为电影的本体属性,二者间的对立,是伴随着电影的诞生而诞生的,也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分化,才使得西方电影得以不断发展。因此,西方电影表现出商业性和艺术性分化后的进一步重组,而中国电影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电影商业性必然会受到压制,对于商业性的讨论也处于消音状态。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电影产业的转型和发展也必然要将商业性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从被压制到被关注,如此巨大的落差使得评论界和业界出现了理解层面的差异,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早在80年代,学界就认为“大而言之,在现代社会里,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商品的艺术品。把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加以对立,似乎有了商业就不可能有艺术,要艺术就非得不顾票房的价值。这完全是一种谬论。”明确指出,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是属于电影本体的概念,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则是属于电影类别的概念。任何电影,都同时具有商业性和艺术性这两个本体属性,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区别在于:这两种属性的强弱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模式,进而导致影片叙事策略、审美功能等方面的差异。而当下的争论可以说是旧壶新酒,并不是如表面上所显示的,学界和业界对于电影商业化和艺术化对立和分化的强调,而是关于商业性在电影中所占比重认知上的差异。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的争论,使中国电影得到进一步发展,纠正了长期以来电影商业性的暂时迷失。因此,贺岁电影呈现的分化“危机”,也并不是真正的危机,不会使其走向消失,而是在反复实践中重新杂糅和重组商业元素在电影中的比重,使得商业性和艺术性融合得更为充分、更为细致。
电影之所以为商品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有两种基本形式: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其中,物质生产即主体运用生产手段作用于客体,一般作用于改造对象的物质形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一切其它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而精神生产则是主体运用生产手段作用于客体,一般作用于改造对象的观念形态,并不对客体进行物质形态的改变。简言之,物质生产是外倾的,作用于外部的客观世界,精神生产则是内倾的,作用于内在的主观世界。当然,由于精神生产实质上是社会意识(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形式的生产,其本质上是一个思维的运动过程,对客体的改造方式是抽象的思维过程,目的也是为了满足生产主体的精神需要,这就决定了精神生产的过程、产品属性都是无形的。因此,其产生和发展必然是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和载体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由此可见,无论是广义的精神生产(“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还是狭义的精神生产(“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都是与物质生产交织在一起,并从属于物质生产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逐渐出现分工,精神生产便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能够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来进行精神创造活动。而“相对独立”则是指精神生产的社会制约性:一方面,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的动力必然指向物质生产的需要:“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精神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者必须消耗的生活资料都是由物质生产来提供的。而脑力劳动者,即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劳动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生理条件、心理条件以及知识水平等主观因素,同时还受到资料、设备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最后,精神产品只有物化于物质产品中才能得以保存,才能得以实现其现实的社会功能。因此,虽然精神生产具有明显的自由性和创造性,是一种“特殊”的独立生产形式,他仍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当然,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也具有反作用力,不仅为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工具变革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而且对生产力中占主导因素的生产者的精神素质和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多体现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劳动者生产技能和积极性的提高上。尤其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进一步将道德、科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特殊方式来研究,使得精神生产成为人创造历史的重要活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相反的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而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电影,固然有着属于精神生产的那部分,表现在创作的自由性和主体的社会性上。然而,马克思又认为,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一切生产劳动都可以归结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即“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因此,电影的制作和发行需要一个庞大的合作团队,只有剧作、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化装、剪辑、洗印、照明等各艺术及技术共同参与、互相协作,才能完成。据此,我们不难发现,电影本身只是一件巨大的产品,只有将它投入市场,完成使用价值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交换,才能成为一件真正的商品。作为一种产品,电影与其它商品一样,其生产过程都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包括:生产环节(电影的制作)、流通环节(电影的发行)、消费环节(电影的观赏),这样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必然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因此其生产也必须考虑到经济效益和商业回报。从这一方面来说,电影是典型的商业艺术,它凝结了社会必要劳动力,其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两重性,且强调其艺术产品作为美的物化方式,并且作为人类无差别劳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是当前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首先是企业,其次才是艺术。
电影的商业性直接导致了电影在美学追求上的大众化、重复性、多样性等特点。作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电影受制于商业性因素,必然会追求大众化,追求媚俗,通过制造带有暴力、色情以吸引观众,或是用无意义的喜剧来迎合观众的娱乐诉求。由于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不同,电影也随之体现出风格的多样性,电影正是结合大众的同一性与个体性,划分出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类型电影都有自身特殊的深层次精神结构、表意策略、叙事方式、形式风格,甚至对观众的心理反应模式都能区分、独立出来,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以便投资、制作、发行等各个环节实现相对稳定的机制。这自然极大地影响了商业电影的回报和重复性生产。
明星的商品化
电影诞生之初,观众很想知道银幕上那些迷人的演员的名字,但制片商“对演员的姓名严格保密,以避免给剧团经理带来向明星和演员支付高薪的麻烦。”当时的观众便开始用演员所演的角色或是所属公司的名称来称呼他们,比如“维太格拉夫女郎”与“比沃格拉夫女郎”就是后者的产物,后来维太格拉夫影片公司很快顺从观众对明星的要求,在演出海报上亮出演员的姓名,但比沃格拉夫影片公司却拒绝这样做。于是美国环球影片公司老板卡尔·莱默尔便诱使“比沃格拉夫女郎”弗洛伦丝·劳伦斯脱离公司,加入到他的影片公司,并在《圣路易斯快邮报》发出一则消息,声称劳伦斯已经身亡。次日,劳伦斯却“在舞台上亮相,好让大家知道‘比沃格拉夫女郎’如今已加盟独立影片公司。”“死而复生”的偶像使得影迷疯狂骚动,莱默尔用这样的造星噱头将劳伦斯捧为世界上第一位电影“明星”,在公众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至此以后,其它公司便纷纷效仿这种有利可图的方法,让自己的明星以真名示人,继而影迷杂志应运而生,明星制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