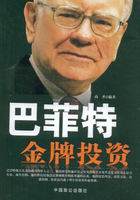这期间,姐姐偶尔停在我脸上的目光如同飞落的沙尘,转眼便隐没在夜的寂静里。而我,也借着灯光,趁她将目光移走的一刻,仔细打量起她。此时此刻,姐姐昔日里雾一般的嘴唇已经变得十分具体,在这段一声不响的时间里,除了色泽暗沉,她们始终无可奈何地微张开,像是极木然的,任由时间、寂静和未知在上面踱来踱去。意识到姐姐心里的不快后,我拼命想用一件另外的事情挽回姐姐的情绪,但一些漫在嘴边的话,因为不具备这个力量,便又被我抹去了。
此刻,我坐在姐姐对面的靠背椅上,隔着一束柔软的灯光,期待着姐姐。也许,当我打碎她对七婶的幻想后,她愿意越过那堵骄傲的墙体,慢慢地跟我说些什么。
姐姐还是不说话,末了,叹口气站起来,从我面前走过,邋遢着步子,犹犹豫豫站在了衣柜前。姐姐慢腾腾打开一扇柜门,似乎又停下片刻想了想自己要做什么,接着伸出手臂在里面翻找起来。我从一旁穿衣镜里看到她的侧影。比起本人,侧影十分黯淡,然而使我吃惊的是姐姐的身形又在变化了。如同三年前,姐姐的身体正在变得细长,这一次,我尤其注意到了她的脖子与手臂。她的脖子随着抬起的脑袋越伸越长,她的手臂随着手的翻动也在慢慢长长,从而在关节处不得像根面条似地垂掉下来。
我不确定姐姐在想什么,但我知道,此刻,那件她正沉没于其中的事物,一定在拼命拽拉着她的身心。而我必须制止这件事物对姐姐的侵害。
“姐,你在找什么?”我惶恐地问。
“不找什么,我想洗澡,找睡衣。”
“睡衣不就在你枕头下么?下雨了,你晾在外面,我给你取回来了。我对你讲过的。”
“唉,都被你搞昏头了。好了,没什么事,你去休息吧。”姐姐转身的一刻,身形也恢复了。
“那么,明天你与我一起去养殖场吧。”
“你不让我去七婶家是为什么呢?她就是没有大经历,我跟她说说家常话会有什么关系呢?”
“是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希望,你来我这里,我们最好在一起,不然,我会觉得自己不管你似的。”
“你不要多想。你是要做事的人,整日忙里忙外,我不给你添乱就好了。”
“姐,我就对你讲实话吧,七婶不喜欢外地人,她和七叔都对外地人有意见,尤其是到梅镇来旅行的人,她说他们的想法和话语都带毒。”
“带毒?”
“嗯,带毒,就是说他们身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像刀子一样,会把梅镇割开一条条口子。”
“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可是她像是愿意与我讲话的。”
“你毕竟是亲戚,而且,你……七婶眼睛厉害的很呢,你是怎样一个人,她大概都看了出来。”
姐姐坐回床边,看着我,眼神里像是有一件极遥远的事物,我看不懂。
06
五月末,天气已经闷热起来。每年这个时候,梅镇便会笼罩在一片安谧慵懒的气氛中。这都是因为珠蚌在吸纳了珠核之后,回到了温暖的水中,如同一具受精的母体,开始了它们各自漫长的育珠历程。在这个季节里,世代养珠的梅镇人都会于无知无觉中感染上一种母性的甜蜜与满足,就好像一个怀胎的妇人,简单梳洗一番,便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懒洋洋走在街巷里,沐浴着微风与阳光。而无论她自身,还是遇见她的行人,都透露着由衷的喜悦。
当年,我便是在这个季节决定留在梅镇的。或许梅镇真的就像一个珠蚌,我便是一位愿意进入它体内的外乡人,一粒被梅镇揣在体内的异物。那么,姐姐呢?她来梅镇,是想和我一样成为一个梅镇人,还是只想撬开梅镇的蚌壳,看一看珠蚌内部的风景?
姐姐依旧往七婶家跑,不过,她不像之前那样毫无顾忌了。她多半乘我去养殖场的时候在七婶家呆一阵子,也能够赶在天黑前回家;假如有一天我特意留在家里陪她,她便与我在院子里一起洗洗衣服,聊聊天气,或者伺弄花草。除了告诉我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又做了更大的事业,姐姐仍然不愿意跟我谈些她自己的事。
姐姐一定被七婶身上的什么东西吸引着,但是我又不能告诉她更多。这些年,我也和梅镇人一样,越来越迷信了。因为梅镇人都说,七婶的眼睛能看见所有人的秘密,七婶的耳朵能听见所有人没有说出口的话。所以,关于七婶,我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得体,从而被她那只无处不在的耳朵听到,就此得罪了她。
在梅镇,没人敢得罪七婶的。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洗了衣服,收拾完一些零碎的家务,我们全家人都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有位亲戚为家中长辈做寿,兼带给孙子过周岁,两件喜事凑在一起,几乎将整个梅镇人都请去喝酒。孩子和他们的父亲走在前面,我和姐姐提着礼物,不慌不忙跟在后头。
阳光懒洋洋洒下来,海风像麻利的育蛛女,轻动手指,便将主人家的喜悦传递在每个巷口,梅镇的每条街巷,因此都流动着一缕节日的喜庆气息。我和姐姐慢吞吞走着,路上不时碰见同去贺喜的街坊。对每个人梅镇人来说,能被主人请去喝酒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当在贺喜的路上遇见,彼此之间都要用最响亮的声音打招呼,以示内心的骄傲和快乐。但这快乐并不是立刻就会释放完的,反而是越临近主人家的门头,快乐就越高涨,仿佛每个人都走在一根攀升的音符上,而音符的前方,便是无止尽的欢乐。这情形有些像每年收获珍珠的季节,那些铺在软箩里的珍珠结束了它们在蚌壳里的时光,从黑暗润滑的母体来到了四处喧哗的光明里,因为吃惊而发出了万千种惊呼。它们吃惊既因为看到了天空中的光亮,也因为看到了彼此身上的光芒。很快,这些惊呼声传到每一个养蛛人的耳朵里,每一个养蛛人便都疼爱地咧开了嘴,他们笑这些惊慌失措的珠子,笑它们美丽的光芒,笑他们的日子再一次笼罩在这些珠子雾蒙蒙的珠光里。
我与街坊大声打招呼的时候,姐姐在一旁边听边笑,大概是笑我和梅镇人一样,说着又土气又俗气的玩笑话。来梅镇两月,姐姐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排场的酒席,所以我要稍稍提醒她:“姐,你别看梅镇平时静悄悄的,但这种场会吵得你受不了的。当心啊,不要一高兴就喝多了。有人给你敬酒,你不要听他起哄,一听你就会醉的。”
“我只是去看看热闹罢了。再说,我哪里会喝什么酒。对了,七婶也要去吧?”
“肯定有她,她算得上家里的长辈了。我告诉你吧,不仅七婶要幸去,七叔也会去的。”
“你胡说什么,七叔不是死了吗?”
“七叔虽然死了,但是梅镇人都记着他,现在,他差不多成了梅镇养蛛人的保护神了。逢年过节,谁家摆酒请客,都会把七婶七叔一起请去。所谓请七叔嘛,就是在七婶旁边摆个空凳子,再摆副酒杯碗碟罢了。大家都相信七叔的魂魄能在海底保护他们的珠蚌,因为七叔在世的时候,赤潮和菌虫从来没害过梅镇人的珠蚌。但他走的第二年,赤潮几乎把梅镇的养珠人全给毁了。告诉你吧,在梅镇的酒席上,除了七婶,谁能坐在七叔的那副空座位旁,谁就能得到七叔更多的保护,谁就可以养出最好的珍珠。坐不上的人,都会眼红呢!”
“那不就乱了,为了养出最好的珍珠,那个位置谁都会抢着坐啊。”
“乱不了,有七婶呢,她说让谁坐谁才能坐。”
“啊,七婶这么厉害!你怎么不早一些告诉我。”
“我告诉你怕你不相信啊,你在大城市生活,你哪里会信这些事,你会说这些都是迷信。”
“信不信的,这可不好说……”
话没说完,姐姐便有些着急地问我:“对了,谁坐过那个位置?你家男人坐过吗?”
“不是随便哪个人能坐在那个位置的。将近两年了,七婶不许任何人坐,就让它空着。之前坐过的两个人,发了财,早就离开梅镇了。不过,他们差不多是给七婶骂出梅镇的。在梅镇,谁都不敢让七婶骂的,七婶的骂,跟毒咒一样,谁被骂过,谁就会倒霉。”
“哎呀,你越说越玄,我听着都害怕了。”
“害怕了啊?害怕了好。姐,你知道吗,每次听你说去了七婶家,我都担心你别说错话,别惹七婶不高兴。你是一点儿都不明白,我们这些生活在梅镇的人,心里都有些怕她呢。”
“不对啊,那天你不是跟我说过,七婶是没什么大经历的。而且,这些日子我和七婶在一起,并没觉着她可怕啊。”
“不是可怕。唉,真是说不清了。七婶不是可怕,是所有人在她面前,都不能乱来,不能像你们大城市一样,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
07
说话间就到了地方,未进门,喧闹声便飞溅出来。
酒席已经开了。梅镇的酒席从不等人,客人随来随开,哪怕天黑,也要开到最后一位客人离去。
院中央已经摆开五桌酒席,对着正屋的那张紫红大桌,七婶端坐在首席,身旁像往常一样空着两个座位,一个是七叔的,另一个是谁都不能坐的。七叔座位前的酒杯和碗碟已经倒满了酒,夹满了菜。
我和姐姐夹杂在热哄哄的喧吵声里,被引入七婶坐着的那张紫红大桌。
与七婶打照面的时候,七婶正举着一根鸭腿吃得满脸是油。我照例大声夸了夸她的好精神,然后玩笑着说:“七婶啊,我们才来,你就已经把那盆鸭子吃掉一半。幸亏我们赶到了,不然连根鸭毛也见不着。”
我的话音一落,众人便跟着哄笑起来。七婶吃得满脸是油,被人一笑,更吃得津津有味。七婶嘴馋是有名的,但她从来不管别人说她什么。而且,我们都知道,七婶是从来不计较我们这些小辈跟她开这样的玩笑的,因为七婶认为,任何讽刺她能吃能喝的笑话,都是对她的夸奖,是在称赞她的身体结实。
七婶的牙毕竟有些松动,因此边吃边要剔牙。趁着剔牙的空当,七婶翻了我一眼,抬手指着姐姐说道:“那是你姐姐啊?她天天来跟我说话,你见我一次就要挖苦我。你们姐妹真是差得太远了。叫你姐姐来这里坐吧。”七婶说完,指了指七叔旁边的空位。
整桌人听到此话立刻停止了说笑,吃惊地望着我,望着姐姐,再望望七婶。有的干脆连伸出去的一双筷子都忘了收回,呆呆地钉在原处。我听完也像耳边炸了雷,愣住片刻,才从旁人的目光里确认自己没听错。
我担心姐姐招来闲话,便小心提醒七婶:“七婶,你忘了吧,我姐姐是外乡人。”
“我不是老糊涂,也没有喝醉酒,我说的就是你姐姐。快,快过来。”七婶用手招呼姐姐。
在众人的注视下,姐姐一脸的无措,她求救似地望着我,让我告诉她她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时,旁桌的人也安静下来了。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寂静箭簇一般飞向我,狠狠地扎进我的身体。也是那一刻,众人的不语让我感到姐姐似乎成了一个抢夺众人财富的罪人,成了整个梅镇人的仇人。有了这个想法,我突然怨恨起七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