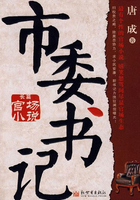尤苏斗不过妻子早霞,更斗不过那个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的父亲,虽然父亲看起来那么顺服和不堪一击,但他用他的衰老、缓慢、无言、执拗一次次地打败了时时想跟他计较过去的尤苏。
挫败感一时让尤苏忘了自己要去做什么,他怔在小屋门前,好一阵儿才反应过来,原本他是要去盛饭的。
母亲没在厨房,那只被她坐了一辈子的小矮凳在黯淡的光线里孤伶伶地摆着,暗褐色的凳面幽幽发着光。尤苏有些意外,母亲什么时间出去的,他竟然没有一丝觉察。盛面时,尤苏下意识地又看了两眼小矮凳,那幽幽的光似乎表明又有什么事物确实停在那儿。
尤苏甩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念头,盛完饭回到正屋,在茶几前坐下,继续吃面。
但纳闷了一会儿,他还是问了一句:“我妈人呢?”
正屋里就他和父亲两人,尤苏当然是在问父亲。
父亲慢条丝缕吸了一口面条,顿了顿气,说:“不是在灶间吗?”
“没在。”
父亲抬眼看了看尤苏,漫不经心地说:“没在能去哪儿?”
尤苏不愿再就这个问题与父亲说下去,只能闷着头吃面,闷着头自己不痛快。他责怪自己,弄不懂自己,为什么一生气、一不痛快他就看不见母亲?他想,母亲现在一定像父亲说的那样,低着头默默坐在灶间吃饭,像是从来没有移动过。谁都能确凿地看见母亲坐在那只小矮凳上,唯有他看不见。
母亲不在灶间能在哪儿呢?然而,此时此刻,唯有尤苏看不见母亲。
尤苏大口吸着面条,嘴里发出的响动几乎震晕了他的脑袋,有一个瞬间,他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他从什么时间开始突然看不见母亲的?是那次因为没把麦垛堆好而挨了父亲一顿痛打,还是另外一次因为一只橡皮和兄弟之间的一次恶斗?抑或那最恶劣的一次,父亲把母亲摁在炕角捶打,咚咚咚的拳头声像是把什么东西扔进了深井里,他们兄弟几个谁都没有上去帮帮母亲,而他也只敢在父亲夜里睡着后,拿着一块砖头站在父亲的床头。
是哪一次已经不重要了。尤苏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突然看不见母亲。每当他愤怒,或者感到疼痛和羞耻的时候,他总会突然看不见母亲。他记得有一年,自己在生产队听到母亲要被批斗的消息后,撒腿就往家跑,回到家后他红着眼睛满院子找母亲,却哪里都不见母亲的影子,可是母亲明明就站在灶前给另外几个兄弟盛饭;另外一次是母亲跑到表叔家,求表叔给尤苏一个工作的机会,尤苏知道后冲进屋子就对母亲爆跳如雷,但是母亲突然就在他的愤怒前消失了,他的愤怒因此不得不嘎然而止,接着就变成了诧异和惊恐。
是他的视力出了问题,还是母亲真得有从他眼前消失的魔力?为什么母亲只在他的眼前消失?消失的时候,母亲去了哪里?
也许是母亲在用自己的消失提醒他的愤怒、疼痛和羞耻。也只有母亲能这样迅速地告诉尤苏,他在想什么、干什么,并制止着他的愤怒、疼痛和羞耻。
尤苏默默守着这个秘密。因为在这个家里,话语多数时间都意味着泄露自己的软弱。
尤苏吃完第二碗面,他挑干净碗里的最后一根面条,起身去厨房送碗。
母亲好端端坐在她的小矮凳上,就像从来不曾移动过。
05
吃过午饭,雪停了。
母亲以她的消失又一次平息了尤苏心头的怨气。看着窗外渐渐亮堂起来的天空,尤苏的心情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缩了。那些游动在他体内的愤怒像暂时获得安全感的蛇,收回警惕的脖劲,虽然迟疑,却还是慢慢将身体放松了。
父亲去了院子,尤苏仍在沙发上坐着,没有父亲与他面对面的干坐,他的身体已经先于他的意识感到了自在与舒服。尤苏看看窗外,天空竟然亮得有些刺眼了,他搁在腿上的手像是自己弹了起来,轻轻点着膝盖。
过了好一会儿,独坐着的尤苏才意识到方才从他身边走过的父亲确实带走了他身体里的一些东西。但显然,父亲留下的东西更多,它们在他血液里,像一种惯力,推着他进入世界,进入自己的命运,永远无法被带走。它们已经成为了他。而让尤苏常常不痛快的正是它们。尤苏认为正是它们使他成为一个失败者,他无法与自己的同事建立一种游刃有余的关系,他无法使妻子早霞像只温顺的羔羊,他无法阔起来,他无法被幸运选中……一切不顺都与它们有关,与父亲有关。
每一次回家,尤苏都想问问父亲,为什么他不能给他一些别的东西?它们跟财富无关,却左右着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幸福。事实上,尤苏知道父亲回答与否都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岁月匆匆,永不回头,他的生命已经不会再有第二种可能。“但他至少应该认错!”尤苏觉得父亲认不认错这件事就像一块堵住水流的巨石,父亲如果认错,他的人生就会像一条水源充沛的溪流,欢腾地流动起来。然而,让父亲认错,尤苏又知道,这种想法甚至比搬开那块巨石更不可能。“我父亲是一个死都不肯认错的人。”大学期间,看着校刊上发表的怀念文章,尤苏试着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字,但每次写完这一行,他就无法再写下去了。与同学们那些美好湿润的记忆相比,他感到羞耻。
尤苏坐在正屋沙发上出神的时候,院门晃当一下被推开了。父亲正在院里修理条帚,见到来人,扔下手里的活儿,在衣襟上拍拍手,迎了上去。
来人递过一瓶鲜奶,与父亲寒暄两句,转身走了。
一个人坐着无聊,尤苏也来到院落里。父亲提着鲜奶瓶上的一节绳扣往屋里走,迎面碰上掀开门帘的尤苏。父亲直接把奶瓶递给尤苏:“给你妈。”
尤苏不知家里定了鲜奶,随口问到:“家里定鲜奶了?”
“给你妈定的。”父亲说完,转身走了几步,继续在阳光下修他的条帚。
尤苏眼皮嗒嗒跳了两下,有根极烫的激光一般的东西刺动了他。他握着鲜奶瓶,感受着鲜奶稠厚的温热。
母亲在另一间小屋的炕沿上坐着喝水,见尤苏拿着鲜奶进来,面无表情地说:
“给小宝拿去喝。”
“他有。你自己喝。这奶好么?”
“好,都说是给城里送得最好的奶。”
“嗯,怎么不多定点?”
“你爸不喝。”
尤苏没再说什么,伸手把鲜奶搁在炕前的一个方桌上。
院子里,父亲仍在修他的条帚,细铁丝绕来绕去,条帚眼看着越来越结实。
尤苏站在院里的一棵枣树下,点了根烟,抬头望了望枣树枝上几只麻雀,又估摸了一下时间,想到差不多该回去了。
怔怔站了一会儿,尤苏想起一件事,对父亲说:
“老二媳妇住院了,你们有空去看看。”
父亲坐在一只矮凳上,两腿夹着条帚,手里正绷着细铁丝。没带帽子的头发像堆倒塌的麦垛,剩下几缕倔强地伸向天空。尤苏话音落下好一会儿,他才不情愿地开了口:
“他们不是要离了吗?”
“就是闹闹,离什么离。”
父亲脸一沉不说话。阳光下,父亲脸上的皱纹变得更加清楚,一根一根,像他手里的细铁丝。
尤苏看了一眼父亲,见他半天沉着脸不吭气,心里有了不耐烦。他低下头猛吸两口烟,等着父亲开口。
父亲慢条丝理忙着他手里的活儿,良久,吐出几个字:
“我不管。”
“什么不管?”尤苏脑门上冒出火星。
“他们的事我管不了。”父亲声音小了些。
“没让你去管什么,让你去看看人。”尤苏嗓门大起来。
“……既然不管,还看什么。”父亲手里绷紧最后一截铁丝,话音有些吞吐。
先前未点燃的愤怒这时猛地被划着了。尤苏紧捏着剩下的半截香烟,手指把香烟的过滤烟嘴压变了形。
“你说你这像是长辈说的话吗?不管,什么不管,我告诉你,老二闹离婚你得负一半责任。老二打了媳妇,媳妇来给你告状,你说什么?也是说你不管。你说有你这样当家长的吗?老二媳妇闹了这么多年,心结不就在你这。你去看一眼她怎么了?难道会丢死你的人!?”
父亲手中的活儿在尤苏的斥责声里慢了下来,腰也随之垮下许多。尤苏说话期间,他没敢抬头看一眼尤苏。尤苏说完话,他的头低的更低了。方才照在他额头上的阳光,也就全落在那堆乱糟糟的头发上。
早霞听到尤苏在院里大声数落父亲,紧走两步来到院里,一脸吃惊地望着尤苏,上前推了一把尤苏,压低声音说:“你干什么?”
尤苏一把拨开早霞的手,声音比刚才又放大许多:
“你说你管什么?你管过什么?打不动了你就不管了,是不是!?……”
尤苏突然停了下来,他瞪大眼睛盯着父亲乱糟糟的头发,抖着嘴唇站在原地,那截没抽完的烟揉碎在他的手心里。
许多话卡在尤苏的嗓子眼儿,他握紧那只满是烟丝的手,没让那些话爆出他的喉咙。
虽然怒气未消,且心有不甘,但尤苏宁愿相信,剩下的那些话一定会要了父亲的命。
父亲蔫巴巴听着尤苏斥责他,听到最后一句,抬起头惊讶地看了尤苏一眼。尤苏感觉到父亲这一眼擦着他的头皮就过去了,根本没敢停下哪怕一秒钟。
早霞站在一旁觉着尴尬,拖着尤苏的一只手臂就往屋里拉。尤苏火气未消,猛得一甩,对早霞说:“拉什么拉,回家!”说完,尤苏大步往院门走出,咣地一声推开院门,一甩手走了。
早霞不知该说什么好,和公婆慌忙说了一声,拽着小宝紧跟着出了门。
54路公交车仍然等得让人心焦。
路边一个简陋的站台旁,早霞带着小宝站在离尤苏三米远的地方,既不敢靠过去,也没说一句话。
尤苏黑着脸一言不发,双手揣在衣兜里,攥紧拳头,纹丝不动站在站牌下,来来回回想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54路公交车迟迟不来,然而尤苏似乎已经忘了等车的事。
这样呆站了大约半小时,尤苏听到早霞说:“你妈来了。”
早霞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
尤苏抬头向来时的路看过去。那条路上空空荡荡,阳光照下来,看着有些晃眼。上午的雪迹已经没有一丝踪影。
尤苏什么也没看见。
尤苏估摸着母亲差不多走近了,问了一句:“你来干啥?”
“小宝的手套拉家里了。”
母亲的声音听着比早霞还遥远。
尤苏停了停,确信母亲又走近了一些,突然很迫切地想和母亲聊些什么:
“妈,我的眼睛不太好。”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是小时候落下的病。”
“妈,你去过什么远地方没有?”
“没有,我能去哪……”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