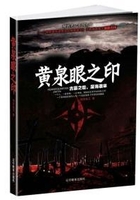马尔焉进了苏来茫家的果园,阳光刹那间变得五彩斑斓,空气突然又浓又湿,迎着阳光望去,果园里浮动着一层淡淡的雾蔼,仿佛一条缓缓流动的大河。马尔焉感到自己浸泡在一条果香四溢的大河里,河水穿过她的头发,她的指尖,她淡粉色的衣袂,所有的一切便染上了果香的颜色,这果香的颜色是怎样的呢?是一种浅浅的橙,时而朦胧如梦,时而明亮如月,染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就变成一条熠熠生辉的山间小溪,染在她的手上,她的手就发出珍珠的光润,染在她的衣袂间,她的衣服就像绸缎一样柔顺。果香还涤荡着她心间的浓浓阴翳,一团一团,慢慢地洇开它们,马尔焉深深呼吸着园子里的空气,有一瞬间,突然感到阴翳不再那么沉重了,半年来,她气喘嘘嘘的肺腑,第一次,蓦地有了一种想要飞升的欲念。马尔焉抬头看看结满果子的树枝,许多叶片已经泛起乳黄,阳光倾照下来,变得近乎透明,但马尔焉无法细加体察这种透明,因为她听到了狗叫,随着狗声,传来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这边是富士、金冠,里面有梨,你家往年多要苹果。”苏来茫站在五米之外说话,没有表情,然而目光闪烁。
“今年一样。”马尔焉皱皱眉,她对这个比她小两岁的苏来茫并无好感。
马尔焉觉得,苏来茫尖尖的下巴丝毫没有青春少年的质朴,甚至没有青春的鲁莽,仿佛早熟使他在一夜之间变得狡黠与谨慎。在村里的年轻人当中,苏来茫颇具号召力,虽然每星期总被母亲嘟哝着去上寺,但村里如果需要年轻人的力量时,总是请苏来茫来团结大家。去年的劳务输出便是一例,苏来茫无须出门务工,家里的果园和田地足够他发家致富,然而因为无人挑头,此事又关系乡、村的政绩,所以不仅乡村干部,就连寺管会主任,都来央请苏来茫给众人做出榜样,苏来茫便由最初的对抗,转为村里劳务输出成员的领队,然而事情不出预料,出去没有多久,苏来茫便扔下同伴独自返回了。村里无人为此说什么,苏来茫家那么一大片果园,收入自然比出外打工好过许多。
苏来茫尖尖的下巴上落了一块光斑,仿佛话音疲惫,一出口便无力地挂在了嘴边。马尔焉感受到了苏来茫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倦怠。
‘“这个年轻人的朝气去了哪儿呢?年轻人过早地呈现衰老之象,并不是一件好事吧。似乎更与这个园子不相符。要是换了哥哥,健康的哥哥会多神采奕奕呀!”马尔焉十分困惑,她难以想象令苏来茫像一堆虚土似地立在那里的缘由,她只是格外厌烦,平素与苏来茫即使照面也不会多语,此时这些困惑闪过脑际,令她突然萌生出一种虚弱感,她觉出自己的无力,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使她困惑的事越来越多了。
“你自己摘,还是拿装好筐的?”苏来茫问。
因为喜欢这园子里的阳光与气息,马尔焉想了片刻,决定自己摘果子。
竹筐在果园的茅棚里,果子成熟后,苏来茫一直住在那里看园子。马尔焉跟随苏来茫,往茅棚走去。茅棚里除有成筐的果子及空竹筐外,只一张凌乱的小床,淡青色床单,显得洁净,摊着一本杂志,马尔焉扫了一眼,尽为穿三点式,或什么也不穿的裸女和半裸女。马尔焉的脸顿时如火烧一般,手臂用了大力,猛然提起两个竹筐,用一种很莽撞的姿影出了茅棚,苏来茫似乎在她身后说了什么,但她什么也未听见。
仿佛与人赌气一般,马尔焉的脚步声与心跳声搅和在一起,撞开果园郁郁湿湿的空气,以及清澈明亮的阳光,一时之间,原本静寂的空气与光线,突然像投入巨石的湖水,在剧烈地晃动之后,就只是碎裂的残片了。
这样不顾一切疾走着的马尔焉忽然又停了下来,被推开的树枝在她身后摇摆不定,很欢欣的样子。马尔焉怔在一片没有遮拦的阳光下,她白皙的脸颊在微红里冒出了汗,攥紧竹筐的手指已经又滑又木,她猛地甩开手臂,竹筐便笨头笨脑地滚了几滚,翻倒在果园松软的湿土上。
马尔焉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暗暗蒸腾,扔开竹筐的手重又攥紧,目光呆滞,仿佛仇恨着什么,又仿佛在做着一个巨大的抉择。而此时,四面的静寂像一个傲慢的对手,凝望着她的目光,充满意味深长的笑意。
几分钟后,马尔焉从凝神中回转过来,她看了看萦绕在她身边的雾蔼,与进园时并无不同,依旧携着果香,缓慢地飘浮着,宛若轻纱,抚慰着她的身体与内心。只是对头顶的阳光,她有了微微惧意,那清澈与明亮的光线,实在不能对应她此刻的内心。想到这里,马尔焉迅速走到一棵果树的阴影下,好似躲避什么,在树下站定后,她扶正翻倒在地的竹筐,一边摘果,一边想:“这是夜晚该多好,月亮柔软的光华,不是太阳这样严厉而猛烈的。”
马尔焉心里正想着的事,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口的,也是不能被人所知的。
五月里的一天,她忙完地里的活回家,一进院门,一股腥膻的气味便迎面扑来,犹如一阵昏黄的阴风,这怪异而不详的气味即刻卡住了她的咽喉,她不得不紧紧捂住鼻子与口唇,因为如果动作稍慢,她会不可遏止地呕吐起来。但马尔焉皱紧了眉头,十分惊异地,随即开始四处寻找这个丑恶的气味。
几分钟后,马尔焉终于在院里端,一堵半塌的土墙后,看见了令她恐惧的一幕,母亲带着白口罩,一只手抄着锅铲,一只手如她一样紧紧按住口鼻。锅里黑乎乎地躺着拳头大小的一块东西,形状丑怪,马尔焉看了一眼便觉得胆战心惊。马尔焉的出现,吓坏了全神贯注的母亲,母亲啊的尖叫一声,甩掉了手里的锅铲,惊乱的样子像遇见了鬼。然而母亲又很快镇定下来,极快地做出了反应,表情凶猛,用尖厉的嗓音训斥马尔焉:“快走,别看,死妮子,赶快走!”
母亲后来把这块又黑又丑的东西研成粉末,然后一粒不剩地装进那些红白相间的空胶囊,再端着水杯,每日按时按点,让哥哥服下这些来路不明的药粒。
最初母亲一直不肯说明原委,眼神里跑动着令人忧惧的慌乱,仿佛被吓破了胆。后来在事情越发不顺的情况下,在一次筋疲力尽的奔波后,母亲绝望地向马尔焉说出了一切。那是三个月大的母腹中的胎儿,是千辛万苦求来,给哥哥冶病的绝密偏方。
马尔焉心猿意马地摘着果子,苏来茫床上摊开的杂志解开了她这些日子以来内心的臃塞。她一直想为哥哥做些什么,此刻她斟酌再三,觉得苏来茫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她决定自己要赶快跟苏来茫好,再做那件事,那样哥哥就有药吃了。
这样剧烈的思索,使马尔焉感到一种亢奋,身体重又蒸腾起来,丝毫感觉不到悲伤,甚至一抬头,就望见了大病痊愈的哥哥:哥哥在澄澈的秋阳下,果实累累的季节里,正神采奕奕地向她走来。
04
苏来茫不知道马尔焉为什么拒绝他的帮助,他记得往年,四轮车把果子运回马尔焉家时,马尔焉的母亲总要请他进屋喝茶,但被苏来茫拒绝。
从第二天起,马尔焉每天只摘一小筐果子,摘得十分仔细,动作轻缓,倾注了对果实由衷的喜爱之情,每摘下一枚果子,便用一张正方形白纸将果子包裹好,一个一个码放在竹筐里。苏来茫从一旁打量马尔焉的举动,觉得自己是在窥视一个秘密制造者,凡经此人之手,那些佳美的果子均变为一个个未解之谜。
马尔焉郑重其事的样子让苏来茫感到好奇,对卖家而家,这种挑选方式会令人不快,马尔焉仔细又挑剔,摘选的都是每棵树上大且漂亮的果子,这些果子如果送往市场,价格自然不菲,然而,苏来茫却为此感到微微地快慰。橙黄或桔红的果子,汁液甜爽,气息甘美,无论挂在枝头,抑或摆放在竹筐里,均散发着一种静谧的喜悦,和一种暖融融的期待。马尔焉细致入微的动作,心无旁焉的神情,渗透着格外的珍重与爱护,苏来茫站在一旁,第一次感受到了果园的富足,果子的美好,以及劳动的自豪。
最初马尔焉也拒绝苏来茫帮她摘选果子,表情十分严肃,每天来到果园,先往茅棚去,取一个竹筐,与苏来茫打声招呼,便独自到了果园的一个僻静处,用绣花似地细微,缓慢地采集满小半筐便架在自行车上,自己带回去了。但不出三天,苏来茫就搭上了手。
“你家往年不是这样买果子的。”苏来茫摘下一枚又红又大的果子递给马尔焉。
“往年都是妈妈来买,她哪有闲工夫。我退了学,时间多。”马尔焉的声音很柔和,脸上却没有表情。
“听说你哥最近好一些了。”
“谁说的?”
“你妈,她说你哥吃了一种新药。”
“是比最初有些精神了。”
“药一定很贵吧。”
“不知道,都是我妈妈买的。”
“你还上学吗?”
“哥哥病好了我才能回学校。”
苏来茫心里是些畏惧的,马尔焉显然与村里其他女孩不同,哥哥是医科学生,她也考上了专科学校,而他高中还未毕业,就跟着亲戚四处跑生意了。对于有学问的人,苏来茫虽然表面无动于衷,私底下却十分敬佩。关于马尔焉的理想,苏来茫觉得那是一件高不可攀,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绝不敢出言不逊,甚至用不好的念头想一下都是要遭诅咒的,这与平日里上寺拖拖拉拉没有关系,如同他爸是他的老子一样不容置疑。
因为马尔焉的理想,在此之前,苏来茫几乎未用青春少年的目光观察过马尔焉,相互接触也是因节日之间必要的走动,比如宰牲后送几块熟肉和一个油香,然而,这两日在果园里的相遇,及简单的交流,使苏来茫从最初的敬佩与疏远,急剧地又增加了一些朦胧的亲近感。若说美丽,马尔焉不及杂志里的女人,但马尔焉说话时眼睛里飘出的扑朔迷离,意犹未尽的样子,太耐人寻味,这与马尔焉的皮肤呈现出的白皙稚嫩有些不符,这种皮肤只会使人联想到单纯与透明,然而正是由相反的性质组合在一起的这个特征,使得苏来茫莫名其妙地开始想入非非了。
九月结束的时候,苏来茫在那本杂志的一个空白处,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马尔叶,200斤,来果园10次,说了6次话,皮肤像平果皮,很滑。
苏来茫对自己的记录很满意,丝毫没想到错别字的事,他常常回想一个镜头,他粗壮的胳膊提起竹筐,竹筐里码放着被白纸悉心包裹好的果子,马尔焉紧随其后,他们一起往园外走去。能与马尔焉这样的女子齐心协力做一件事,村里除了他恐怕没别人了。
十月天早晚略有寒意,果树的枝条已经空空荡荡。秋意渐浓,黄昏暮合时,一种巨大的空寂感游荡在园子里,落叶正在悄无声息地腐烂。果园湿气重,夜晚更凉。仅剩一些未运出的果子,过几日,待买家取走,苏来茫便也要回家住了。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一人在黑屋里独坐了许久后,马尔焉躲过母亲,轻手轻脚出了门。
马尔焉走在路上,脚步慢慢吞吞,很迟重的样子,全无少女走路的绰然姿态。她穿着一件很厚的毛衣外套,淡蓝色,出门时,她突然觉得很冷,便转身回屋加了衣服,暖意立即涌上,仿佛喝了一口镇定剂,很快止住了身体的颤抖。走在路上,她一直观察着廖廓的天幕,墨蓝里透显威严,没有月亮,是她掐算好的,她细细研究过月相,所以选择黑月这天出门。
“最好又来了云,把星星也遮光。”
马尔焉觉得天不够黑,美丽繁重的星辰闪得她心意烦乱。她手里握着电筒,出门后打开,但立刻又关上了,一路再未使用。她记得看见那一小束光的时候,心里极为惊怕,甚至冲动地想扔掉电筒。但随即想到,手里握着它,要比手里什么也没有强出许多,因为手里空空,太令人感到无助了。
“最不济,能用它打一只野猫。”思忖到这,路边树林中猛地窜出了一条黑影,在路中央倏忽一闪,伴随着一声落慌而逃的惊叫,便消失在林木深处了。马尔焉闻听猫声,虽然惊出一身冷汗,却并没有扔出手电筒,事情总是这样,想象与现实出入很大。
正走着的马尔焉突然停了下来,对着月亮消失的方向,她慢慢跪下了,身体前倾,嘴角微微蠕动,而后低下头,几分钟过去了,马尔焉并未像往常一样,眼泪很快地流下来,泥土未曾接到她的眼泪。
“苏来茫会有什么反应呢?那本杂志被他翻得那样破烂了,对女人一定很老练吧,他会迫不及待的,希望我变成杂志上那些不穿衣服的烂货。”马尔焉知道,是这件事分去了她内心的虔敬,想到这里,鼻腔里才有了一丝酸楚,但仍是没有眼泪流出。
马尔焉坚定地站了起来。
果园黑黢黢的轮廓依稀可辨,一路上草木里的虫跳、怪异的鸟鸣,以及那只发出惊叫的猫,让马尔焉几乎惊慌失措了,所以,当看清果园里闪动的一星点灯光时,马尔焉的脚步加快了许多。
苏来茫的狗认出马尔焉,停止了狂吠。
马尔焉看着苏来茫的时候,发觉事情并非如她想象。苏来茫很怕她,丝毫没有一点接近她的意思,甚至连看一眼都不敢,就仿佛眼前站着一个可怕的幽灵,被对方施了魔法从而无法逃脱。苏来茫呆立着,手足无措,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愣了许久,才磕磕巴巴挤出一句话:“你找我有事啊。”
马尔焉听了很生气,血已经涌聚在她的脸上。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马尔焉盯着局促不安的苏来茫,停了片刻,她生硬地开了口:“过来,抱住我。”
茅棚外,湿寒的夜一点点走向深处,天幕不知不觉布满了黑云,繁星尽数匿迹,天黑得像不曾有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