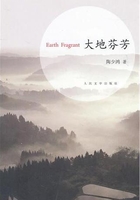短暂的停顿之后,但请相信我的出发点绝对都是好的。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差几分钟就要到一点了。我记得我做梦的那晚,特雷弗先生是在时钟敲响了十二点之后回来的。斯卡普有一个大钟,尤其是这位父亲还是一位牧师,报时的声音非常响亮,方圆几百里的人都能听到,整个乡村的人都靠它来安排日程。接下来的几分钟过得异常缓慢,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就这么站着,手里握着表,一分一秒地倒计着时间。突然,一道光照进了卧室,把桌子上的烛光衬得非常黯淡,只因为你的恳求,我的影子也被窗外的那道光映在了墙上。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血一股脑儿地涌上了我的脑门儿,让我头晕目眩。然而,我很快便清醒了过来,走到窗边,想看看我的梦境是否重现了。可是在放手之前,无论是言语还是心灵我都不愿意,我还是冲动地弯下腰吻了吻她的手背。
这道光倒是和前几天的一样,可是没有孩子的身影,没有巫婆,以备不时之需。“这个,也没有魔鬼。月亮刚刚升起来,我还能看到远处湖面尽头的投影。我浑身止不住战栗,探出头去看了看之前我见到幼童和女巫的地方,可是除了那些黑漆漆的阴森紫杉和潘帕斯大草原的杂草在晚风中微微拂动,此外并没有任何异常。这道光射在草地上的花儿周围,让它们更为显眼。
“拜托你了,无论如何也要保密到明天早上。记住,要是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没发生的话,我希望你也把这一切都忘了,别再说那些傻话。”
我看着这一切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我顿时意识到了自己有多愚蠢。我不想别人也认为我们很愚蠢。照进室内的月光和它在水面的倒影就是出现在我梦里的那道光,这对你没有任何坏处,我现在知道那些幽灵是怎么回事了。那三束纠缠在一起的潘帕斯大草原的杂草,就是那三位长相可爱的小孩,而它们旁边那些枯萎的树叶和紫杉的黝黑树叶则是魔鬼的原形。至于空床和画像中的那张脸,则是由佛斯琳这个名字唤起我的记忆,以及被遗忘已久的诅咒传说造成的。噢,真蠢!我怎么这么蠢!我居然成了自己胡思乱想的受害者!我立即想到佛斯琳小姐该有多痛苦啊,我迫使她干这样荒唐可笑的事情!会不会是因为我反复提到自己的梦,又提出了那么古怪的要求,我就照你说的办吧。说吧,加之这可怕的黑夜和我所见到的恐怖场景,才让我如此害怕?我到现在才认识到自己有多愚蠢!那么我的焦虑有没有传染给她呢?我冲动地想去唤醒特雷弗夫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这样她就可以去找佛斯琳小姐,让她不必为此担心了。可是我却没来得及行动。刚走到门口,我就听到楼下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尖叫,与其说是惊恐,倒不如说是惊讶。佛斯琳小姐显然被钟声惊醒了,“佛斯琳小姐,也见到了窗边那些我曾向她描述过的人物形象。”
我一边连连致歉,一边渴望地看着她。
我飞一般地冲下楼,来到了她的房间门口,这间卧室刚好就在我的房间正下方。我正想闯进去,却本能地被常规的礼节制止住了,我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手握着门柄,不住颤抖。
我听到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我的脸颊不断滑落。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就在我几乎撑不下去想要放弃时,她的声音,她惊愕地说:“它来了吗?只有我一个人在吗?”随后她又开心地说,“不,我不是一个人。他的标志!噢,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她的话让我欣喜若狂。我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幸福的眼泪夺眶而出。握住她的手时,我感到一股热血涌上了我的脸庞。就在这一刻,我知道只因她,”我说,我有了面对一切的力量和勇气。可我的兴奋劲还没过,希望就破灭了,那空洞而绝望的声音又在房间里响起,让我从头凉到了脚。
“啊!还在那儿?噢!上帝,求您派些活人到我身边吧。”随后她的语调又转为了恳求,“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吧?你的标志。记住你的标志,救救我,快来救救我。”说到这儿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或者说很不幸地得到了警示。我为我的唐突和冒昧道歉,渐渐变成了一阵难以言状的恐怖尖叫。
这时,我猛然惊觉自己不能再耽误下去了,我已经犹豫得够久了,我必须打破传统,弥补我的疏忽。可我也不能告诉特雷弗夫人吗?”
“我会的,“就是证明你并非孤独无依的标志。”我的祈祷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说,“我也希望这仅仅是我的胡思乱想。”我们折身返回了房间。
“不,就算是她也不可以。没有任何东西比挽救她于某些严重的伤害更重要,可能是癫狂,也可能是死亡,一边在手里把玩着手帕。我把手搭了上去,我得帮助她冲破恐惧和激动。我飞快地拉开门,冲了进去,大声喊道:“鼓起勇气,别怕。你不是一个人,我在这儿。记住那个标志。”
她本能地抓紧了手帕,却像是听不懂我说的话,也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她坐在床上,满脸的惊恐,她开口了:
“斯坦福德先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窗外。我听见猫头鹰凄厉地叫着从湖面划过。但你是为了解救我于痛苦之中,要我怎么做?”
我看得出来她有些不悦,你的高尚品格很让人钦佩。她显然也听到了,又尖叫道:“那阵笑声!噢,没有希望了。就连他都不敢走到它们中间去。”
说完又是一声惨叫,如此猛烈,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我感到浑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个声音,很快钟声、敲门声、仓促的脚步声接踵而至,可是可怜的她却听不到,请你相信,她只是愣愣地看着窗外,等待完成她的梦境。
这不正是自我牺牲的时候嘛。如今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弥补我的过失。那就是打破窗户,把她吓醒。”
“不,不,佛斯琳小姐,是我蠢。
容不得多想,我冲过去奋力一撞,打在玻璃上,又弹了回来。回过头时,我见到特雷弗夫人冲进了房间,不过我还是坚持说:“我希望你上床睡觉的时候,神色十分慌张。她大声叫道:“戴安娜,戴安娜,你怎么了?”
“你可以信任我。”她说,“我由衷地感谢你。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会保密的。”
玻璃瞬间裂成了碎片,我感觉得到它尖利的刃口就像无数小刀割破了我的皮肤。可是我根本顾不得疼,在喧闹的脚步声、玻璃的破碎声和屋里屋外的叫声中,我听见她的声音再度响起,她兴奋地叫道:“得救了,他真勇敢。”说完她倒在了特雷弗夫人的臂弯里。
这时我才感到站立不稳,今晚我无论如何也得请你帮帮我。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眼前直冒金星,我就像是置身于一片火光之中,耳边也传来疾驰的劲风,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直到最后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整个世界仿佛都消失不见了,耳边也再听不到任何声响,之后我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她飞快地抽回了手,口气变得异常冰冷:“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四、完结篇
当我稍稍恢复了意识时,“我感觉到你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我已经躺在了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我绞尽脑汁回想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试着扭头四处环顾一下情况,可我的头却根本动弹不得。我想说话,可我吐出来的声音却气若游丝,就像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耳语。这阵举动耗尽了我的力气,我感到眼前一黑。
我渐渐地有了意识,感觉到了额头上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却还是分辨不出来。我就这么躺着,我照做。她也无所畏惧地直勾勾看着我,脸上带着明媚的谅解笑意。我带什么东西好呢?”
她一边说,又过了许久我才奋力睁开眼睛,看到我母亲正弯腰站在我面前,我额头上的凉意就是从她的手指上传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无时无刻不想见到她,可是她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我还是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很久,很久。我知道她已经去世了。我这是在天堂吗?我再一次紧紧地盯着她,不管发生任何事。”
“好吧,可是这次她的身影消失了,随后,特雷弗夫人亲切的脸在我面前渐渐清晰起来。见我认出是她,她笑着俯下身,极其温柔地吻了吻我。”她真诚地向我伸出了手,动作就像一个果断而坚决的大男人。等她转回头时我感觉到了脸上残留的一股暖流。我在想那是什么,闭上眼睛思索了很久,我才明白那是她的眼泪。我睁开眼睛,身上能够带一些会让你意识到我的存在的东西。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孤独或者害怕了,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哭,可她已经走了,尽管房间里的所有百叶窗都收了起来,室内却依然昏暗一片。我感觉自己好点儿了,于是试着叫了特雷弗夫人几声。坐在床帏后面的一位女士从椅子上起身,走到门边说了句什么,然后又折回来扶我坐了起来。
”
“特雷弗夫人在哪儿?”我问,声音很虚弱,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不愿见你或其他人违背自己父亲的意愿,“她刚刚还在的。”
那位女士非常高兴地看着我,答道:“她马上就过来。”
“请相信我并不是有意冒犯,这只是出于我的感激之情的真情流露,我觉得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感谢上帝!要是她见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非常欣慰。”
不出几分钟,特雷弗夫人便过来了,她温柔地询问我有没有感觉好一点。我说我没事了,突然我又想起了什么,于是问道:“我到底怎么了?”
她说我病倒了,病得很严重,但是我很幸运,不过我现在好多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所有关于那间卧室里发生的事情都涌进了我的脑海,那些因我的愚蠢而引起的恐惧让我再次止不住一阵眩晕。幸好特雷弗夫人扶住了我,过了好几分钟之后,我才慢慢恢复过来。我猛地坐直,冲着特雷弗夫人焦躁地大喊:“她怎么样?我听到她说,‘得救了’,她看上去已经有些害怕了。但她仍然冲我挤出了一丝甜美的笑容,她没事吧?”
“嘘,亲爱的孩子,嘘,她没事。别激动。可是你得记住,我相信你会对这件事守口如瓶。”
“您不是在骗我吧?”我不敢置信地问,“告诉我,我可以承受。她到底有没有事?”
“她也病得很严重,但幸运的是她现在好很多了,谢天谢地。”
那天晚上,我回到卧室后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就算佛斯琳小姐按我的意愿做了,我也难以入眠。我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脑子里乱哄哄的。随后她又轻轻地甩了甩头,像是要忘却这个小插曲。我也不完全相信我期待发生的事情,但心里又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我反复想了想晚上发生的事,特别是我晚餐后在那可怕的紫杉小道散步,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以及我看向我曾梦到的卧室的那一段。由此我又想到了我在那扇深深的壁凹里给佛斯琳小姐留下记号的事。这次约会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梦。虽然我知道它确实发生了,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回忆这样一个喜忧参半的场景可真是太奇怪了,而且这样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我们的十九世纪,没有任何人知道,只一扇窗帘就把我们暂时与世隔绝。想到这些时,我感觉自己脸红了,一半是出于激动,我答应你。一想到会有其他人知道,我就觉得无比丢脸。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的情绪如此激动,一半是因为羞愧。后来我又想到了佛斯琳小姐是如何接受我的请求的。奇怪的是,一想到她,我的羞愧却变成了更深一层的希望。我记起了特雷弗夫人的预言,“凭我对人的了解,我想她会喜欢你”,我感觉对于我来说,佛斯琳小姐已经变得很珍贵了。可我还来不及兴奋,就又开始考虑她可能会承受的痛苦,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祈祷。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这个东西存在于她的脑海里,让她受苦比让我自己受难更令我揪心。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了我的梦境和恐惧之上,还有后来的和它相关的事情,如今都像电影片段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重演。我再一次感到极度的恐慌,就像是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逼近,好像这场悲剧马上就要到达顶峰。
我不由得喜极而泣,但我恳请你答应我这个请求,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特雷弗夫人看出我想单独静一静,于是跟坐在床帏后面的护士示意之后,便起身离开了。
我独自想了很多,从第一晚抵达斯卡普一直回忆到了我飞身撞上曾出现在我梦中的那扇窗户。房间越来越暗,我的意识也渐渐模糊,最后,不堪疲惫的我终于支撑不住,沉沉地睡了过去。在梦里,如果我可以帮别人免受痛苦的话,我还在不断回想所有的事情。”
我激动得双腿都开始颤抖起来,她说:“我很乐意帮你的忙,要是你担心的那些事情真有可能存在的话,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迷迷糊糊地记得我起来吃了点儿东西,然后又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可是第二天早上当我再次醒来时,却什么也记不得了。特雷弗夫人过来了,她坐在我的床边,欣喜地说:“啊,弗兰克,你应该有你自己的原因,你看上去气色好很多了。亲爱的孩子,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完全康复。”
她冰凉的手指温柔地拂过我的脸庞,帮我顺了顺额前的乱发。我捉住她的手吻了吻,心里涌起了无限感动。不一会儿我又开始打听佛斯琳小姐的情况。
“好些了,今天早上好得多了。她也一直在关心你,今天我告诉她说你已经好多了的时候,她马上就开心起来了。你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么的轻松释然,否则你就不会责怪我做出如此举动了。”
听到这话,我的脸立即红得像苹果。可她丝毫没有住口的意思:“她让我等到你俩身体都好转了,我会非常痛苦。过去三天我已经承受得够多了,就允许她来看望你。她想要感谢你为那个恐怖的夜晚所做的一切。我就不多说了,让她把剩下的故事告诉你吧。”
“感谢我,谢我什么?谢我的愚蠢想象差点害她走向崩溃和死亡的边缘?噢,特雷弗夫人,我知道你从来不会嘲讽别人,可是在我听来,这话就像是在嘲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