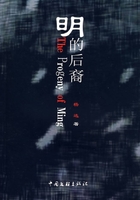她回过头,看见景兽的笼子,奇异地,他的绿色斑纹在夜晚发出桃红色的瑰丽光芒,微微照耀着他的脸,让他看起来像一个英俊而忧伤的小丑。她忘记了哭泣,不由自主地向他走过去,问他说:你是因为这些美丽的斑纹所以叫做景兽吗?
兽笑了起来,他说,难怪你会被发配到动物园来当管理员,大学考试没及格吧?问这种不着调的问题。
姑娘有些恼怒,她说,你懂什么,你根本不在我们考试重点之列!
虽然如此,她却清楚地明白,兽的名字不会是这样来的。对于那些庞大的兽族来说,他们的来历都有着详细而冗长的记载。悲伤兽是古代诗人的后代,荣华兽往往成为帝王的园丁,而最为神秘的舍身兽,传说甚至是远古时候的神明——但景兽……你能告诉我吗?她问。
兽半晌没动,在管理员要离开之前他终于开口了,他说,景兽是古代将军的后代。
——景兽从东方来,是古代将军的后代,将军拯救了所有的军队,生,为景,故名景兽——管理员终于想起《动物学概论》里面,有过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
她想要开口说话,但兽打断了她,你要吃巧克力吗?他执著地问,白天有个孩子给我的。
他们一起吃了那块巧克力,一块廉价的巧克力,甜味很重,包装的金箔纸发出巨大的声响。兽把巧克力递过来的瞬间,管理员触到了他的掌心,那里面都是密密的倒刺,她一惊,很快缩回了手。
送巧克力的孩子就是那个画素描的孩子,他除了每天跟着管理员在动物园乱逛,还会送给景兽一些吃的。兽和他终于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常常隔着笼子坐在一起,埋着头各做各的事情,不时说两句话。
兽说,你为什么老是待在我这。
孩子顺口就骂了一句脏话——跟着管理员越久,他知道的脏话越多了。
兽并不介意,反而笑了一笑,埋着头,继续看书了。
管理员送午饭过来就看见他们两个这个样子,她哭笑不得,对孩子说:干脆我把你也关进笼子和他做伴好了。
他们三个聚在一起吃了午饭,同往常一样,这里依然是动物园中最安静的角落,不远处,两头舍身兽互相撕咬着对方的身体,发出阵阵怪吼,一群孩子兴奋地围着他们的笼子,把乱七八糟的食物丢在他们身上。管理员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吃了一口鱼香茄子,忍不住问景兽说:你为什么不表演一些节目让孩子们多看看你呢,他们会送你很多东西的。
——这次轮到兽骂脏话了,他头也不抬,说:去你妈的。同时,吐出了一根鱼刺。
孩子坐在管理员身边吃着属于他的午饭——他从包里摸出几个面包和一包牛奶,他问管理员:你要吃巧克力吗?
姑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昨天吃过了。
那个下午,孩子异常沉默,但除了孩子自己,没有人发现这一点,他们两个一起在动物园里面走着,不时有孩子过来问路或者买纪念品,然后在他们面前分散开来。
对于没有见过动物园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怪异的景象。在树丛或者花台的间隙中,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铁笼耸立着,兽们安分地待在里面,玩着分配给他们的单杠,铃铛,吊环,或者别的玩具。孩子们在他们身边欢快地奔跑着,或者同他们说话,甚至在一起唱着少先队队歌,其乐融融。一个面容惨淡的姑娘推着巨大的手推车在孩子中穿行,是画面中最让人熟悉却又格格不入的事物——但是,对于熟悉着动物园的人来说,这一切,是那么的悲伤。
因此,那个孩子跟在管理员后面,突然拉住了她的衣服。她停下来,低头看他,她说,你怎么啦。
孩子欲言又止,最终说:你要吃巧克力吗?
姑娘无奈地看着他,笑了,她说:好吧好吧。
——他到底还是个孩子,因此变得心情好起来——当天晚上,姑娘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睡在她身边的孩子自言自语地梦呓说:你要吃巧克力吗?
记得动物园的人已经很少了,记得动物园失踪之前那些日子的人早已经死了。因此他们永远也不会告诉人们那个管理员的故事,告诉人们她虽然不美,却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她坐在台阶上,把头埋在膝盖里深深呼吸,优美雪白的脖子像鹤一样起伏着。
景兽看着这个属于姑娘的形象,继续做着引体向上,阳光照射下,他的身体投下淡淡的、半透明的影子。
他对姑娘喊着:你最近吃什么了,怎么越来越瘦?
但她置若罔闻,肩膀坚挺地不动,然后,急剧颤抖起来。
兽看着她,保持着上下起伏的动作,几乎听不见地,叹了口气。
夜晚来临的时候,孩子入睡了,动物园像深海一样平静。管理员最后送完了宵夜,骂骂咧咧地在笼子前坐下来。景兽看着姑娘,问她说:你想离开这里吗?
她说,是的。
她说是的,我想离开动物园,离开永安城,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母亲在那里等我回家。
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没有钱念大学,考永安大学动物学专业时,就签订了合同,要在动物园做满一年管理员才可以。
兽几乎是冷笑了一声。
管理员问他,你笑什么?
兽说:你不会回去的。
永安是一个大城市,各种各样的人来了就不愿意回去,它那么繁华,有高大的楼宇和富有的建筑商,有大人和孩子,有将成为达官显贵的幸福的孩子和成为流亡者,绑匪,妓女,甚至成为艺术家的不幸的孩子。从三环到五环,再到六环,毫无疑问,最终有一天,永安会成为一个最大的城市,成为一个同国家一样巨大的城市,再占领整个漂浮在海上的陆地,因此,连动物园中的兽也明白,没有人可能,或者愿意离去。
管理员理了理刘海,她说,可我怕一个人在这里。你不害怕吗,你也是一个?
兽说,不是的,以前我们有两头,你来之前,死了一头。
哦。她说。
喂。兽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即使穿着厚厚的毛衣,管理员依然敏感地感觉到他掌心的倒刺。她一缩肩膀,转过头去,问兽说:怎么?
兽说:我可以吻你吗?
她眯着眼睛看他,一层温柔的桃色光芒笼罩着他的脸,她迟疑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好的。
她闭上眼睛,没有看见那个孩子,但兽看见了,孩子在远处的推车后面,小脸绷着,等着她,灯为他投下寂寞到几乎看不见的影子。
那一天晚上,不仅是那一头寂寞的景兽,所有的兽都闻到了空气中不安的气息——冬天就要来了!冬眠的兽在储备着最后的体力,而醒着的那些在盘算怎么度过这个漫长而空白的季节。
他吻了她一会,甚至大胆地伸出手,抚摸着她的身体,铁栏杆冰凉地贴着他们的脸。远处一头悲伤兽的鸣叫让她浑身一颤。她觉得一阵虚弱,好像身体里面所有的器官都在萎缩。她抬起苍白的脸,问景兽:我会死吗?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兽笑了,他说,你不会死的,只是冬天要到了,你可以睡得久一些。
直到动物园中迷路的孩子越来越多,兽们才发现,管理员失踪了。但最晚知道这个消息的注定是那些骄傲的兽——他们有来自游客的食物,永远不会觉得饥饿。但寂寞的兽们早早发现了管理员的消失,在舍身兽的笼子对面,那头景兽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似乎陷入了土地。
一头舍身兽,用被自己咬得血淋淋的双手抓在栏杆上,问他说:喂!你要吃巧克力吗?
他毫无响动。
几个孩子跑过来看他,发现他还活着,发出缓慢的呼吸。他们看了看牌子上的名字,大声叫他说:景兽!景兽!
他依然一动不动。
他们扔石头去打他,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快起来给我们讲个故事,不然我们一起玩木头人的游戏好吗?接着,一个孩子惊叫起来:他的眼睛!他的眼睛!
兽的眼睛中流出了气味浓烈的绿色液体,孩子们吓得跑开了。
过了两天,动物园里面完全乱了套,兽们惊恐地走来走去,问每一个孩子说:你们帮我们去找找管理员好吗,我们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同她最亲密的那几个开始骂脏话。
但那头景兽依然躺在地上,肚子渐渐隆起来,像一个孕妇。
动物园失踪之前一天,那个画画的孩子终于出现了,他长高了很多,看起来像一个大人了,但脸上依然带着忧伤而倔强的表情,皮肤上有着淡色的绿色斑纹,站在笼子旁边,静静看着躺在地上的景兽。
他叫他说,喂。
他终于张开眼睛,颜色疲倦,他说,我要生产了。
我知道。孩子翻个白眼,骂了一句让人熟悉的脏话。
在动物园失踪前一天,去了的孩子们都听到了人生中最多的脏话,很明显,管理员的不良习性传播得很远,以至在很多年以后,这些孩子长成了大人,他们成为了永安城历史上最喜欢骂脏话的头头。随着景兽的腹部隆起和浑身发出的恶臭,敏感的兽们被触动了最脆弱的神经,他们抱着头走来走去,或者沉默,聚齐在一起焦虑地对望,再也不逗孩子们开心了,除了管理员,所有的兽都在等待新的管理员或者园长的出现,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出现。
兽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自己被抛弃了,不久以后,这一块最后的绿地就会成为新的商业用地,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而他们会成为童话书的传奇。
但这一切,都是幻觉。
到了下午时分,一队穿着黄色工作服的人出现了,他们给兽们送去了食物,帮助他们打扫了笼子,在园内各处出没,忙碌着什么。一组庞大的车队开进了动物园,里面有建筑工人,医生,教师,警察,还有上头来的红头文件。
景兽的笼子终于被打开了,几个医生冲进去,翻看他的眼皮,捏他的手腕。
奇异的是,这一切都是在静默地进行着,无论是孩子还是兽们,都像神灵一样,默默地注视着这些有序的忙碌。
那一晚,兽们都睡了一个安稳觉,即使冬天的气息已经在鼻子上,动物园中的草木发出萧瑟的声响。画画的孩子依然没有离开,他同景兽睡在同一个笼子里,就像管理员曾经说过的那样。
景兽抓着他的手,挺着肚子,不时发出痛苦的喘息。
天亮以后,动物园就失踪了。
它的确是失踪,因为永安市民没有人觉得它消失,他们总认为,动物园还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只是它太深,又太广,潜入以后,只得绵长安静地呼吸。
那些艰难的时候终于过去了。
老人们在动物园中度过了他们最后的童年,接着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孩子,关于他们同动物园的照片被保存在市政府的某个秘密资料库中,只有拆毁了动物园的人才能看见。
兽们,依然生活在现在的永安,他们可能是新的纺织工人,大学教师,医生,包工头和监狱长。他们有自己的房子,社区,寺庙或者教堂,可以有选择地同人类通婚,进任何医院看病,购买特效药,甚至接受极为机密的改造手术。一个永安市民永远不会对在街上擦身而过的一头兽多看一眼,无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或者鼻头上刺出尖锐的兽骨。他们对他们毫无兴趣。兽们见不到孩子,迅速就老了,老了以后,躺在养老院中,问扫地的清洁女工:什么时候吃饭啊?
女人很粗暴地说,我不知道。
他将在几天之内死去,平静地死去,服用药物,不再生育。他曾经是那个画画的孩子,现在是一头年老的景兽。他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很多动物园的故事,但对于他来说,动物园的故事以及失踪毫不重要,对他而言,重要的是那个最后的女管理员,以及他缓慢吸食她内脏的夜晚,同他的同类一起,把她最终吃掉的夜晚。
但他将骄傲地把这些带进坟墓,在永安大学生物系动物学的任何一本专业图书上都只能找到关于景兽的简略记载:身生绿纹。有短尾。掌生倒刺。性狡。稀缺。他们是古代将军的后代。景门为生。
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是饮血食肉的胜利者,幼兽饮人血才能长成,成兽食人肉而孕。
兽躺在床上,想着这些,那个打扫卫生的女人就凑过来了,她扫着他的床下,骂他说:我说你多少次了,不要把垃圾丢在床下面!——对这个女人而言,这些才是重要的。
在三十分钟车程之外的永安大学,新的生物学教授正在看老教授留下来的论文,同任何人一样,他跳过了关于动物园的大门装饰和檐角上的嘲风兽那一段,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由老教授亲手接生景兽的那段——那只兽浑身的皮肤终于变得透明,可以看见他身体中生长的幼兽,泡在绿色的液体中,还没出生,已经大约人类孩童七八岁样子。最后,兽破开了,像一个灌满水的气球爆炸了,皮肤裂开,绿水漫出,人们从中抱出那只瑟瑟的小兽,是一只雌兽,还没有长出任何斑纹,皮肤很白,虽然面孔不是很美,但不知道为什么,非常迷人。
——他无比兴奋,决定去寻找这只小兽,她应该已经长大了,在巨大的城市中隐匿着——他关心的,也就只有这些,他不会像无聊的小说家们,去寻找动物园失踪的故事,因为这其实比吃饭还简单:上头看上了市中心的这块宝地,决定修建商业中心,并且让里面的兽都出来生活,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谁都可以想象,贵人们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决定几乎失眠,就像很多年前他们决定修一座长长的城墙保卫我们的国家那样。于是他们说,拆了动物园!动物园就失踪了,并且,就像他们决定让其失踪的一切东西,鲜少有人提起。
动物学家们不会相信,贵人们不会相信,建筑商们更不会相信,小说家竟然如此无聊去真的写了整个故事,但他们不明白,小说家关心的不是失踪的动物园,而是动物园失踪之前最后被政府暗中安排给野兽们的牺牲者们和情人们的故事——所以说,贵人们讨厌知识分子,讨厌小说家,讨厌诗人,讨厌挂羊头卖狗肉的含沙射影。
实际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永安城还在,永安城的人们还在,兽们还在,工厂还在,经济增长值还在。即使动物园失踪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唯一的一个问题——但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去关心了——那就是,动物园失踪了,那么以后,孩子们应该去哪里度过漫长的白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