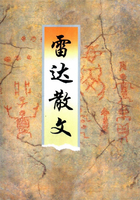1月10日,鹦鹉螺号又重新在水下潜行了,船径直向西。11日,我们安然无恙地经过了礁石密布的韦塞尔角,于13日到达了帝汶海,远远望见了同名的帝汶岛,帝汶岛只是在中午大副记录方位时出现了一下。我隐约看见了群岛中的罗地岛,据说那里的女人在马来西亚的奴隶市场上是公认的美女。
此时,船朝着西南方向,向印度洋航行。我作了种种揣测仍旧猜不出尼摩船长要把我们带向哪里。
1月14日,我们已经看不见岛屿,鹦鹉螺号放慢速度,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在大海上恣意畅游。
航行中,尼摩船长兴致勃勃地潜入水中,亲自测试着不同水层的水温,得出了比仪器测量更为准确的结果。他告诉我,3000英尺的深度上,任何纬度的海水温度都是华氏40度。
我对船长的实验饶有兴趣,可是却不知道这个与人类社会断绝了关系的人做这些实验有什么意义。他把实验的结果都告诉我,是否就意味着我还有回到陆地的希望?我憧憬着那一天的到来。
1月15日早晨,我和船长在平台上散步,船长告诉我他对各地不同海水的密度都有着准确的观察。我从他的描述中发现鹦鹉螺号并不排斥在繁忙的欧洲海面航行,或许不久之后,它就能送我们回文明的大陆了。
接连好几天,我都和船长一起做着许多实验。实验中,尼摩船长显示出了他超人的创造力,我们也相处甚欢。但几天后又不见他的人影,我又重新陷入了孤独之中。
1月16日,鹦鹉螺号在海面下几英尺的地方停住不动了,我猜想是船员们在做一些内部维护工作。我从客厅的玻璃窗中观察着海底的情形,但探照灯没有打开,外面一片模糊。
就在这时,鹦鹉螺号周围的海水被一片磷光照亮了!这由无数微生物发出的灿烂磷光充满了生命力!鹦鹉螺号就沐浴在这深海纤毛虫的磷光中随波逐流了好几个小时。
期间,我和同伴还看见了像火蛇一样游动的大型海生动物和那不知疲倦的海猪在戏水;经常碰到玻璃窗的大剑鱼,还有像一条条彩带般飘舞着的小鱼群。
多么绚丽夺目的景象啊!我们都被这亦幻亦真的奇景折服了。
日子一天天逝去,康塞尔不断地对所见的生物观察分类,尼德·兰则想着改善船上的饮食,我们也都习惯了在船上如蜗牛壳居一样的生活。
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想起自己非同寻常的处境。
1月18日,鹦鹉螺号航行到了南纬15度、东经105度的地方。风暴将至,天气异常恶劣,风疾浪高。我在平台上听见大副测量天气后那句每天必说的话居然被另一句我听不懂的话代替了。接着尼摩船长走出来,拿起望远镜向天边望,好几分钟都一动不动。他放下望远镜,和大副交换了一下意见。大副看起来很激动,像是提出了反对,船长依然镇定如常,又说了几句,大副点了点头。
船长步履坚定地在平台来回踱()步,时而停下来交叉双臂观察大海。他下令加速前进,然后又拿起望远镜望了一阵。我心中纳闷,就回房拿了自己的望远镜也上平台观察,但我的眼睛还没挨到镜片,船长就愤怒地一把夺下了我的望远镜。他仇恨地盯着天边,然后转头对我说:“先生,现在是您履行我们之间承诺的时候了。”
“什么承诺?”我问。
“在我需要的时候把您和您的同伴关起来。”
船长说完,连一个让我提问的机会也没给,就把我和同伴们关到了刚来船上时的那个房间。无需赘述,加拿大人自然是怒不可遏。
同伴们听我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都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正一筹莫展,午餐已经送来了。
吃完午餐,我们各坐一隅。忽然头顶的光球熄灭了,我们陷入了一片黑暗。令我惊异的是同伴们不久就沉沉睡去了,我正感觉费解,自己竟也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双眼。饭里有安眠药!由不得我们不睡!
我依稀听见了鹦鹉螺号关闭舱门的声响,猜想着它应该又潜入了更深的海底。浓重的睡意驱散不开,一会儿,我就坠入了梦乡。
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舱房。想必同伴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怕是只有等到某个偶然的机会才能知道了。
我登上平台,同伴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了。鹦鹉螺号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宁静和神秘,速度适中地在海上航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换过气后,鹦鹉螺号保持在50英尺深的水下潜行,以便能快速浮出海面。在1月19日这天,这种奇怪的运动方式重复了多次。大副来到平台,又说着和往常一样的那句话。
下午两点,我在客厅整理笔记时,尼摩船长进来了。我们相互致意后,他便默不做声了,看上去神色疲惫。他十分焦虑地客厅踱来踱去,终于,他开口问我:“您是医生吗?”
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迟疑了半天才说:“是的,去博物馆工作之前,我行医多年。您这里……有病人?”
“是的,您愿意医治我的一个船员吗?”
“我这就跟您去!”
我觉得这和昨晚发生的事一定有着某种联系。我跟随船长来到临近的一个水手舱房。舱房的床上躺着一个四十来岁,外貌刚毅的男子,他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人。
我弯下身查看,他并非生病,而是受伤。我解开他头上血淋淋的纱布,发现他头盖骨被钝器砸破,脉搏也若有似无,四肢已经冰凉了。
我知道他命不久矣,重新包扎好了他头上的纱布,转身问船长:“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重点,”船长支吾道,“是鹦鹉螺号在一次碰撞中,一支操纵杆被震落砸到了他。他伤势究竟怎样?”
“很不幸,他最多能再活两个小时,我也无法挽救了。”我摇摇头。
船长握紧拳头,眼中泪光闪烁,他的表情让我大吃一惊,我做梦也没想到他这样的人还会有眼泪!
床上的水手奄奄一息,生命正慢慢地离他而去。我盼望着他还能吐出什么临终遗言,好让我了解他一生的秘密!
就在这时,船长却让我离开了。我回到房中,整天心神不宁,晚上睡觉时还从噩梦中惊醒。
第二天一大早我登上平台时,船长已经在那里了。他只字未提昨天的水手,只问我是否愿意进行一次海底漫步。我提议要带上两个同伴,他爽快地答应了。八点半,我们已经穿好了潜水服,带上了探照灯和呼吸器,与尼摩船长及他的十多个船员一起出发了。
我们来到90英尺深的海底,这里不是细沙和森林,而是更为神奇的珊瑚王国!对我这样的生物家来说,再没有比观赏这种珊瑚形成的石化“森林”更为有趣的事情了。
没走多远,我们眼前的珊瑚丛愈加稠密,我们跟随尼摩船长走进一条暗道。两个钟头后,我们走到了1000英尺深的海底,这里的珊瑚树枝叶粗壮,不再是孤立的灌木丛,俨然是广阔无边的森林!我们在森林里自在游走,海底动植物的五光十色让人陶醉、晕眩。
这时,船长停住了脚步,他的船员在他周围围成一个半圆,肩上扛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
我和同伴们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场面。地上几处隆起的地方中有一块上面插着一个珊瑚制成的十字架,一个船员在船长的指示下在十字架附近用铁锨挖掘了起来。我明白了,这是一块海底公墓,船长要把他的水手安葬在这里!
墓穴挖好了,船员们把白色麻布包裹的尸体安葬到其中。我们大家都双膝跪地,虔诚祷告,向死者道别。然后,我们这支送葬队伍就原路返回了潜艇。
回到船上,换好衣服后,我心情沉重地坐在平台的探照灯旁。船长也走了过来。
“那个勇敢的船员一定会安息在他同伴的身旁,起码不会受鲨鱼的侵扰。”我对船长说。
“是的,先生。”尼摩船长严肃而激动地回答我,“免受鲨鱼和人类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