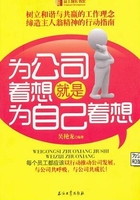良佑借来的老爷车又开始七拐八拐,车里放着早年蔡琴的老歌:“好春才来,春花正开,你怎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我跟着美滋滋地哼,良佑说:“真没看出来,你还会唱这个。”我白他一眼说:“虽然我们之间是存在代沟,但我只要稍加深沉,还是跟得上你们老一辈的脚步的。”良佑故意一脚踩住急刹车,然后说:“去死。”
良佑不明白我此刻的欢喜从何而来,因为他不是病人。我还记得当初考大学时家里让我填报医学类院校,我死活不去。谁愿意天天跟生老病死打交道?纯粹是自虐。后来,我爸摇头叹气地说我这个女儿没出息,送我去军校不去,让我学医也不学,一点大志向都没有。我当他自言自语,不置可否。什么叫大志向呢?在我眼里,只要是大人的志向便是大志向。
但不得不承认,我对中医还是颇有些兴致的,或者说是好奇。要知道那么一锅花花草草煮出来便能治病,稍加改变一种药引便能要人命,真是悬乎。于是,那时候我的底线便是如果家里非让我去学医,我就去学中医,不用开刀,不用临床,顶多给人把把脉,抓个药,整日满身都是清爽的草药味道,也是件美事。
我跟良佑说这些,良佑只甩给我一句话,他说我《西游记》看多了。
老中医住在一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小区里,整栋楼的外观已经黑漆漆的,院子里的自行车棚也锈迹斑驳,细细高高的文竹贴着墙,叶子上落满尘埃。我问良佑:“不用去诊所么?”“不用,老先生早不出诊了。”听起来应该是位高人了,于是我信心满满地跟在良佑身后爬楼梯。
都说人不可貌相,这话今日终于眼见为实了。眼前这个还没有我高的小老头儿只让我把裤腿捋起来,然后拿他瘦骨嶙峋的手在我膝盖骨上推了推,左右拿捏了几下,说:“是骨裂吧?”我说:“嗯。”“怎么也有三四年了。”我连连点头。小老头儿又说:“又不是什么大事,怎么到现在还没好?”我说:“当时拍片子是带着石膏拍的,所以骨裂的地方医生没看出来,就当韧带拉损治的,后来就耽误了。”小老头儿让我把裤管放下,然后坐直身板轻轻咳了一声说:“一帮白吃饭的。”我被他严肃又揶揄的口气逗得笑出声来。
小老头儿继续问:“要手术么?”“啊?不是说不用手术么?”我被唬在原地。“医院不都告诉你要手术么?”“可中医不是不用开刀么?”这次轮到小老头儿笑起来,他说:“谁告诉你中医就不用开刀的?不过你这点小事儿确实不用。回去拿热毛巾加醋敷,每天睡前一次,坚持两三个月就差不多了。”“就这样?”“嗯,就这样。”良佑连忙用胳膊拐我,他说:“还不快谢谢老先生?”我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说:“这就完了?”良佑说:“难道你还想去开刀不成?”我才恍然大悟我之前被渲染得见刀见血的旧创,此刻被面前的小老头儿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我意气风发地靠在座位上说:“走,省了问诊的钱,妹妹请你吃火锅去。”良佑说:“你知道这里哪家火锅最好吃么?”我说:“不知道。”他说:“还不是,乖乖跟哥哥走吧。”说完一踩油门我又是一个趔趄。
都说成都和重庆两地的火锅有名,不到这里确实不知道,整个市区的空气里都是辛辣的火锅味,好在川锅向来是我最爱,要不还真是要人命。我跟良佑七荤八素地要了一大桌,肥牛、羊肉、鱼丸、鸭肠、鸭血、毛肚、墨鱼……还有好些我连见都没见过的东西。良佑给我要了一大杯热豆浆,自己要了瓶哈啤。锅底红椒绿叶煮得翻腾热闹,两个人隔着一张方桌,话题也开始丰满起来。
“怎么跟那个小白分了?”良佑一直叫沈安年“小白”,第一,因为他比我们都小;第二,因为他比我们都白。由此推论,这声“小白”纯属出于嫉妒。
“两个人性格不合。”
“就这么简单?”
“要不能有多复杂?”我白了良佑一眼。
“分了也好,跟个小男生能有什么发展,等有朝一日人家羽翼丰满了,你丫头再美也人老珠黄了,谁还记得你的好?”
我说:“在你眼里就从来没好人。”
“好人?什么叫好人?好人就会一直陪伴你、照顾你,不离不弃么?还是好人就会跟你抛头颅洒热血地谈恋爱?”瞧瞧,此男一贯的愤怒架势又上来了。
“别人我不知道,但沈安年是好人。”
“那你为什么还跟人家闹分手?”
“我配不上他。”我夹了一根茼蒿,直视良佑的眼睛。
我给良佑说沈安年的好,说沈安年的纯良,说沈安年对我的谦让隐忍,说沈安年对我的一片深情。纵使我们吵架后,我一气之下去找别的男人,他仍愿痛苦接受,然后守在我身边。他说:“苏小绿,我不是不恨你,可我更怕失去你。”那架势,咬牙切齿,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感觉后背一阵冷风。
我透过热气腾腾的水汽看着良佑说:“这样的男人不好么?”良佑沉默半晌,叹了口气说:“不好,因为他把你惯坏了。”良佑说在爱情里,一方一味地纵容另一方未必是件好事,他说这样的爱情只能越来越失衡,直到最后无法把握,如同我和沈安年。可是,当每个人都全心全意拼死拼活爱着的时候,谁又能计划得了这么多?
我不能,沈安年不能。良佑,也不能。
我认识良佑的那一年,此男正无比壮烈地与一个北京姑娘谈情说爱。丢了某城里的安稳工作,千里迢迢投奔到北京去与那个姑娘挤地下室。
那时候的良佑,几乎终日无精打采地挂在网上,到处问人借钱。而我当时还是白纸一样的少年,不曾与人说欢喜,不曾为爱辗转颠簸。那时的落魄男子良佑,在我眼里是多么神奇,就像所有小说里渲染的那样,他有才气,他执著爱情,为了心爱的姑娘他可以放弃一切甚至生命,所以,他是英雄。
那时他视我如孩童,只有情绪低落时才主动与我说话。他跟我说他的爱情、他的姑娘、他的执念、他的不如意,他说他的姑娘太有主见太过凛冽以致他无法驾驭,他说他的生活空间太过狭小几乎让人窒息。末了,他说爱情的代价总是沉重。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继续为这场爱情竭力消耗。良佑许久与我不联络的时候,我便猜,他与他的姑娘,想必又是风生水起。
若干年后,这个激烈愤怒的男子与我说抱歉。他说:“丫头,这么多年,只有你对哥哥不离不弃,而我,却从未真正关心过你。”我说:“当我遇见你时,我的人生尚未开始,你身上所有的风景于我来说都是谜。之后,我却也像你这般为了爱情辗转颠覆,我才发现,我像跟在你身后的影子。”
我坐在良佑对面,捧着豆浆,细数他的种种过往。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离开北京后去了敦煌。那次你在敦煌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里吵架。”
他说:“记得。你斥责我从未过问过你。”
“是,那个时候我正与沈安年处于纠结之中。再后来,你又遇到新的姑娘,你写信给我,并给我看你们的照片,你说你已经为爱情消耗不起了,所谓幸福大抵也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你要准备跟那个姑娘结婚了。那时候我真替你高兴,我想,你总可以安生下来了。却不想,最后你们还是分开了。”
“呵呵,我记得我给你写那封信时是在咖啡馆里,身边没有纸,便从人家杂志上偷偷扯下来一张空白页,后来才发现背后竟还有朵玫瑰。”
“后来你与那个姑娘还有联系么?”
“没有,我们分开后,她就消失了。我试图联系过,但毫无音信。”
我微笑起来,想到同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江水木。只是,那个姑娘消失的原因是爱而不得,那么江水木呢?我多希望他失踪的原因也是如此简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