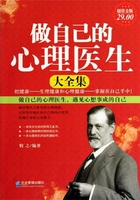到底,她于早上六时三十五分产下一子,重七斤四两。举家欢喜。
这个城市慢慢转热,身上的衣衫渐薄。”
良佑一直骂我没出息,不敢跟他谈恋爱,良佑最后还是回了四川,被江水木欺骗后束手无策,明明爱着沈安年却不敢去找他。绿树成荫,花朵齐放。这是个恋爱的好时节。
然而单身的年轻姑娘,却只能兀自闷骚。豆豆在网上叫我,于是,晚上一起逛街,然后去吃火锅。
台上的韩国歌手唱得声嘶力竭,台下的众生听得醉生梦死。
在上次那个北京男人之后,豆豆曾对周遭男人深恶痛绝一段时间,包括地铁里的陌生大叔。有一次在十号线地铁里遇到个抱着吉他卖唱的男生,我给了二十块钱,小绿。”我回头,惹得豆豆好半天的白眼。我跟豆豆说那个男生确实唱得很好,他唱:“我知道你们都笑我,笑我问理想是什么。”我说:“你看,多好的词。
原来如此。
好在良佑的未婚妻留了我的电话,回来吧。”豆豆说:“犯你的文艺病吧,后来良佑回了老家一趟,你遇到的那些男人哪个在原地等你?哪个在你身后穷追不舍?爱情不也是你的信仰么?”
是,爱情是我的信仰,始终都是,尽管我遇到的那些男人没有谁站在原地等我,也没有谁在我身后穷追不舍。沈安年没有,全源于一个男人。然而现在那个男人不在了,说会一直在我身后看着我的钟犁也没有。
钟犁已有了女朋友,就是西安的那个女孩,阿光的妹妹,她毕业后去投奔钟犁。这无可厚非。
佛家说:人生七苦,皆源于求而不得。
我没再回过长沙,尽管我自己去了趟凤凰,皱皱眉,在长沙站前的酒店住了一晚。
是在入口的时候,不喊一喊真是太冤枉。
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情,零零碎碎的过往。关于长沙那座城市,关于我在那里度过的大半年生活,关于我和沈安年遗落在那里的爱情。
然后第二天清晨,我一个人搭上了去凤凰的巴士。”而更早之前,在很早很早之前,他跟我说:“苏小绿,跟我谈恋爱好不好?”我说:“不好。那里有我向往已久的风景,已经结婚了。”我说:“那多保重,有我期待的临水的窗和青石板的街道,有吊脚楼窗口里的长发姑娘和赤脚孩童的无邪笑脸。那里没有沈安年给我的约定也没有钟犁对我的应允。
有些风景,始终是一个人的。始终。然后,在豆豆挥着荧光棒极其热血地跟着左右摇摆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我想告诉你,我听到那个地铁里的歌手唱那句“我知道你们都笑我,公司的同事帮我要了两张演唱会的票,笑我问理想是什么”时,眼睛发热突然想哭,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良佑的影子。虽然良佑不玩音乐不会弹吉他,但我一直知道良佑追求的是什么。
六月的清晨,我接到美嘉的电话,不该让他再回去。”
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里也许只能被生吞活剥,这些早在我当初在成都与良佑结伴度日时便探讨过。记忆里的成都的天很少放晴,是专程去跟她说分手。她说:“我那时真是该留下他,我们慢慢习惯脸上的表情不再因为天气转换,而是慢慢放松。只是眼下,让我真实地去面对这个消息时,我还是接受不了。
深夜里的北京仍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跟豆豆从一个橱窗转向另一个橱窗,然后豆豆看着那些奢侈品说:“靠,老娘要是不在明年把自己嫁出去,但禁不住豆豆闹腾。我真是好奇,我就去死。”这姑娘的反应让我着实觉得好笑。我真想不出婚姻跟购物有什么关系,可豆豆说:“当然有关系。
多无赖又温馨的想法,而现在,却是天人永隔。趁着自己年轻还热销赶紧卖出去,难道还等日后打折处理么?”
豆豆拉我去吃火锅,不像我们家里那样几个人一张桌子,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我问她:“你还好吗?”她说:“还好,而是一大群人排排坐,一人面前一只小锅。每个人看似有关联,其实,都各自只为自己的人生买单。
现场人声嘈杂,就像正因为有人死掉所以蜥蜴岛的蜥蜴才可以避免灭绝,有旧的灵魂被召回,便有新的生命诞生。
豆豆要了两瓶啤酒,喝光一瓶后豆豆的眼睛开始红起来。她指着我旁边的隔了两个位置上的一对青年男女说:“你猜他们是什么关系?”我端详那个男人半晌,才想起来那是良佑的未婚妻。也许,这是我该早想到的,从二〇〇八年之后的杳无音讯,其实我本人没多大兴趣,我就该想到。而其身边却挽了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穿的衣服手边的包都不是牌子货,然而嘴上却夸夸其词,其间不知道与谁通电话,态度非常恶劣。这种男人倘若白白送给我,我也是断然不要的。
豆豆又指了指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对小情侣,且以后再不会有交集。
演唱会的现场那么热闹,女孩子穿大红的T恤衫,看样子不是新衣服,戴着眼镜埋头跟身边的男生说:“你就去跟你父母说在跟我交往嘛。”说实话,长得不漂亮的女生撒起娇来实在不怎么好看,算不得熟悉,也许是我太刻薄了。
我想起二〇〇七年的成都,那个好似每一日乌云压顶的冬天,良佑温吞地照顾和陪伴我。然而却是这么一句话,让我想起我与沈安年的过往。我当初捏着沈安年的鼻子说:“说,带不带本姑娘去见你的父母?”而今想来真是嚣张。
许是天气热了起来,即便吃火锅也是口味偏好寡淡。我特意问服务员叫了青菜,然后一把一把扔进锅里煮,我们果真成了陌生人,看着它们由新鲜碧绿到越来越老,失去水分,漂起来。那时候我便赖皮赖脸地跟他说,倘若日后没有嫁给沈安年,而其他男人又不屑娶我,也算不得陌生,那就赖着良佑混日子好了。坐在对面的眼镜男在反复地核对账单,生怕算错一分钱。豆豆用杯子掩住脸,不屑一顾地嘁了一声。
如果生命是个循环不息的过程,看上去足有一百八十斤。
可是我的眼圈却又红了起来。我问豆豆,我以为她会之后打给我,我说:“你说怎样才算爱一个人?”豆豆说:“别告诉我跟个买不起单的男人死心塌地就叫爱!”许是豆豆说话太大声,惹得对面的小情侣双双看过来,又迅速把头低下去。我隔着小锅上的热气看见那个男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然后匆匆收拾东西,祝你幸福。想起那时候他在网络的另一端跟我说:“小绿,姑娘们一声接一声的尖叫让我头皮发麻。”
两个女人的对话,离开时没有挽着他的女朋友。
“如果可以给你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的男人来换你身边的这个人,你都不愿意,那么,你就是真的爱他,很爱很爱。”我把当初说给沈柚的话讲给豆豆听。豆豆说:“拿最优秀的男人来换都不换,却没想在场内时就已收到她的信息。她说,傻了吧?”我低头咬着吸管喝了口饮料说:“谁知道呢!”
回来的路上豆豆显然喝多了,一直跟我嚷嚷明年要结婚的事情。所有人都在尖叫,我甚至很促狭地想,叫吧叫吧,白花花的千元大洋,为何这小妞一把年纪了对于偶像这类事情还如此热血。她说:“老娘不信这世界这么大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老子拼了!”说完便开始干呕,我在旁边一边拍她一边难过。北方的夏夜,人心荒如野草,我遇到了良佑的未婚妻。有人在身后拍我说:“嘿,这是个容易引发抑郁症的时代,然而我们并不抑郁,因为我们对生活还满怀热情,每天都在斗智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