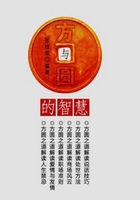这个城管秘笈透露了好些城管执法的实用招数。比如在“反暴力抗 法的局部动作” 一节中,教导城管14以暴制暴”时怎样不落下把柄:注意要使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快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 施,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
这本城管秘笈是真是假,尚有待详察,但城管执法,以“打”闻 名,却是事实。俗话说,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举国上下,连三 岁的孩子,一提到城管,都当是打人的,有的地方,据说提城管可以止 小儿哭,跟提大灰狼--样。
我个人是主张取消城管的,因为这个所谓的执法部门,于法无据。但 是,中国的惯例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门只要成立起来,想要取消就千难万难D考虑到上级领导的难处,我可以退而求其次,严格规范域管行为, 不能打人,与暴力绝缘。当然,这也很难,因为城管的行为模式已经定型 了,似乎不打就不叫执法。暴力的滥用,导致执法对象也日趋暴力化。
在发达国家,执法行为多半是不使用暴力的,即使带枪槭的警察, 也是如此,除非碰到刑事犯罪,除非碰上暴力性极强的群体暴乱。显 然,我们的城管管理的对象,不是犯罪群体,也不是情绪激动的示威群 众,他们面对最多的人,无非那些进城谋生的小商小贩,那些走街串巷 谋生的穷人。如果不是逼急了,他们一般不会暴力抗法。
小商贩之所以跟城管周旋,打游击,就中国而言,的确是他们的生存 的必要。城乡的集市贸易,就是存在无法理解的自发性,商贩自发集聚, 而买者也自发拢过来,一旦政府千预,换个地方,盖上房子,大家就都不 来了。自古以来,集市贸易看起来无序,其实内部有序,政府要做的,一 般都是因势利导,稍微整顿一下,然后坐等收税即可,用不着大动干戈。
再说,小商小贩,贩卖是他们的谋生之道,是他们的饭碗,自古 乡下人想挣钱,主要的渠道是跟城市人交易,你不让他交易,横加干 涉,等于是断了人家的财路和生计,注定要招致激烈的反抗。
比较起来,城市的面子,跟乡下人的生计,一个人道的政府,是 应该向着后者的。所以,为了城市的面子可以对商贩进行管理,但要适 可而止。除非个别人扰乱了居民的生活,阻断了道路,又坚持不听劝阻 的,可以请警察来强制执行。不能像现在这样,用暴力赶尽杀绝,这样 做,只能让暴力升级,再升级,最后,纵然城管个个武功高强,打人不 留痕迹,也一样有麻烦。
一票难求
每年春运的时候,一票难求,但票贩子、黄牛党手里却有大量的票 源,这种现象,已经延续很久很久了。没错,就目前的铁路运力而言, 春运期间车票的确会有些紧张,但是紧张到这个程度,人们通宵排队依 然一无所获,甚至体力不支而猝死,还是不正常的。
干什么吃什么是国民的老毛病,干铁路,’就吃两条线,似乎天经 地义。从买票走后门,到自觉跟黄牛党结合,把经手的车票当成自己 生财的终南捷径,是一条顺理成章的灰色路线。应该说,这条路线上 已经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要想斩断它,已经到了非动大手术 不可的地步。
铁路售票实名制的建议,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之所以实行不了, 绝不是技术手段的问题,也不是所谓铁路部门的认识问题,症结就是一 旦实行了实名制,这个灰色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而这个集 团恰好又有力量寻找各种借口,将实名制挡住。
说到底,铁路部门的这种灰色、不法的利益状态能够生存,而且越 活越滋润,即使在铁老大经常亏损的情况下也依然滋润,关键还是源于
铁路这种公共资源的经营性垄断。改革三十年了,像铁老大这样既是政 府部门又是经营公司的部门,已经不多了,经营者、管理者和裁判者三 合一的强势垄断地位,使得铁路的经营成本永远都会居髙不下,永远黑 幕重重。这个近乎世袭制的王国,垄断着用纳税人的钱修建的铁路,将 这种公共资源当成自己的铁饭碗,内部人子子孙孙吃下去,绝对不允许 外面的人分上哪怕一杯羹。这样的一个准封建王国,其内部的猫腻,无 论外面的人怎样想破解,只要王国还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健忘
哈尔滨的平房区,有座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纪念馆。它是公认 的侵华日军的罪证,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这个纪念馆的 办公楼的一层,目前已经变成了商品房的售楼处。(据2009年9月19日新 华网)
日军七三一部队是干什么的?我想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 那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从细菌战的特别部队。现在哈尔滨平房的遗 址,就是当年侵华期间他们的基地之一。这样一座遗址纪念馆,对于 记住那段悲惨的历史,向世界昭示侵略者的罪行,无疑是必不可少 的。特别是在日本政府并没有就细菌战问题有明确的表态,而且日本 国内的右翼势力依然否定曾经在华从事过细菌战的情况下,这个遗址 就显得格外重要。
开发商有积极性不奇怪,如果能把楼都卖了,他们肯定也会卖的。 但是,有关部门为何会准许他们这样做?
也许,在开发商和有关部门眼里,遗址办公楼最适的用途,是为 “经济建设”服务,或者说,为开发商以及卖地的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服 务。不知道有关部门,此番可以将遗址办公楼用作售楼处,以后是不是 也可以临时改作歌厅呢?比如说,为了某个部门临时举行联欢会。
一个民族的尊严,是靠对自己历史的尊重建立的。如果我们对自己 在过去不久的那段被侵略、被屠杀、被侮辱的历史,都采取一种无所谓 的态度,那么,中国以外的人,将会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还有什 么资格去谴责日本的右翼?
画圈为牢
都说中国人窝里斗,柏杨先生当年给国人头上*J上“丑陋”两字,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人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习性。其实,更早一 点,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之初,我们的志士仁人也经常为国人的这种习 性而懊恼颓丧,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几。
窝里斗多半是因为派系。孔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这里所谓的 党是指阿党,以私利结合的一伙。可惜,国人中君子太稀缺,所以偏要 党。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能找到一个个的小圈子,说话、做事,往 往以小圈子为依据,想不斗都难。
中国人祖袓辈辈活在乡村世界,说是家庭或者家族本位也许并不十 分合适,但毕竟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个洋葱头结构的圈圈里,圈圈有核心 有边缘,每个人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 们说话的。不过,洋葱头里的每个人有一点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对圈 子的依赖。当人们还生活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 生活单位,乡村里的公共生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但毕竟有人 替他们说话,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里。可 是-旦离开了乡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 们的活动,原来公共生活的情景无法再现。城狐社鼠,没了依托,难免 无所措手足,未免按照原来的圈子模式,复制类似的圈子,力求再现过 去的情景,江湖上的结拜、行会里的师徒等等都属此类。
进入现代之后,城里的人似乎离中世纪很远了,离农村也很远了, 但活动在潜意识里的暗流,却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不拜把子磕头 了,但不靠上个小圈子心里就不塌实,没有办法寄托自己的情感,甚至 没法子给自己找乐。小圈子无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结构的替代品,难免 在行动中以小圈子为依托,动机和冲动,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为 准。如果说,对过去的中国人而言,家庭具有价值观的意义,那么,现 在的小圈子,怎么也有半个价值观的分量。
古代中国的乡村,虽然不能说没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葱头的结 构中,不可能人人都参与。每个洋葱头的核心人物才可以参与议事, 而且说话的分量各有不同,往往只有那些乡绅和别类的精英才可以真 正参与意见。其他人只有汉娜?阿伦特所谓的labor (劳动)而没有 action (行动)的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而在那个时代, 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场景,是一种非稳态的情景,属于无法用“礼”来 约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难分彼此,相互渗 透,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社会,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商人已经不 算是好人,而车、船、店、脚、牙,则跟黑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了 (俗谚: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因此,在农村社会以外,也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国的沿海都市总算有了市民社 会的雏形,但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又秋风扫落叶似的将每个人都 变成了单位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尽管处在非农村的场景里,但至少 在外观上很像是乡村。在其中的人,也像农村人一样,彼此没有隐私空 间,可以戚戚瞭嚷。但是跟过去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资源 都掌握在单位领导手上,人的行动,不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更重要的 是,单位没有了过去农村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垂直与领导发生联系, 没有过任何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每个人都会追求跟领导或 者跟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套上某种关系,地缘、亲缘、业缘等等都成了现 成的工具,而各个领导间的分化,则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系。实际上看 起来派系间的争斗往往是无原则的,甚至像是乡下妇女间莫名其妙的闹 剧,但事实上都有其利益争夺的背景,比如,每个髙校资深教授之间, 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最早大多起源于建国后第一次职称评定。从 表面上看起来,各单位领导似乎对派系和派系斗争深恶痛绝,但实际 上,派系斗争往往对单位的主要领导有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更方 便地控制局面,做个似乎是超然的仲裁者。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it真正的公 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学术 讨论中,没有fair play的风度,没有弄清问题的预设,甚至想把对方批 倒,再踏上一只脚,帮腔是自己人,批评者必是敌人D其实,我们早就 掉入了祖先为我们准备好的圈子里而不自知,画圈为战,也画圈为牢。
最牛女生的背影
温家宝总理到北航图书馆看学生,在一国总理面前,一位女生端坐 不动,背对着总理照旧看书,照片传到网上,被誉为最牛的女生。
总理来学校看学生,恰好赶上期末复习的紧要关头,埋头读书顾不 得跟总理打招呼,或者起立表示敬意,都没什么。但是,这是在中国。 我们是一个曾经跟领袖握手后多少天都不敢洗手的国度。
按常识,总理视察一个单位而没有事先准备,多半是出于总理的意 思,而且这个意思要足够坚定,或者干脆是“突然袭击”,临时起意来 的,否则,下面的人依旧是要摆一摆的。
记得当年我所在学校也接待过领导人的视察,学校里凡是能在视察 中露面的师生,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练,不仅欢迎队伍的动作要热烈而 整齐,雀跃都得雀跃得一个样子,连在图书馆里看书的、饭厅打饭的, 都经过长期练习。万一被领导人问到了,怎样回答,都得准备好预案, 第一方案,第二方案,务必保证整齐、有序、得体,一丝纰漏都不能 有,让领导人满意,令学校领导面上有光。
这样视察的场景,不劳有关媒体剪接加工,所有的镜头都完美无缺,像这样最牛的女生,即使有心牛一下,也肯定不会有机会。
不管怎样,这位最牛女生的背影,对于我这个过去时代的过来人而 言,意味着过去时代的过去。现在的年轻人,无论领袖多大,对他们来 说,都是人,即使崇拜,也是追星式的,他们不会当拜神的香客。领袖 人物到来,没有引发这个女生下意识的起立,也没有让图书馆的其他学 生毕恭毕敬,连椅子都不敢坐,即使坐也欠着半个屁股。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其实不易。
回想起我们当年,那种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崇敬,一想到领袖也会跟 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也会死亡,就感到是一种亵渎。恍惚已成隔世。我相信,这样的感觉,至少在普遍意义上,不会再有了。
最牛女生的背影,昭示着一个人口最多的民族,终于正常了。我们 终无可以正常地看世界,看周围,看政治领袖。唱了那么多年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要神仙皇帝”,经过30年改革, 才真的变成了现实。
现在,如果各个地方某些端足了官架子走到哪里都要求管辖的百姓 尊崇的地方长官、单位长官,也能够放下架子,别再前呼后拥,别再全体起立,这个世界,也许就更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