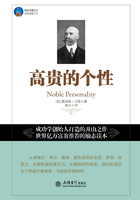人生总会有些奇遇。因为是奇遇,所以往往在某个不经意间突然降临。
二〇〇六年的春末,省作协报请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到沅城县挂职副县长。
刚到那天晚上的接风宴,是在沅城最高档饭店的最高档宴会厅摆设的。我喝多酒了,脑子有些晕晕乎乎,双脚也有些飘飘忽忽,近十来年我可没这么放开地喝过了。快十一点了,在驾驶员搀扶下回到临时住处——沅河宾馆三楼尽东头的客房,我准备洗个澡就睡觉,谁知响起了“嘭嘭嘭”的敲门声。我微醺的惬意被敲掉了,心里生出几分懊恼:县里的头头脑脑们刚才一起吃一起喝,有什么急事酒桌上咬咬耳朵不就行了?事要不急,明天说不行吗,非要现在不可?再说,我大小是个副县长了,不管你官比我大比我小,也得讲点文明,怎么把门敲得这样急响,吓人一跳。我从沙发上起身,很不乐意却又使劲地在脸上堆出几分笑,嘴里叨叨着:“来罗来罗,请进请进!”
门打开,首先戳进一头白发,接着仰起一张布满沟壑的国字脸,鼻梁上架着副白色泛黄的眼镜,撑着白头发国字脸的是有点佝偻的高瘦身架。
“同志,您找谁?”我问。
好像没听清我的问话,也许是故意的,白头发国字脸径直走到沙发前,动作很夸张地重重地坐下,带得沙发一阵晃动。
“同志,您找谁?”我又问。
“同志,我找您。”国字脸上也向我堆出笑,但笑意似乎没将渗进脸皮里的苦意覆盖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铺撒在沟壑间,看着有点瘆人。
“找我?”我愣住了。
对方收住脸上瘆人的表情,像动画镜头剥离出了真实。
这当儿,我倏地想起来了:“啊,高鸿鹄,高老师,高大哥!”
“高鸿鹄,高老师,高大哥!”高鸿鹄说着,往我胸部重重地推了一掌,“你他妈又当作家又当官,只想着捞好处,把高鸿鹄高老师高大哥给忘了!”
我一个趔趄,急忙扶住身边的桌子角,连连作揖道歉:“不敢!不敢!”
“不过还好,还没全忘掉。要全忘了我可饶不了你!”
“我就是忘了自己姓啥,也不敢忘了高大哥。是兄弟喝高了,喝高了,贪杯误事啊!”我急忙取出一次性水杯,躬身沏茶,乘着这时机使劲把“高大哥你老得也太快了,让我都认不出来了”的话咽到肚里。
“你可是活得最仔细的人,还会贪杯?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别给我耍贫嘴。”高鸿鹄说着起身往外走,“通知你件事,明天上午八点半,到沅河水库西坡山洼参加一个活动。早点休息吧。”
“什么事?”
他好像耳朵有点背,没回答,又好像故意的,走到门口,才答非所问地来了一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给我摆官架子!”
“不敢,不敢。”我显得更谦恭了。
“你是喝得多了一点。”高鸿鹄回身作了个结论,临关门前又甩下一句话,“不多打扰了。”
我将刚沏好的茶放到茶几上,回坐沙发上,发了一阵子愣:这到底是哪门子事哟,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屁股没坐热就走了;非要我明天去参加活动不可,去干什么又不讲清,还居高临下地“通知”我。这个高鸿鹄,怎么弄得神神叨叨的?
算了,不去了,也许压根儿就没什么事,他开个玩笑……不行,老高可是不苟言笑的人;再说多年不见了,真没事他不会我刚上任就开这样的玩笑……我的脑子里打着架。
我习惯烦躁时洗个澡,温度适宜的热水似乎可以将烦躁洗净。可今天洗完躺到床上后,脑子里简直像大雨后的河水泥沙翻滚,想的事更多了。
到了沅城,八品芝麻官的乌纱帽戴在头上了,我当然不想保它,更不会企图用它换一顶更大的。但不论“在其位谋其政”也好,“入乡随俗”也好,也不论顾及省作协的影响也好,不丢自己的脸面也好,总要注意一点。离开省城前,省作协的副主席老章找我谈话,告诫沅城这地方“文革”中闹腾得很厉害,去了要注意一些……“文革”闹腾的事,我无所顾忌,闹腾得再厉害,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是人心上垒堵铁墙也该生锈了。再说那些事与我何干?我要注意的是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刚到这段时间很重要,第一印像更重要……高鸿鹄他们是什么活动?官方的民间的,还是半官方半民间的?情况没搞清楚,林副县长一到职就贸然参加合适吗?再说,去参加,是代表县政府,还是代表个人?代表县政府,谁授予你这权了?代表个人,是何缘由?这些都要有个说法的。我后悔刚才没把高鸿鹄拉住问个清楚。
这样吧,过去叫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现在讲多请示多汇报,少犯错误少烦恼。我从上衣兜里掏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餐桌上给的电话表,要通了我的顶头上司——牛志国县长的手机。
“牛县长,休息了吧?打扰了打扰了!”
“林副县长,怎么样?”牛志国县长是沅城本地人,先当了四五年的副县长,去年才扶正,说话胸腔共鸣很好,瓮声瓮气,沅城味很浓。刚才的接风宴就是他主持的。一开场他说县委王书记到州里开会,三天后才能回来,下午特意打电话让他一定要接待好省里下派的林副县长。牛县长说,现如今吃饭就是吃文化、吃档次、吃氛围,你那鸡鸭鱼肉、鱿鱼海参谁在乎,你们都是头头脑脑的,别在林副县长面前给我弄得没文化没档次的。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牛县长这话是实话实说还是虚话实说,是正话反说还是反话正说。现如今的餐桌上也是个小社会,扑朔迷离,让人分不清真假呀!
“牛县长组织的火力太强了,我喝高了,喝高了!”我想装得有点语无伦次,以便下一步以守为攻,但自我感觉装得不太像。
牛县长哈哈大笑:“其实,吃饭前我是这样交代的,林副县长是文人,特别要突出文化,每人至多敬一杯,女士优先也不能超过两杯。谁知一喝开,他们就不按既定方针办了。”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喝高了。”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想你牛县长的既定方针到底是什么我早看出来了,你一使眼色,两个女部长还是女局长就凑过来,一左一右地给我灌酒。
“听你这声音不怎么高啊,老林,你可别蒙我……”牛县长的话里没有笑意了,真是酒坛老将,从手机里就能听出对方肚里装了多少酒。
“真的喝高了,真的,借我两个胆子也不敢蒙领导……”我只有一装到底,手机里又传来牛县长的笑声。
好在牛县长没有完全揭穿我:“不管喝高没喝高,明后天双休日,你就好好在宾馆休息得了。”
“休息?我想明天请人介绍一下,尽快进入情况……”话没说完,我说不下去了,这是典型的假积极,说着假积极的话我脸发烫了,好像又一杯酒下肚。
“你要干两年,还在乎这一天两天,星期一我亲自给你介绍,不,亲自汇报得了。”稍停顿了一下,听得出那边的牛县长呷了口茶,“你过去没来过沅城,我从县政府办公室给你找个人当导游,城里城外好好逛一逛。不,从县文工团找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着,你兴致可能高一点。”
“别别别,别找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弄不好我犯错误了,让你这县长负领导责任。”我也幽了一默。
手机里又传来震人耳膜的笑声。
“县政府办公室的人也别找,好不容易盼个双休日,让人家和老婆孩子一起,有什么事办什么事得了。”
这当儿,我的脑子忽地转了个弯。高鸿鹄说的活动,牛县长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会有赞同不赞同两种态度。我和牛县长今天才认识,贸然发问,让人家表态参加不参加,也太不得体了。于是我说:“这样吧,听说沅城之美,在沅河水库。明早我自个儿到沅河水库附近看看,想走就走,想坐就坐,自由一点。”
“那也好,那也好,到水库也就是一根烟的工夫……早点休息吧,星期一见。”
这就好了,到水库我是报告过的,高鸿鹄他们的活动完全可以说是偶然碰到的,至于到了那里该怎么办,看情况再说吧。
躺在床上好一阵子,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来吃两片“安定”,到底还是忍住了没吃。
我认识高鸿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不,初期的事,大概是八二、八三年,在省作协办的创作学习班上。那时我刚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省城二中当语文教师,非正式头衔是业余作家,其实只能算个写作爱好者。
创作学习班开班没几天,请了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教授介绍“伤痕文学”。这位教授的基本观点是“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高昂的作品给人激励”。
刚讲到这里,后排传来沙哑的声音:“教授,我能说几句吗?”
一听口音就是州县来的。我回头看,提问者一身黑色对襟衣服,灰白头发罩着一张国字脸,瘦高身材有点佝偻,戴一副白色眼镜,是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还是没及时擦拭,镜框已经有些发黄,看上去五十来岁,模样带着州县的土气。
“请讲,请讲。”年轻教授很豁达。
“我不同意‘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高昂的作品给人激励’的观点。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大悲之作,它使人消沉了吗?《红楼梦》是中国的大悲之作,它使人消沉了吗?没有嘛!”灰白头发国字脸的嗓子好像有点问题,使劲“噢噢”了几声,又往下讲,“如果你的观点成立,鲁迅先生‘没有悲哀和思考的地方,就没有文学’的观点,恐怕就不能成立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总有些悲哀的,按照你的观点,就只能使人消沉了。而实际上,先生的许多作品,特别是小说,含着悲意,但能使人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是号角,是战鼓呀!”灰白头发国字脸讲得很有激情。
“什么……请你复述一遍。”教授涨红了脸。
国字脸复述了一遍。
“哦,我是从卢新华的《伤痕》讲起的,是从《伤痕》讲起的……并不是普遍地讲,你曲解我的意思了。”教授有点语无伦次。后来,他又讲了一通道理,但未能否定国字脸的观点。
这事使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学员眼前一亮。要不是出于对教授的尊重,我会当即站起来附合国字脸的。我对国字脸油然而生敬意。
课后一打听,国字脸就是在《边塞文学》和《群众文艺》上发过稿子的高鸿鹄,沅城县城小学的历史教师,实际年龄三十四五岁。
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高鸿鹄的文学、历史知识很丰富,说话“抬竹竿进城,直来直去”,便产生了信任感,一来二往,与他无话不谈了。他给我讲沅城“文革”两派争斗、恋人反目成仇、同窗学友形同路人、在大街上公开打死地富反坏右分子等咄咄怪事。我则向他汇报立志写作的决心,有时还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学习班期间,我写了两个短篇,请他提过意见。他认为我的小说基本是图解,彻底否定了,弄得我很难堪。但他讲意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从不客套,这使我对他刮目相看。
三个月满了,学习班结束了。分别那天,我拉着他走进一家挂着“文林”横匾的小酒馆。酒过三巡,高鸿鹄眼圈泛红:“老弟,前几天我给你讲过,别看沅城贫穷落后,我们沅城一中高六七班学生素质特别好,在沅城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要有现在这种条件,我那批同学中可以出很像样的作家、工程师……可十多年了,大家都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忙活,没一个像样的。”
这是真的吗?一个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小县,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