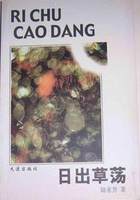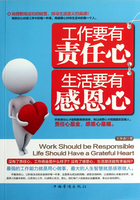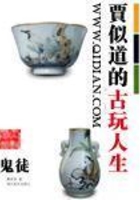管翼贤
当代大文学家郑振铎先生,在他着手编辑的《世界文库》的发刊缘起上说:“伟大的文人们,对于人群的贡献,是不能以言语形容之的,他们是以热切的同情,悲怜的心怀,将他们自己的遭遇,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微笑、悲哀、愤怒、欢悦,一点也不隐慝,一点也不做作,他们并不在说教、在教训,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
这是说一个文学家,怎样把他婉曲动人的情怀,从弘丽隽妙的谈吐中,发为伟大的作品,而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人们,成为了对人群的贡献;这个贡献是由美的方面,通到真的方面和善的方面。
科学家的贡献,是由真的方面通到善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但是他的情怀并不婉曲动人,谈吐也并不弘丽隽妙。
哲学家的贡献,是由善的方面通到真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但是他的情怀甚至于冷得骇人,谈吐甚至于使人莫明其妙。
人,人生,是希望其同向真、美、善的地方走去,承受科学家哲学家的启示和文学家的感动,这些都很必要,但这些又都很费劲,因为我们对科学家须理解,对哲学家须思考,对文学家须体验,并不是任何人只要听到他们一语一句,或者一个原理,一个解说,一首诗以及一篇小说,便能通了七窍。他必须有理解、思考、体验的能力,才能够懂得。任你文学家对人类贡献如何的伟大,要不是你的读者,读者要没有哲学的能力,那伟大从哪里成立?
文学家之所以比较的容易使人鼓励、慰藉、激发,正是他将某一段人生,在理解了,思考了,体验了,把它真、善的地方,用正面或反面的方式,再加上一件美的外衣,显示给你,我们不必多费劲,也便能体验出来,只要我们太不是白痴,太不是文盲。
如果我们将人生的某段,缩成某点,索性再将那件美的外衣也脱掉,便是赤裸裸地将那一点体验得来的真、美、善,用三言两句很平凡的话语叫喊出来,这个,我想只要有灵性,有耳朵,感受了便能理解,能思考,能体验,一点也不费劲吧?
在实效方面说,我们要理解一点什么,看一本书,不如听一篇演讲;听一篇演讲,不如听一段格言;听一段格言,又不如学两句俗谚。这就因为俗谚只是用一两句最干脆的话,便把一个人生法则,正面或反面的启示给你了。
过去几十年,读一部《四书》,知道了做人,读一本《增广》,也一样知道了做人。
现在,从小学念《公民教科书》,一直念到《人生哲学》,知道做人了。不能这样,你最好还是去读《增广》,虽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人生法则,但没法子,因为现在通俗一点完全一点的代替这本书的书,还没有出世!
《增广》上说:“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便是我说的听格言俗谚胜过读书的注脚,假如你不能再多读书了,那么,你最好多听人说关于人情世故道德文章的话。
只是用一两句最干脆的话,嚷出来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某一点体验,这又是最天真的。因为他只凭他的热情,一感到某点的叹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愤怒、的欢悦,便是一点也不隐慝,一点也不做作,更不用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他只是如实地,赤裸裸地,吐出为快。就是说,他所体验得来的真、美、善,他不十分要经过科学的分析,哲学的论证,以至于如文学作品加上美的外衣,他的话使我们一听就懂,一懂就开窍,就搔着痒处,于是得了个启示。
当他要嚷出他的话,他也不是在说教、在教训,虽然有时人们觉得他似乎穿着教衣。他也不是在冷嘲,在热骂,虽然有时人们觉得他似乎有点红着脖子,竖着眉毛。他听是抓着他所遭遇的事物,凭他热烈的同情,悲悯的心怀,给一个批判或认识,如实地,赤裸裸地再倾吐出来,丝毫不加妆点,而且很干脆就是这两句,不管它的美丑,所以,它常常是对社会反动的,是有点像疯疯癫癫的。
非难他的,说他在穷发牢骚,只要不是非难他的,一定说:“干吗老说在我心坎上?”因此,这说话,是更能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
老宣的疯话,现在催促快出单行本,这原因上面完全说了,就把它当做序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