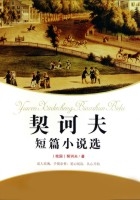孙庄一直怂恿着孙鹰去吵奶奶,快快拜月,月亮都老高了。可是,说是去段里学习的孙安路还没有回来,早该下班的安芯也没影儿。好不容易把撇着八字脚的巡道工盼来了,他却是很沮丧的样子。奶奶问:咋啦?跑到月亮上砍桂花树砸着腿啦?
巡道工说:叫玉兔咬啦。
出么事啦,看把你愁的。
原来,今晚要过专列,各个行车单位都要挑选党员和政治上可靠的职工上岗,把当夜班的一般职工换下来。车站和工务段还要配合铁路警察,在车站和铁路沿线布岗,每隔三五百米就得站一个人,戒备森严的,可巡道工不在此列。沿线多长呀,整个工务段绝大多数职工都被派出去了,他一直守着合西养路工区里的电话机,期待派班命令,想不到,他竟是今晚少有的闲人。
秀说:不派就不派吧,俺过俺的节。天凉了,野地里熬上一夜,也怪难受的。
奶奶说:做么都得给个理。么叫可靠?俺当过兵,受过伤,还当过班长,咋不可靠?干铁路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一年穿破了一堆鞋,从来没出过事,还不可靠?不就是给国民党抓了壮丁吗?可俺后来不是又当了解放军吗?
奶奶气呼呼地说出巡道工的心里话,忽然想到儿子,便急急地去问张家。张段长和张卫国也没回来,这让她感到欣慰,因为,凭此可以断定,今晚安路和张家父子一样也有紧急任务。
秀,别等啦,兴许安路不回来吃啦。奶奶的声音里竟有些兴奋。
秀说:电务不是行车单位,安芯该回来的。
奶奶对孩子们说:把那砸死狗留给姑姑。谁不听话,下班放学不赶紧着家来,就这么治她!枣儿,拜了月,把小白兔眼睛的红豆换了,沾上两颗兔子屎,再叫她尝尝。
蹿个儿的枣儿眼看就要做大姑娘了,长得像秀也像奶奶,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枣儿问:奶奶,姑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
说么呢?咋啦?不像?
枣儿说:我觉得姑姑最可怜啦,你谁都喜欢,就是不喜欢她。
奶奶没吱声。她在大家坐好后,念着儿女兴许还得家来过节,便为安路、安芯各置了一副碗筷。摆放女儿那副碗筷时,她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和树枝间的月光,安芯的筷子上夹着一片月光,碗里则盛满了月光,月光像酒一样,从碗里溢出来了。
在奶奶的指挥下,枣儿和秀双手合十,对着嫦娥姑娘和月亮拜了三拜,最后,奶奶边拜边祷告——
八月十五月正圆,
西瓜月饼敬老天,
敬得老天心欢喜,
一年四季保平安。
奶奶一念叨完,三双被呵斥、拍打了许多回的小手,立即抓住了它们各自觊觎着的月饼。这时,安芯正巧赶到了。她左手拎着沉甸甸的藤篮,右手提着一捆山东大葱和一面袋煎饼,两个巴掌都勒出了红印子。她下班后去接车了,东西是她婶婶托人捎来的。奶奶有些不乐意,可大葱怪招人欢喜的,郁闷着的巡道工眼睛一亮,见着安芯便浑身不自在的于金水也放松了心情,奶奶立刻抽出几棵,剥了皮,也等不得拿去涮涮,就被他俩夺去了。张嘴就咬,还直叫香。
安芯坐下后,给大家说了个事。下班路上,有个秃脑袋的剃头师傅在东站道口拦着她,想买下她的大辫子。安芯对那人已经眼熟了,一上街就见他盯着自己,有时还跟着,吓得安芯直往人堆里躲。于金水说,秃子要辫子做么呢?安芯说,摆设嘛。
庄啊枣啊都乐了。庄儿眨巴眨巴眼,把孩子唱的顺口溜改了词,现编了一段,并教枣儿跟在后面学山东快板,给他伴奏——
剃头师傅本领高,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
脑瓜从来不长毛,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
一手拿把刮蛋刀,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
追得大姑娘没处逃,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
买根辫子脖子上绕,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
绕呀绕,绕得师傅翘辫子,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
逃呀逃,大姑娘变成尼姑了。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
把大家伙儿都笑坏了。奶奶擦着笑出来的泪,说山东快书真是这个味,有人还真想做尼姑呢。
气得安芯踹了庄儿一脚。接着,她给巡道工和于金水倒上酒,说:我给你们唱一首本地民歌吧,这还是那年去525部队看露天电影,在大月亮地里,小于的战友想起牺牲了的小戚,把小戚爱唱的歌哼了几遍,我跟着学会了。庄儿,呱唧呱唧吧。
奶奶说:死妮子,多咱见你在人前唱歌呀,装疯吧。庄儿却瞄住了安芯的藤篮,它先是塞在桌子底下,接着又被安芯放到窗台上了。在很不热烈的掌声中,安芯唱起来——
日头哥哥歇山后,
月光姐姐到村口;
清风牵着姐衣袖,
清泉唱在路尽头。
灯笼火把迎接你,
月光姐姐跟我走;
灯月相翘望,辉光相映红,
月光姐姐你莫怕羞。
杭州和范明明当夜班去了,他俩听不到她的歌唱。歌声却招来了好些邻居。其实,这会儿所有的窗口都在侧耳倾听。杭州妈妈说:啥个地方的歌子呀,收音机里厢从来没听到过,咯几天我们杭州也老是哼哼。张婆子领着双胞胎也下楼了,两个孩子见了秀,亲得直往她怀里扑,张婆子抬头看看自家窗口,轻声说:秀比他俩亲娘还亲呢。
在歌声中,于金水热泪盈眶,对着奶奶喊了声娘,再端起杯一饮而尽,算把干娘正式认下了。秀则夺下了巡道工的酒杯,不让他一个劲地灌自己,直往他碗里夹菜,还递给他一块月饼。巡道工攥着饼,呆呆的。安芯的歌声似乎也因此带着哭腔。
待安芯唱完,奶奶用筷子在巡道工的碗上敲了一下,说:还不饿呀,直发愣,想么呢?
巡道工说:俺听着票车的动静,二十三次十七次都正点到站了,看样子,专列一时半会还来不了,指不定要等到下半夜。不管专列、军列,到了合欢站都得加煤上水,停一阵,这一夜就过去啦。
奶奶说:你还念着它呀。车上坐的大干部要是知道啦,一高兴,没准让你当段长。
巡道工连连叹气。就着月光,奶奶看见他眼里竟有泪光,受到多大委屈似的。奶奶连忙进家,拿了一双刚刚替他做的棉鞋塞在他怀里。奶奶的枕下,有一叠用纸铰的鞋样,其中也包括巡道工的。巡道工扛着铁镐成天在轨道上梭巡,费鞋呢,一年发多少双胶底鞋也不够他穿,好些鞋都是踢石渣踢破的。休息天他穿的是布鞋,可哪个休息天他不也在铁路边溜达?
巡道工说:赶明儿,俺到鹰厦线道口边的山上开块菜地去,种上萝卜白菜。
奶奶问:不吃食堂啦?
不,休息天去种种菜。别叫人看着,笑话俺。休息天也在铁路边转悠,那不是拿热脸贴冷腚吗?
奶奶说:别说气话啦,在铁路边开菜地,还不是恋着铁路吗?
等到大家都撂下筷子,孙庄把个鼓鼓囊囊的纸包往桌上一倒,哗啦,竟是花花绿绿的上海糖果。不是于金水送的,而是安芯藤篮里的。孙庄说:姑姑真小气,买了一篮子糖都舍不得给我们吃,我请你们吃姑姑和于叔叔的喜糖!
安芯急忙伸出双手按住了那堆糖果,冲着孙庄骂道:小坏蛋!往后你别向我要东西!这是别人托我找列车员捎来的,上海糖果不好买,在供应车上每人只限一斤。别人等着结婚呢。
安芯把糖果收拾起来,却给孙枣孙鹰各塞了一把。奶奶说:枣儿鹰儿,还给姑姑,俺不吃别人的东西。俺有于叔叔送的,俺拿去。
说着,奶奶话里有话了:真是出鬼啦,要捎上海糖,不找列车员,找的不是电话员,就是电报员。俺见范家老三也一趟趟地去接车,捎来的也是糖果。这俩大闺女咋啦,你说说?
孙安路不知道,他被选中去跑那趟专列是个意外。跑专列的司机、司炉尤其要经过严格挑选,除了政治可靠,还得技术过硬,段里有三个包乘组专跑保密车,人家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可是,到了节骨眼上,三位大车,两个吃了坏月饼跑肚拉稀,一个好好地走着道,叫从楼房窗口里飞出来的“砸死狗”砸伤了一只眼。都和月饼有关。公安段警惕了,便派人去调查,前者的月饼是从广州捎来的,时间太久长了霉,后者的月饼虽是铁路食堂做的,但砸伤火车司机的,却是当列车员的小两口子,他们用月饼为武器在干仗呢,彼此也是被砸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