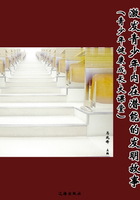且说金玉宇经营私产,为了进货之时可以保证质量、降低成本,在为金家生意进货时,顺带购入私货。待货物运抵都城后,再把私货运往他的私铺,然后把金家的货运入金家货仓。
而他记录货账之时,会按金家货量和私货量,仔细的分记在金家货账和私货账上。至于南边那两家供应商的负责管事,也早已经被他用重金收买,这样在核账结款时,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前阵子他一直守在总商号,等着那两家的管事过来核账,结果收到了他们送来的信,说是这阵子比较忙,核账的事情会延后一个月。他知道短期之内不会有人过来核账结款了,就再不守在总商号发闷,又出去找狐朋狗友去花天酒地了。
却没有想到,不过才出去疯玩了十来日,南边就派了管事们过来核账结款,且来的还不是原来负责的管事,而是没有打过交道的新管事。
这让金玉宇非常的不安,他生怕经营私产的事情,会被金太爷和金玉轩知道。故一路上都心绪不安的想着说辞,想着若是金太爷或是金玉轩问了起来,他要怎么样才可以蒙混过关。
大掌柜这里,早已得了金玉轩的吩咐,所以待金玉宇到后,就把两家的货账交给了他,笑道:“因为一直是大爷负责这两家供应商的,所以大爷不在,我们也不可擅自核账。这两本是他们两家送上的货账,还请大爷拿回去仔细核对,早日把货款结清了,让他们早日回去复命。”
金玉宇此时已经是一身冷汗,轻颤着接过两本货账,小心的问道:“太爷和三爷知道这事儿吗?这两本货账可有人翻看过?”
大掌柜虽然不明白金玉轩的用意,但是金太爷想让金玉轩继承金家产业的想法,他还是猜出了七八分的。故不敢碍了金玉轩的打算,按着他所交代的,陪笑着回道:“太爷和三爷今日一直在忙着商议万宝阁开新分号的事情,所以只吩咐我好好款待那两家的管事们,并没有面见他们。至于这两本货账,因为大爷不在,我也不敢翻看,也不敢让旁人随意翻看。必竟这货账在咱们行商的人来说,是需要严加保密的贵重之物。”
金玉宇听了这话,悬着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不耐烦的摆了摆手,吩咐道:“好了,我知道了。今日天色已深了,想来那两家派来的人也睡下了,这核账结款的事情,等我明日过来再说吧。今日既然是大掌柜坐号值夜,我也就不打扰了,大掌柜也早些休息,守夜的事情,交给那些伙计们就是了。”
大掌柜笑着答应一声,恭敬的送金玉宇出了总商号,方回去按排好晚上坐号值夜的伙计们,盯着伙计们关好了总商号和后院所有的门窗,才松下口气的回到屋子里歇息。
再说冰院这里,君雪绮一觉睡到近晌午方醒了过来,在沈嬷嬷的千哄万劝之下,略用了一些午饭,就又无精打采的歪在西暖阁的炕榻上,透过敞开的窗子,看着奶娘和丫鬟们,哄着玲姐儿和笛哥儿在院子里玩闹。
沈嬷嬷见君雪绮看着孩子们嬉闹,精神好了一些,便将正厢里的月灵和水灵打发了出去,然后在炕榻上坐下,笑劝道:“奶奶,如今您有了身子,是不能与三爷同房的。三爷这往书厢一搬,就要在那里住到奶奶十二月里出了月子,才能再搬回来的。依婆子的浅见,奶奶要不要考虑,给三爷收房侍妾,也好有个贴心的人,帮着奶奶伏侍三爷。”
君雪绮听到这里,脸上原本带着的淡淡笑意,就收敛了起来。沈嬷嬷之言,早在君太太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劝了她几次。
那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与其让金玉轩出去偷腥,再招了别的女子进门,或是让西跨院里的柳玲兰得机受宠,不如提拔个贴心的自己人。这样往后,她身边也能多一个膀臂,就算将来失了夫君的疼宠,也有个自己人帮她拢住金玉轩。
只是她心里的想法,倒是与君太太和沈嬷嬷不同的。不管是不是自己人,只要是女人,就不会愿意与别的女人共侍一夫。就算她在贴心的丫鬟中提拔一个侍妾,往后也会渐渐因为她夫君的女人的关系,让她觉得厌恶。
与其让她亲自给金玉轩挑选女人,然后往后与几个女人争夺夫君的宠爱,她倒宁愿让柳玲兰借机受宠。必竟柳玲兰的存在,是她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情,而还不存在的那些女人,却是她可以阻止的事情。让她在往后的日子里,与不止一个女人争宠,她宁可终其一生,只与柳玲兰一人争个高下。
再者,她已经是要作母亲的人了,总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子女的嫡庶之别,还有嫡庶之间的家产之争,一直都是富裕之家难以避免的纷争。说她有私心也好,就算为了她的子女,她也不想让金玉轩有太多的女人。
君雪绮想罢,笑对沈嬷嬷道:“妈妈,这事儿就算了吧。三爷夜里若是寂寞,自有柳姨娘去伏侍他,侍妾之事就不要再提了。”
沈嬷嬷以为君雪绮只是小性子,不清楚此事的重要性,故苦口婆心的劝了好些话,又道:“奶奶,像三爷这样的男子,那可是有好多女人盯着呢。与其让那些不三不四不知底细的贴上来,倒不如奶奶放个人过去。既有人帮着奶奶看着三爷,又能显出奶奶的贤惠来。可若是让柳姨娘得了这个好处,那可是要出大麻烦的。必竟柳姨娘已经有了笛哥儿这个儿子了,若是再让她怀上了,她往后的底气可就要更足了。”
君雪绮无奈的摇了摇头,苦笑道:“此事就这么定了,妈妈也不要再劝了,往后也不要再提起来。如今一个柳玲兰就已让我很是头疼了,我可不想再招几个柳玲兰进来。我累了,想静静的躺一躺,妈妈出去忙吧。”
沈嬷嬷见状,心里虽然着急,却也是没有办法了。只得苦叹一声,欲言又止的看了看君雪绮,方摇着头出了正厢。
君雪绮待沈嬷嬷走了,方松开一直紧握着的双手,轻抚了抚尚未鼓起来的肚子。
女人总是这样的,先是为了夫君着想,再是为了子女着想,日子过得永远都是战战兢兢的。大户人家的,愁的着妻妾之斗、子嗣之争、家产之夺。而那些小户人家的,愁的就是柴米油盐、房屋地亩。
都说男人在外创业艰辛、养家不易,可女人在内要思虑、要谋算的事情,又哪里是轻松容易的呢?
这晚,因为金玉轩留在家里陪伴君雪绮,所以金老爷跟着金太爷出去赴受邀的寿宴,回到霜院时,已然是微醺了。
苏夫人带着李嬷嬷和丫鬟们伏侍金老爷洗漱、更衣后,就打发了她们出去,哄着金老爷上床歇息。
谁知金老爷虽喝多了酒,却并没有喝醉,所以不仅没有困倦之感,反而精神的睡不着觉,拉着苏夫人聊起了家常体己话。
苏夫人见金老爷精神好,便拉着他笑道:“有件事儿,自玉轩媳妇有喜后,我就一直在琢磨着。总想着跟老爷好好商议商议,偏这阵子老爷忙着各铺子里的事情,也没有个闲工夫。今儿晚上倒是个好时候,我说出来,老爷细想想,看可行不可行。”
金老爷见苏夫人一脸严肃,便知道她要说的绝非小事,故坐起身子,一面温柔的为苏夫人盖好被子,一面正色问道:“何事让夫人如此发愁?”
苏夫人笑回道:“玉文的身子骨,老爷是比我都清楚的。邓氏嫁进门来也有九年了,又有可人和蓝玉两个侍妾,可玉文至今在子嗣上也没有消息。如今托了老太太的福,纳了欣月那孩子为姨娘,也不知道能不能给玉文带来一儿半女的。我私心里想着,等咱们老俩口没了,他们兄弟就是不分家,也是各房是各房的。玉轩下面儿女双全,玉文下面若悬空着,也不是个法子。说句忌讳的话,总也要有个儿子给玉文摔盆披麻才是。所以我想着,若是待玉轩有了嫡子,玉文还没有子嗣,那就把笛哥儿过继给玉文吧。他们是亲兄弟,与其去过继别人的孩子,不如过继玉轩的。老爷觉得呢?”
金玉文的子嗣之事,金老爷也是愁了许多年的。过继之事,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没想要过继金玉轩的,想的是从金家族里挑个寒门的。
如今听了苏夫人之言,金老爷也觉得很有道理,与其去族里挑选,莫不如过继金玉轩的。必竟以金玉文的身子骨,往后他们兄弟定是分不了家的,里外的事务只能由金玉轩夫妇去料理。
只是一想到柳玲兰,再想到柳夫人和柳氏,金老爷就有些头疼,苦笑道:“你说得倒是轻巧。要知道,玉轩就算是点了头,那个柳氏也不见得会愿意的。到时候,若再扯上大嫂和玉宇媳妇,那家里又要不得安宁了。”
苏夫人冷笑道:“老爷这话说错了,过继之事是咱们二房的家务事,要说老太爷和老太太阻挠还说得过去,可若说要听从着长房的来,却是有些过了的。再者,玉文的子嗣之事并非小事,总也要为他和邓氏着想着想。别的兄弟们都儿女绕膝,偏就他们夫妻膝下悬空,难道长房当大伯、大伯母的就忍心吗?至于那个柳氏,不过是个偏房妾室,难道我这个当太太的,还要看她的脸色行事吗?况且,就是不过继笛哥儿,那孩子也是要由嫡母正室教养的,怎么都不可能养在妾室身边。她若真为了笛哥儿着想,也该在过继之事上点头。必竟去了玉文那里,笛哥儿就是嫡出,可若留在玉轩那里,他就只是个庶出罢了。”
金老爷也知道苏夫人所说在理,只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故苦叹道:“这事儿先放放,总也要等玉轩有了嫡子再说。你就别着急了,咱们睡吧。”
苏夫人也跟着苦叹了一声,点了点头,翻身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