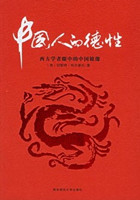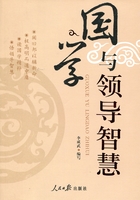世之为谗诬诽谤者,不特施之于生者,而或且施之于死者,其情更为可恶。盖生者尚有辨白昭雪之能力,而死者则并此而无之也。原谗诬诽谤之所由起,或以嫉妒,或以猜疑,或以轻率。夫羡人盛名,吾奋而思齐焉可也,不此之务,而忌之毁之,损人而不利己,非大愚不出此。至于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因人一言一行,而辄推之于其心术,而又往往以不肖之心测之,是徒自表其心地之龌龊耳。其或本无成见,而嫉恶太严,遇有不协于心之事,辄以恶评加之,不知人事蕃变,非备悉其始末,灼见其情伪,而平心以判之,鲜或得当,不察而率断焉,因而过甚其词,则动多谬误,或由是而贻害于社会者,往往有之。且轻率之断定,又有由平日憎疾其人而起者。憎疾其人,而辄以恶意断定其行事,则虽名为断定,而实同于谗谤,其流毒尤甚。故吾人于论事之时,务周详审慎,以无蹈轻率之弊,而于所憎之人,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夫人必有是非之心,且坐视邪曲之事,默而不言,亦或为人情所难堪,唯是有意讦发,或为过情之毁?则于意何居。古人称守口如瓶,其言虽未必当,而亦非无见。若乃奸宄之行,有害于社会,则又不能不尽力攻斥,以去社会之公敌,是亦吾人对于社会之本务,而不可与损人名誉之事,同年而语者也。
(第五节 博爱及公益)
博爱者,人生至高之道德,而与正义有正负之别者也。行正义者,能使人免于为恶;而导人以善,则非博爱者不能。
有人于此,不干国法,不悖公义,于人间生命财产名誉之本务,悉无所歉,可谓能行正义矣。然道有饿莩而不知恤,门有孤儿而不知救,遂得为善人乎?
博爱者,施而不望报,利物而不暇己谋者也。凡动物之中,能历久而绵其种者,率恃有同类相恤之天性。人为万物之灵,苟仅斤斤于施报之间,而不恤其类,不亦自丧其天性,而有愧于禽兽乎?
人之于人,不能无亲疏之别,而博爱之道,亦即以是为序。不爱其亲,安能爱人之亲;不爱其国人,安能爱异国之人,如曰有之,非矫则悖,智者所不信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博爱之道也。
人人有博爱之心,则观于其家,而父子亲,兄弟睦,夫妇和;观于其社会,无攘夺,无忿争,贫富不相蔑,贵贱不相凌,老幼废疾,皆有所养,蔼然有恩,秩然有序,熙熙暤暤,如登春台,岂非人类之幸福乎!
博爱者,以己所欲,施之于人。是故见人之疾病则拯之,见人之危难则救之,见人之困穷则补助之。何则?人苟自立于疾病危难困穷之境,则未有不望人之拯救之而补助之者也。
亦子临井,人未有见之而不动其恻隐之心者。人类相爱之天性,固如是也。见人之危难而不之救,必非人情。日汨于利己之计较,以养成凉薄之习,则或忍而为此耳。夫人苟不能挺身以赴人之急,则又安望其能殉社会、殉国家乎?华盛顿尝投身奔湍,以救濒死之孺子,其异日能牺牲其身,以为十三州之同胞,脱英国之轭,而建独立之国者,要亦由有此心耳。夫处死生一发之间,而能临机立断,固由其爱情之挚,而亦必有毅力以达之,此则有赖于平日涵养之功者也。
救人疾病,虽不必有挺身赴难之危险,而于传染之病,为之看护,则直与殉之以身无异,非有至高之道德心者,不能为之。苟其人之地位,与国家社会有重大之关系,又或有侍奉父母之责,而轻以身试,亦为非宜,此则所当衡其轻重者也。
济人以财,不必较其数之多寡,而其情至为可嘉,受之者尤不可不感佩之。盖损己所余以周人之不足,是诚能推己及人,而发于其友爱族类之本心者也。慈善之所以可贵,即在于此。若乃本无博爱之心,而徒仿一二慈善之迹,以博虚名,则所施虽多,而其价值,乃不如少许之出于至诚者。且其伪善沽名,适以害德,而受施之人,亦安能历久不忘耶?
博爱者之慈善,唯虑其力之不周,而人之感我与否,初非所计。即使人不感我,其是非固属于其人,而于我之行善,曾何伤焉?若乃怒人之忘德,而遽彻其慈善,是吾之慈善,专为市恩而设,岂博爱者之所为乎?唯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为不德,尤易见耳。
博爱者,非徒曰吾行慈善而已。其所以行之者,亦不可以无法。盖爱人以德,当为图永久之福利,而非使逞快一时,若不审其相需之故,而漫焉施之,受者或随得随费,不知节制,则吾之所施,于人奚益?也固有习于荒怠之人,不务自立,而以仰给于人为得计,吾苟堕其术中,则适以助长其依赖心,而使永无自振之一日。爱之而适以害之,是不可不致意焉。
夫如是,则博爱之为美德,诚彰彰矣。然非扩而充之,以开世务,兴公益,则吾人对于社会之本务,犹不能无遗憾。何则?吾人处于社会,则与社会中之人人,皆有关系,而社会中人人与公益之关系,虽不必如疾病患难者待救之孔亟,而要其为相需则一也,吾但见疾病患难之待救,而不顾人人所需之公益,毋乃持其偏而忘其全,得其小而遗其大者乎?
夫人才力不同,职务尤异,合全社会之人,而求其立同一之功业,势必不能。然而随分应器,各图公益,则何不可有之。农工商贾,任利用厚生之务;学士大夫,存移风易俗之心,苟其有裨于社会,则其事虽殊,其效一也。人生有涯,局局身家之间,而于世无补,暨其没也,贫富智愚,同归于尽。唯夫建立功业,有裨于社会,则身没而功业不与之俱尽。始不为虚生人世,而一生所受于社会之福利,亦庶几无忝矣。所谓公益者,非必以目前之功利为准也。如文学美术,其成效常若无迹象之可寻,然所以拓国民之智识,而高尚其品性者,必由于是。是以天才英绝之士,宜超然功利以外,而一以发扬国华为志,不蹈前人陈迹,不拾外人糟粕,抒其性灵,以摩荡社会,如明星之粲于长夜、美花之映于座隅,则无形之中,社会实受其赐。有如一国富强,甲于天下,而其文艺学术,一无可以表见,则千载而后,谁复知其名者?而古昔既墟之国,以文学美术之力,垂名百世,迄今不朽者,往往而有,此岂可忽视者欤?
不唯此也,即社会至显之事,亦不宜安近功而忘远虑,常宜规模远大,以遗饷后人,否则社会之进步,不可得而期也。是故有为之士,所规画者,其事固或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其利亦能历久而不渝,此则人生最大之博爱也。
量力捐财,以助公益,此人之所能为,而后世子孙,与享其利,较之饮食征逐之费,一啕而尽者,其价值何如乎?例如修河渠,缮堤防,筑港埠,开道路,拓荒芜,设医院,建学校皆是。而其中以建学校为最有益于社会之文明。又如私设图书馆,纵人观览,其效亦同。其他若设育婴堂、养老院等,亦为博爱事业之高尚者,社会文明之程度,即于此等公益之盛衰而测之矣。
图公益者,又有极宜注意之事,即慎勿以公益之名,兴无用之事是也。好事之流,往往为美名所眩,不审其利害何若,仓卒举事,动辄蹉跌,则又去而之他。若是者,不特自损,且足为利己者所借口,而以沮丧向善者之心,此不可不慎之于始者也。
又有借公益以沽名者,则其迹虽有时与实行公益者无异,而其心迥别,或且不免有倒行逆施之事。何则?其目的在名。则苟可以得名也,而他非所计,虽其事似益而实损,犹将为之。实行公益者则不然,其目的在公益。苟其有益于社会也,虽或受无识者之谤议,而亦不为之阻。此则两者心术之不同,而其成绩亦大相悬殊矣。
人既知公益之当兴,则社会公共之事物,不可不郑重而爱护之。凡人于公共之物,关系较疏,则有漫不经意者,损伤破毁,视为常事,此亦公德浅薄之一端也。夫人既知他人之财物不可以侵,而不悟社会公共之物,更为贵重者,何欤?且人既知毁人之物,无论大小,皆有赔偿之责,今公然毁损社会公共之物,而不任其赔偿者,何欤?如学堂诸生,每有抹壁唾地之事,而公共花卉,道路荫木,经行者或无端而攀折之,至于青年子弟,诣神庙佛寺,又或倒灯复瓮,自以为快,此皆无赖之事,而有悖于公德者也。欧美各国,人人崇重公共事物,习以为俗,损伤破毁之事,始不可见,公园椅榻之属,间以公共爱护之言,书于其背,此诚一种之美风,而我国人所当奉为圭臬者也。国民公德之程度,视其对于公共事物如何,一木一石之微,于社会利害,虽若无大关系,而足以表见国民公德之浅深,则其关系,亦不可谓小矣。
(第六节 礼让及威仪)
凡事皆有公理,而社会行习之间,必不能事事以公理绳之。苟一切绳之以理,而寸步不以让人,则不胜冲突之弊,而人人无幸福之可言矣。且人常不免为感情所左右,自非豁达大度之人,于他人之言行,不慊吾意,则辄引似是而非之理以纠弹之,冲突之弊,多起于此。于是乎有礼让以为之调合,而彼此之感情,始不至于冲突焉。
人之有礼让,其犹车辖之脂乎,能使人交际圆滑,在温情和气之间,以完其交际之本意。欲保维社会之平和,而增进其幸福,殆不可一日无者也。
礼者,因人之亲疏等差,而以保其秩序者也。其要在不伤彼我之感情,而互表其相爱相敬之诚,或有以是为虚文者,谬也。
礼之本始,由人人有互相爱敬之诚,而自发于容貌。盖人情本不相远,而其生活之状态,大略相同,则其感情之发乎外而为拜揖送迎之仪节,亦自不得不同,因袭既久,成为惯例,此自然之理也。故一国之礼,本于先民千百年之习惯,不宜辄以私意删改之。盖崇重一国之习惯,即所以崇重一国之秩序也。
夫礼,既本乎感情而发为仪节,则其仪节,必为感情之所发见,而后谓之礼。否则意所不属,而徒拘牵于形式之间,是刍狗耳。仪节愈繁,而心情愈鄙,自非徇浮华好谄谀之人,又孰能受而不斥者。故礼以爱敬为本。
爱敬之情,人类所同也,而其仪节,则随其社会中生活之状态,而不能无异同。近时国际公私之交,大扩于古昔,交际之仪节,有不可以拘墟者,故中流以上之人,于外国交际之礼,亦不可不致意焉。
让之为用,与礼略同。使人互不相让,则日常言论,即生意见,亲旧交际,动辄龃龉。故敬爱他人者,不务立异,不炫所长,务以成人之美。盖自异自炫,何益于己,徒足以取厌启争耳。虚心平气,好察迩言,取其善而不翘其过,此则谦让之美德,而交际之要道也。
排斥他人之思想与信仰,亦不让之一也。精神界之科学,尚非人智所能独断。人我所见不同,未必我果是而人果非,此文明国宪法,所以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之则也。苟当讨论学术之时,是非之间,不能异立,又或于履行实事之际,利害之点,所见相反,则诚不能不各以所见,互相驳诘,必得其是非之所在而后已。然亦宜平心以求学理事理之关系,而不得参以好胜立异之私意。至于日常交际,则他人言说虽与己意不合,何所容其攻诘,如其为之,亦徒彼此忿争,各无所得已耳。温良谦恭,薄责于人,此不可不注意者。至于宗教之信仰,自其人观之,一则为生活之标准,一则为道德之理想,吾人决不可以轻侮嘲弄之态,侵犯其自由也。由是观之,礼让者,皆所以持交际之秩序,而免其龃龉者也。然人固非特各人之交际而已,于社会全体,亦不可无仪节以相应,则所谓威仪也。
威仪者,对于社会之礼让也。人尝有于亲故之间,不失礼让,而对于社会,不免有粗野傲慢之失者,是亦不思故耳。同处一社会中,则其人虽有亲疏之别,而要必互有关系,苟人人自亲故以外,即复任意自肆,不顾取厌,则社会之爱力,为之减杀矣。有如垢衣被发,呼号道路,其人虽若自由,而使观之者不胜其厌忌,可谓之不得罪于社会乎?凡社会事物,各有其习惯之典例,虽违者无禁,犯者无罚,而使见而不快,闻而不慊,则其为损于人生之幸福者为何如耶!古人有言,满堂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则举座为之不欢,言感情之相应也。乃或于置酒高会之时,白眼加人,夜郎自大,甚或骂座掷杯,凌侮侪辈,则岂非蛮野之遗风,而不知礼让为何物欤。欧美诸国士夫,于宴会中,不谈政治,不说宗教,以其易启争端,妨人欢笑,此亦美风也。
凡人见邀赴会,必预审其性质如何,而务不失其相应之仪表。如会葬之际,谈笑自如,是为幸人之灾,无礼已甚,凡类此者,皆不可不致意也。
(第四章 国家)
(第一节 总论)
国也者,非徒有土地有人民之谓,谓以独立全能之主权,而统治其居于同一土地之人民者也。又谓之国家者,则以视一国如一家之故。是故国家者,吾人感觉中有形之名,而国家者,吾人理想中无形之名也。
国为一家之大者,国人犹家人也。于多数国人之中而有代表主权之元首,犹于若干家人之中而有代表其主权之家主也。家主有统治之权,以保护家人权利,而使之各尽其本务。国家亦然,元首率百官以统治人民,亦所以保护国民之权利,而使各尽其本务,以报效于国家也。使一家之人,不奉其家主之命,而弃其本务,则一家离散,而家族均被其祸。一国之民,各顾其私,而不知奉公,则一国扰乱,而人民亦不能安其堵焉。
凡有权利,则必有与之相当之义务。而有义务,则亦必有与之相当之权利,二者相因,不可偏废。我有行一事保一物之权利,则彼即有不得妨我一事夺我一物之义务,此国家与私人之所同也。是故国家既有保护人之义务,则必有可以行其义务之权利;而人民既有享受国家保护之权利,则其对于国家,必有当尽之义务,盖可知也。
人之权利,本无等差,以其大纲言之,如生活之权利,职业之权利,财产之权利,思想之权利,非人人所同有乎!我有此权利,而人或侵之,则我得而抵抗之,若不得已,则借国家之权力以防遏之,是谓人人所有之权利,而国家所宜引为义务者也。国家对于此事之权利,谓之公权,即国家所以成立之本。请详言之。
权漫无制限,则流弊甚大。如二人意见不合,不必相妨也,而或且以权利被侵为口实。由此例推,则使人人得滥用其自卫权,而不受公权之限制,则无谓之争阋,将日增一日矣。
于是乎有国家之公权,以代各人之自卫权,而人人不必自危,亦不得自肆,公平正直,各得其所焉。夫国家既有为人防卫之权利,则即有防卫众人之义务,义务愈大,则权利亦愈大。故曰:国家之所以成立者,权力也。
国家既以权力而成立,则欲安全其国家者,不可不巩固其国家之权力,而慎勿毁损之,此即人民对于国家之本务也。
(第二节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