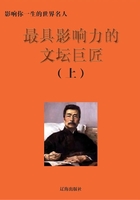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这是中国佛教初期的情况。当时佛教的发展,只限于北方,但从第五代弘忍之后,分裂为南北两派即南宗、北宗;北宗以神秀为主,南宗以惠能为主。他俩都是弘忍的徒弟。后来惠能弟子神会北伐,经过一番奋斗,又恢复了正统。
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根据史料排除各种传说和神话,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肯定达摩是一个历史人物,其事迹、年代也大体考出还较近乎情理,因此为研究禅学史打下一个基础。这是他的贡献。
《荷泽大师神会传》是胡适根据《神会语录》及其他材料写成的。他说:在禅宗的历史上,神会和尚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应当继承禅宗正统的,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都往往忽略了他,结果却是两个无名的和尚(行思与怀让)依靠后辈的势力成为禅宗正统!这是历史上一件最不公平的事。胡适写此传不仅恢复神会的历史地位,而且还理顺了禅宗的历史。现略述如下: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摩为第一代,惠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弘忍为第五代;但法统传到第五代后,就发生问题了。那时,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他门下有两个大徒弟:一个有学问,名叫神秀;另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名叫惠能。门徒们认为,老师的衣钵,准会传给神秀的,因而对于外来的和尚惠能却有点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有一天,弘忍法师想传法,于是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和尚诗),看谁作得好,就把衣钵传给他。当时,神秀作了一偈,写在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弘忍看了觉得不错,认为一个人修行能达此境界也算难得,有意将法传给他。不料正当众僧徒议论纷纷的时候,惠能从厨房里走将出来,也口占一偈,请人题在墙上。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看了,说:不行!接着脱下鞋,将偈擦掉。但到了半夜,他却亲自到厨房,将法传给惠能,并叫他快逃走,躲过几年,方可传道。第二天,众僧知道五祖已将法传给惠能都很惊讶,急忙去追,但已追之不及了。
惠能到广东后,遵师之嘱躲了几年,才敢公开出来传道,那时,神秀在北方自称六祖,很有势力,颇受朝廷的尊重,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就是东京洛阳西京长安;三帝就是武则天、中宗、睿宗),并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而惠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惠能原是广东新州人,后来住韶州曹溪,人们称他为“曹溪派”,又称“南宗”,故有“南能北秀”之说。他所提倡的教义是易行的“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这与北宗教义主张“渐修”,教人坐禅、面壁、受苦修行形成尖锐的对立,所以胡适称南宗为革命派,并认为这是中国禅学之始。而北宗是沿袭印度佛教的,故称之为印度禅。
那时,湖北襄阳地方有个姓高的,大约在唐睿宗景云元年,为了想学禅不以千里为远南下到曹溪拜惠能为师。惠能收留了他,并赐名为神会。后来惠能死后,他便北上到河南滑台传道,并大胆宣称:北方神秀一派的法统是假的。他说,五祖弘忍传法给他师父惠能,有袈裟在韶州为证,因此他们才是正统。并指斥北宗普寂妄图坚其师神秀为第六祖,而自称第七祖,他要誓死反对。与此同时,他竭力宣讲南宗教义,大讲“顿悟”的功能,力排北宗教义“渐修”之繁琐,当时很受听众欢迎。但北宗和尚势力浩大,且得朝廷的支持,因此神会被赶出东京黜居江西、湖北一带,过着流浪生活。后来,安史之乱,两京陷落,明皇出走,太子即位;至唐肃宗至德二年,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神会才有机会回到东京。那时大乱初定,国家财政困难,朝中有人提出出卖度牒(即作和尚的执照;有了它不仅可以当和尚,还可免除各种租税),增加收入,但这种“公债”无法推销,非得请一位善于宣传的和尚不可,于是大家想到很有口才的神会,请他出来负责此事。这时他已90高龄,搭棚设坛,大肆鼓吹,听众深受感动,剃发买牒者极多;100吊钱一张,政府得到了大宗收入。神会有功,唐肃宗下诏叫他入内供养,并替他建造禅院于荷泽寺中,到公元762年死去,活了93岁。后来朝廷下敕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神会经历千辛万苦的北伐终于成功了,于是惠能的南宗便成为禅宗的正统了。胡适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评论道:“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又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却被埋没了1000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900年的隐晦,还保存2万多字,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而重写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胡适在这方面的贡献了,他不仅为写中古哲学史找到材料,而且还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开一新局面,这些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日本京都花园大学教授柳田圣山(日本佛学权威)说:“博士的禅学论文,其主要者限于禅宗史的初期,旨在阐明从来研究之不明处和被歪曲处。在意义深长的热情和武断的结论里曙光出现,恰与肩负现代史苦恼的伟大硕学影像相映着。”又说:“时至今日,对中国禅学作研究的人,在相当期间还不能忽视胡适的遗业。”其次,有关胡适论禅学的文章,在法国、美国均有翻译本。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
胡适后来总结治学经验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说,小心的求证。”不过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地批评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的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因此,他提出寻找材料应当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
总的说来,胡适对此次欧洲之行,收获不小,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他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里说: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惠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另方面,关于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事,开过几次会,做了一些计划,如款子的用途、董事会的组织等等,写成意见向中英政府报告,并由双方政府任命人员组成董事会。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二项任务了。在完成学术研究之后,他又应邀到英国各大学去作学术演讲,大约有十来处,讲题为《中国近一千年来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这些活动对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促进文化交流,均起到应有的作用。据当时留英学生叶元在回忆说:“我在那年9月间到了伦敦。他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我每天上完了课以后总要去看他。我还陪他常常去吃中国饭。那时候他的客很多,英国的在朝和在野的名流都以一见他为荣。经过伦敦的日本学者也都去看他。后来旅馆里一位女侍者知道了他的身份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位女侍者竟要他‘刻思’她。”由此可见他在英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又到柏林、巴黎讲学,所到之处中国留学生来访者甚多。但在巴黎却遇见了一桩不愉快的事。那时“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竟发了一张传单,题为《警告旅欧华侨同胞》,其内容大意为,胡适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走狗,要大家提高警惕,严密探察他来欧所干的勾当。并称我们将要宣布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这张传单是在巴黎万花楼饭馆散发的。那天在法留学的傅孟真、梁宗岱等人请胡吃饭。胡适去得晚,只见门口饭馆的老板张楠在等人,一见胡来便劝他不要进去,说是里面有他的传单。胡适不在乎,笑着对张说我来吃饭,不要紧,也想看看传单。胡进去后与傅孟真等人一起吃饭,大家都未提及此事。饭后出门到一个小咖啡馆休息。这时胡适才问,看见传单了没有?傅孟真说,我们把传单收起来了,怕你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于是大家把传单交给了他。后来胡适保留了一份,有的寄给了友人看看。这事就这样收场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呢?这可从国内张慰慈的回信里得到答案。张收到胡寄来的传单后,回信安慰他说:那张警告接到了。这是“胡闹”,走狗这个名称,怎么会加到你的头上。真是莫名其妙的笑话。推其原因,张慰慈说:在君(即丁文江,当时在孙传芳手下任上海商埠总办)近来非常厉害,他一下子就封了15个国民党的机关,大概你的新名词是靠了在君的福得到的。劝他不要吃眼前亏,最好巴黎、柏林少住为是。胡适接到张的来信以后,不久又接到清华友人钱端升的长函。信里先谈的是别后感,钱说:“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我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接着讲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预备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做经理,希望他能返国来清华当校长整顿这个学校。这事如果胡适同意,他们可以建议有关方面聘请,并称,“只消你说你愿意考虑我的建议,我便想法宣传;这个宣传功夫当然不至十分费力,因为太多数人是十分希望你来的。”胡适在来函上,批注云:我愿意考虑你的提议;却十分不愿意你去设法宣传。这是我的答复。请谅解此意。这可能是他回信的大意,及其对此事的态度。这时,北大方面如王世杰、周鲠生等一班朋友也都希望他能够在寒假中赶回北大,进行大学内部改组计划,宣称这一层又非你在此地很难办到的。又说:“你如能早些回来,确实很能做些事,至少能供给我们一种领导能力,你以为如何?”
胡适此行,原有计划应聘留在英国大学里教书的,后来英方对华态度骤然变更,这使他在英国的兴头一落千丈。所以钱端升在信里劝勉他说:我们本来希望你在英国大学界中占一地位,替中国从文化方面表扬表扬,间接也可以收一点政治上的效果。谁知英国的面孔又变长了呢?在外国没有意思,还是回到中国来罢。这时的胡适已感到外国异邦终非久留之地,于是准备回国,抖擞精神重新再干一番事业,故于是年12月31日乘船离英,取道美洲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