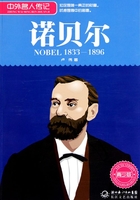同年5月胡适作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在《新青年》(四卷六号)上。这期为易卜生专号,胡的文章除上述外,还与罗家伦合译了《娜拉》;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翻译了《小爱友夫》。从上述情况看,这期很可能是由胡适主编的。他在文章里说: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是挪威资产阶级主张改良社会的剧作家,胡适等人竭力推崇他,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这对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在争取女权,提倡男女平等方面,娜拉的形象给人们以巨大的力量。那时“娜拉”的地位,在某些地方是超过了孔夫子。1928年《小说月报》计划为这位作家举行百周年纪念。之前一年的12月,该报的编辑叶绍钧曾要求胡适写纪念文章,他在信中说:“明年3月为易卜生百周岁纪念。小说月报拟载几篇关于他的文字。先生介绍易卜生最早,又是最有力的人,那篇《易卜生主义》可谓已深入人心。敢恳抽些工夫,为月报特撰一文……”可见胡适这篇《易卜生主义》在当时很有影响。后来在学生运动中他介绍给学生,那就起了反作用的了,比如: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就劝学生说:“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这就是一个例。
是年9月,皖系军阀段祺瑞御用国会在北京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段以参战军督办名义继续控制北京政府。这件事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胡适对此也是不满。10月25日他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曾琦写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作序时说:“今年总算是中华民国的大选举的一年:有省议会选举,有国会的选举,又有大总统的选举。但是我们中国青年却完全是不曾与闻,这种大选举,完全由几路财神和一班武人随意支配,糊里糊涂的就派出十几个省议会和一个新国会来了,由这个财神、武人、政客派出的国会里,又糊里糊涂举出一个大总统来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真容易做!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肩上的担子真轻!”又说:“今年的省议会选举和国会选举乃是中华民国的大耻羞!这种耻羞比日本的廿一款大得多呢。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应该知道这种政治腐败黑暗别无他种救济的方法,只有一条方法,须要全国青年出来竭力干涉各地的选举,须要全国青年出来做各地选举的监督。……”胡适原有信条,不谈政治,只谈文化,但形势逼人,当时的“事”,当时的“书”,都是要他表态的。出于爱国的热忱,他无所顾忌批评了国政,并号召青年们起来肩负国家重担,作主人对政府实行监督。这些民主言论在客观上对当时的青年是有影响的。
这年冬天12月《每周评论》出版了。因胡适不主张在《新青年》上谈政治,而且有20年不谈政治的话。他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专致力于新文化的运动,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陈独秀与***等对此不以为然,故另创了这个刊物,主旨在评论时政,传播马克思学说及社会主义等。这时胡适正返乡办理母丧不在北京。从这中间可看出《新青年》的同人们,思想上已经出现分歧了。
1919年初胡适返京,对此未加可否,只在上面发表过几篇翻译文章应付一下。
同年3月,陈独秀因细行不检,在北大受到攻击,于是他向校中请长假,蔡元培校长借撤销文科学长之故解其职。留他充史学系教授给假一年,准备开一门宋史课。但终未应聘。之后,他专心致力于《每周评论》。5月7日他写信给上海的胡适,向他报告北京“五四”运动的经过情况,并说:“现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接着又说,“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可见当时统治者对《每周评论》是视为眼中钉了。6月陈因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革命传单被捕。胡适代他做主编工作,直到8月该刊被封为止。在这期间,胡适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批评当时舆论界传播社会主义等学说的现象,实际是针对着***而说的。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又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是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胡这篇文章出笼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在家乡昌黎也著文批驳,并公开声明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札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E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又说:“我觉得布尔札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胡适听不进去,仍坚持己见,著文答辩。8月30日因刊物被查封,争论也就不了了之。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第7期回顾这段往事说:“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可见胡适不谈政治则已,一谈就是要从根本上谈起,用个别代替一般,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其实质是以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其影响很坏。从此后《新青年》内部矛盾日愈加深,分裂渐渐表面化了。陈独秀由于各方面的营救,被关了83天释放。
陈出狱后,仍在北京居住,翌年初,代胡适到武汉去讲学。讲演完毕,在当地文华大学、中华大学等校的校长陪同下返回北京。这几位校长到京目的之一,是要物色几位“新文化”的教授,并要会晤胡适。不料他刚到不久警察就来敲门了,问:陈独秀先生在家吗?“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陈的回答倒使警察吃一惊。警察说现在市上一些报纸报道说陈先生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上司不知,所以派我们来看看,陈先生是否还在家中。陈回答说:我是在家中呀!那位警察若有所思地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陈答: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警察想要个证明,问您能不能给我们一张名片呢?陈唯诺从命,由口袋里摸了一张给他。警察走后,陈觉得事情不对,估计他们还会回来,于是暂避于胡适家。但因陈、胡关系太密切,可能被搜捕,故又转到东四三条50号***家中。之后,在李的护送下,离开了北京到李的老家乐亭县,不久南下上海。从此陈便与北大胡适等人分道扬镳了。陈独秀后来在上海继续办《新青年》,尽管他与胡适等有分歧,但还是合作办刊物。胡适仍继续供稿,不过多是一些诗词而已。1920年冬,陈到广州,曾请陈望道接办《新青年》。那时,陈给胡适信说:“来函敬悉,大作已载新青年八卷五号了。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八卷四号以前,我绝对是个读者,五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见进行……”从这封信里,可看出其内部的矛盾是难以调和了。所以后来陈将《新青年》迁至广州,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性的机关刊物继续出版。据胡适在其口述日记里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陈、胡之间,政见不合,后来各行其道,但个人友谊仍是很好的。1920年冬,陈结婚时请胡做证婚人。当时,胡有演说,事后又作了一副对联:“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请章士钊书写,代为转贺。因对联有语病,章提出修改。1920年11月24日他写信给胡适说:“对文甚好,我已经照写。但是若有人下一转语,恐怕有点语病,何也?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转语即是:出洞房入监狱,次离别后团圆。我们祝贺人家的新婚,同时隐射人生中一段挫折,怕的是出误解,你证婚时演说,说到独秀的话,‘出监狱入研究室,出研究室入监狱。’我就担忧,有人将你的意思,联思到‘出洞房入监狱’一点,这或者是我神经过敏的地方,但是你以为然,请把这副对联不用,由我另办一副,请你另做一首对文、交我补写,你看好不好?……”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陈胡的友谊,他们在生活上也是十分有趣的。他俩在新文化运动史上都有巨大贡献,当时被人们称为“圣人”,但性格却很不一样。陈比较豪爽、直率,胡则机灵,柔和。鲁迅对他俩曾作过比较。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一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这话值得玩味。足见他二人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刚,一个是柔,但他们还能合作共事,后来尽管政见不同,但友谊是长存的。1923年12月3日汪原放致胡适信云:“仲甫先生前日说不日要到北京一行,你们又可时常见面了。他来时,无时不问起你的身体康健与否。我们无不希望你毫无病痛!”由此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