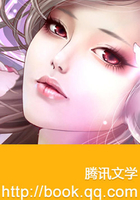胡适回国后,因返乡探亲,故于1917年9月中旬才到北大任职。当时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蔡刚上任不到一年,决心整顿北大,拟将工科归并到北洋大学,集中力量要办好文理科。文科以陈独秀为学长;理科由夏元瑮兼代。成立大学评议会(即后来之校务委员会),施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料那年7月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回北京拥戴溥仪搞恢复帝制的政变,于是北京大乱。好在“复辟”不长,十来天就结束了,但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当时北大校内竟有两个多月无人办事。胡适9月30日写信给他母亲说,到京已近20日,而大学尚未上课。各事至今尚乱七八糟,一无头绪。这年北大新学年开学是9月21日,胡适在会上作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阐述了他过去要办高等教育的主张和理想。上课原定在26日,后因来不及,又改到10月1日上课。这学期胡适所任的课程共有三门:英文学、英文修词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一星期共有12个钟头的课。他说,事体本不甚繁,本可兼任外校功课,但此番来京已迟了,各校都已聘定教员,且新任课,亦不愿太忙。
胡适初进北大,当时是小心翼翼的,工作很勤奋,对人和蔼恭敬,因此得到各方面好评。同年12月,他倡议在哲学门(系),开办研究所,为大学本科毕业生提供继续读书的场所。后来校方采纳了他的意见,遂聘他为该研究所的主任。此所因属初创,事务比较繁忙,因此他的工作也就多起来了。次年4月又增加了一项职务,任英文部主任,管理校中的英文教学,而且有些学术交流活动也少不了他。就在这年春天,北大请一位美国学者讲“欧洲文学”,他被请去任翻译。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为人作口译,之后便成为经常性的工作了。后来有人向他求教,如何做好翻译,他介绍经验说:“翻译原则只有一条:‘细心体会作者的意思,而委曲传达它’。换言之,‘假使作者是中国人,他要说这句话,应当怎样说法?’依此标准,则无所谓‘直译’与‘意译’之区别;亦无‘信、达、雅’三种区别。此三种区别皆是历史的遗痕。在初创翻译之时代,不能兼顾到‘达意’与‘保存风格’两种条件,所以译者往往删除细碎的枝叶,只留原意的大旨。如今时代不同,应该保存原文的细腻语句,应该充分显出原文的风格。具体有五条:(一)直译可通则直译。(二)直译而不可解,则意译。(三)有时意译,与原文字句形式相去太远者,则注原文于下。(四)译者于原意范围之内有增减之余地。(五)译者宜时时为读者设想,有时不便改动原文,可加注解。”这些便是他多年来的心得体会。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在《闲话胡适》一书中,说胡适英文很好,却没有译出一本可以传诵千古的英国文学杰作,为他感到惋惜。
除了在英文方面的工作,中文科的事也不少,时常应邀到校外去讲演。1918年4月14日他在一封家信里说:“今天7点起,吃了4个鸡子,一碗豆腐浆,坐车到教育部会场讲‘墨子哲学’的第四次,足足讲了两点钟。我本只有三次讲演,因章秋桐(士钊)先生不在北京,故延长一次,其四次讲毕。此项星期讲演,专为普通人士设的,颇有功效。我的讲演,不但有许多少年男女来听,居然有一些老先生来听,所以我虽辛苦,却很高兴”。胡适这一席话,不但他自己高兴,他妈妈听了也是会高兴的。当时他讲《墨子》,确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考证《史记》中何以没有墨子列传?而韩非又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这样大的学派,为什么消灭得如此神速?这些他都有精辟的论述。难怪梁启超读了他的论墨文章,说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后来,梁出版《墨经校译》请胡作序,可见其对胡之器重。不过他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前,而把胡的放在后,这点胡不太高兴。
这年暑假,胡适忙得顾不上回家乡探望老母和新婚的夫人,在校中除料理一些教学事务外,便是集中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休息时也常到公园散步,或是做些应酬。一天,他在中央公园请蒋梦麟吃饭,蒋带来一位上海客人黄炎培,他是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彼此初次见面,都很欢喜!后来谈起家事,原来父辈是相知的,当年都曾在东北吴大澂的幕府里共过事。因此,一见如故,免不了要客气一番。黄比胡大12岁,他夸奖胡适说: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样的后人。胡适听了这话,心里十分欢喜。事后他写信把这话告诉他母亲说,我在外边,人家只知道我是胡适,没有人知道我是某人的儿子。今次忽闻此语,觉得我还不致玷辱先人的名誉,故心里颇欢喜。可见胡适的性格,是很喜欢人家捧他。陈翰笙与他是北大老同事,一直有交情。而今谈到胡适时说,胡适欢喜人家捧他,他也喜欢捧人家。这话一点不错。
胡适教学忙了一年,其效果如何呢?据学生们反映是很不错的。他进北大时年仅27岁,翩翩年少,人称胡博士,学贯中西,口才又好,这在当时本科教授行列里,可谓佼佼者也(沈尹默、马裕藻、刘复、刘文典、沈兼士等,时为预科教授),因此,蔡元培竭力辅持,并引为得力助手。1919年秋蔡便任他为代理教务长了。后来,胡适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里说:他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之生涯中度过,因此他对蔡元培非常恭敬。
当时,胡适所开的课,以讲中国哲学史最为有名。先前讲这个课的教师是阵汉章(伯弢),人称两脚书柜,可见读书之多。据说,《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字字背出。他哲学史讲了一年,只讲了个三皇五帝。第二年改由胡适来教,他另起炉灶,先发讲义,按照自己研究的体系,从《诗经》讲起。他认为《诗经》里写训世诗的诗人们,都是真正的思想家。这样一个变动,可引起北大师生的震惊和议论。有位先生拿着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讥笑地说: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同学中的反应却很好。当时顾颉刚是这个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在《古史辨》序言里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不能下。”又说:“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后来他约外系同学傅斯年(孟真)去听课,也很满意。顾说:“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这段故事,后来胡适有回忆。他说:当时学生说他是学术造反,想把他赶走。因为傅斯年那时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班上的同学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之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他这么一说,这场风波才没有闹起来。说到这里,胡适很有感慨地说:“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1919年2月,胡适将此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是书一出,颇受学界之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一次,但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的老同学熊克武由四川来信说:“大著《中国上古哲学史》来川,购者争先,瞬息而罄。”胡适的这部书,到1930年已出第15版了,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这部著作是以他留学美国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为基础,加工增补而成的。主要特征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运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打破“经学”与“子学”的界限,对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比如将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对当时独尊儒家的学术状况,无疑是一个突破。其中又说老子比孔子早等等。这些论述在当时都是比较新颖的观点,所以学术界影响很大。蔡元培在《五十年中国之哲学》一文里评论说:“距今四年前,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以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的辩证法(即逻辑学),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没有的。”这个评价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看法。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里也说:“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说,并非溢美”,并称此书有“划时代意义”。再从形式上来说:是书除引文外,都是用白话文来写,而且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革新。
书出版后,胡适送了一本给章太炎(炳麟)向他请教。章看过后,回了一信,对他的书虽有所肯定,但也提出一些批评,要他注意。信是这样写的:
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