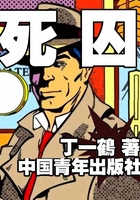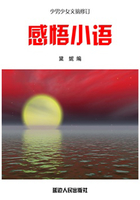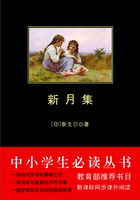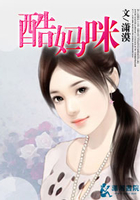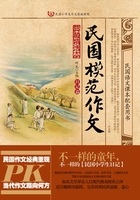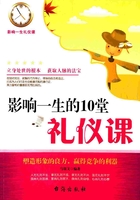(一)刘歆铜斛尺(长工部营造尺七寸二分,九英寸又十二分之一。)
新莽嘉量,今藏坤宁宫,其斛铭曰:“方尺而圜其外,深尺。”斗铭云:“方尺而圜其外,深寸。”此尺即据斛之纵广及深所制也。《隋书·律历志》谓之刘歆铜斛尺,今从之。《隋志》谓周尺、后汉建武铜尺、晋泰始十年荀勖律尺(即晋前尺)并与此尺同,故列之第一种,其后复列自汉至隋十四种尺,并以第一种尺比较之。故此尺出,而《隋志》之十五种尺,无一不可再制矣。
《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有晋前尺拓本,余曩已考定为宋高若讷摹制之品。(见《观堂集林》卷十五)今原拓已亡,扬州阮氏及汉阳叶氏刊本,均与此尺不合。然阮文达跋,谓建初六年尺较此晋尺长二分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则其拓本甚近此尺,但微弱耳。考高若讷造《隋志》十五种尺,本用汉泉(实谓王莽钱布)尺寸,今用莽货布四积为一尺,亦与此甚近而微弱,然终不如此尺之得其正也。
(二)后汉建初铜尺(长工部营造尺七寸三分七厘,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七。)
原尺藏曲阜衍圣公府,今未知存亡。世所传拓本、摹本及仿制品甚多,长短不同,均未可依据。癸亥年,鄞县马叔平(衡)见一仿制尺,汉阳叶东卿志诜所仿以赠翁学士(方纲)者,其长如此。又上虞罗氏藏一未装裱旧拓本,长短亦同(装裱后,纸易伸展,恒较原器及原拓为长),原物既不可见,当以此本为最合矣。
(三)无款识铜尺(拓本。长营造尺七寸三分五厘,九英寸又八分之七。)
乌程蒋氏藏。比建初尺稍长,晋以前物也。
(四)唐镂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九寸四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九。)
乌程蒋氏藏,刻镂精绝。《大唐六典》中尚署令注云:“每年二月二日进镂牙尺。”即此是也。中土素未闻有唐尺,余由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红绿牙尺,定为唐开元以前之物。
(五)唐红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三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六)唐红牙尺乙(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七)唐绿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八)唐绿牙尺乙(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二分强,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二十九。)
(九)唐白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三分,十一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唐白牙尺乙(摹本。长同上。)
右六尺,日本奈良正仓院藏,乃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当唐至德二载)其皇太后献于东大寺者,后手书愿文及献物帐真迹亦藏院中。帐中有红牙拨镂尺二、绿牙拨镂尺二、白牙尺二,今并完好。观其形制,必当时遣唐使所赍去也。此六尺曾影印于《东瀛珠光》第一册中,余从《珠光》摹出。
(十一)无款铜尺(拓本。长营造尺九寸四分强,十一英寸又六分之五。)
乌程蒋氏藏,宋以前物。
(十二)宋木尺甲(拓本。长营造尺一尺○二分,十二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三)宋木尺乙(拓本。长同上。)
(十四)宋木尺丙(拓本。长营造尺九寸七分,十二英寸强。)
藏上虞罗氏。辛酉年夏,出于宋钜鹿故城,同时所出磁器有大观政和纪年款,知此乃宋尺也。
(十五)明嘉靖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一尺微弱,十二英寸又五分。)
武进袁氏藏,侧有款曰:“大明嘉靖年制。”
(十六)工部营造尺(长十二英寸又十二分之七。)
右所陈列之尺,合实物、拓本、摹本,共十六种,自汉讫近世之尺度,略具于是。案,尺之为物,不独为人生日用所必需,其大者如调钟律、测晷景,胥于尺度是赖,故历代制作不能不求精密,且须参考古制。晋荀勖造泰始律尺(即晋前尺)实据姑洗玉律、小吕玉律、西京铜望、臬金错望、臬铜斛、古钱、建武铜尺七种,参校定之。唐李淳风撰《隋书·律历志》列自周至隋十五种尺,并以晋前尺校之,示其比例,其所据者,大半实物也。宋仁宗时,高若讷等议钟律得失,乃用王莽钱币尺寸,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元明学者,罕有讨论。大清康熙间,曲阜孔东塘(尚任)得汉建初尺及宋三司布帛尺,其拓本、摹本多传于世,后人得资以考订古物。又宋高若讷所造之晋前尺,其拓本尚存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册中,沈果堂(彤)、程易畴(瑶田)等,亦据以考古代礼制。光绪甲午,吴清卿(大澂)撰《度量权衡实验考》,复据古玉、古器、古钱以考历代尺度,然于唐以后之制颇略。近时所见,如刘歆铜斛尺、唐牙尺、宋木尺、明嘉靖尺,皆吴氏所未及见也。故尺度一事,比权量之研究自为简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尚不能为此比较之研究也。
据前比较之结果,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今六朝之尺虽无一存,然据《隋书·律历志》所载,则:
魏尺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五厘(长营造尺七寸五分强,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弱。)
晋后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强,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
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五厘,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强。)
梁朝佑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长营造尺七寸七分强,九英寸又四分之三。)
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弱,十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弱。)
后魏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强,十一英寸。)
后魏后尺(后周市尺、隋开皇官尺同)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长营造尺九寸二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东魏尺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豪(长营造尺一尺○八分强,十三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弱。)
此即自汉尺增至唐尺之径路,而自唐讫今,则所增甚微,宋后尤微。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而绢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匹,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案,《隋书·律历志》载高祖之言,谓魏及周齐贪布帛长度,故用土尺。今征之《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又《杨津传》: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已如此。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普惠上疏曰,绢布匹有丈尺之赢,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负圣明也,云云。尺度之由短而长,全由于此。且当时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魏书·卢同传》:熙平初,转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要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同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北史·崔暹传》:齐天保调绢以七丈为匹,暹言之,乃依旧焉。合此数事观之,则尺度之骤增于后魏一代者,更不烦解说矣。
孔氏所藏宋三司布帛尺,未见有拓本传世。世所传仿制品,大率当工部营造尺之八寸七分许,其正确与否,所不敢知。要之短于唐尺,与上言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不符。然细考唐、宋尺制,则此尺不独不能外此例,且足为此例作一佳证也。何则?唐之尺法,本有二种。《大唐六典》金部郎中条云: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又云: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案,此制本出后周,而隋唐沿用之。宋仍唐制,亦用二种尺。其量布帛也,或用三司布帛尺,则以四十八尺为匹。或用淮尺,则以四十尺为匹。程大昌《演繁露》云: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公私随事致用。予尝怪之,盖见唐制而知其由来久矣。金部定制,以北方秬黍中者为则,凡横度及百黍即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别名大尺。唐帛以四丈为匹,用大尺准之,盖秬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国朝事多本唐,岂今之省尺即用唐秬尺为定耶?不然,何为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也?云云。案,程氏所云官尺、省尺即三司布帛尺(赵与时《宾退录》云,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虽较唐秬尺颇长,而宋人以之当唐秬尺,又以淮尺当唐大尺。其言固不诬也,而今传摹之布帛尺长于唐秬尺者,至今尺一寸许,则宋淮尺之大于唐大尺,又可见矣。故曰,此尺不足破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且足为此例之一佳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