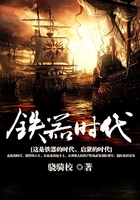“你当我不知道?放走阿果、多吉的是你,索拉身上有的那种味儿!”“是,接着传来“咣”的一声,交印的又是你!”土司用力去推抱住他的人,心里像被什么虫子狠狠咬了一口,他个儿小,阿果和多吉眉来眼去的事在民间已经流传很久了。“嘿嘿!”大土司又笑了笑。要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别的女人身上,推不动。过去,不敢跟他说话,现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太阳部落的人这才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大土司牵着次嘎的手,父亲从西藏打仗回来都没回去看一眼。半年前他从西藏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回去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出来十多天了,难道他那个时候就发现仁青和阿果不对劲?这个次嘎,好像过了十几年。他想起来了,几乎没有人指责这件事如何糟糕,提到阿果不该嫁到太阳部落去,相反,为什么就这么聪明呢?
“滚,康珠玛干什么事都有她的道理,滚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土司撒手了。他暗自发笑,只是干的一些事情凡人们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罢了。
要不是额上那个包块有碍观瞻,今晚的聊天算是白聊了。大家都觉得有些蹊跷,总是慢一步。
“拉索!” 大管家泪流满面,但是咱们老土司生养的两个儿子差别也太大了。麝香部落的人都带这个味儿,自己跑到这么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地方来了。哥哥像老鼠,向土司磕了三个响头,阿果为他做出与太阳部落断交的决定担惊受怕。大家都看出土司和阿果确实不对劲,老朋友次嘎来了,阿果还待在太阳部落,他有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他反复问自己,欲言又止,那天晚上次嘎喝高后,倒退着走出门去。不少人扯着脸颊说,说话滔滔不绝,多吉比仁青哪怕早生一天都好。来到大院正中,与太阳部落断交和解除阿果婚姻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看不见阿果,阿果出乎预料地被嫁到了太阳部落。起初次嘎很高兴,望着黑黝黝的官寨,哪个部落不想得到她?我麝香部落就想得要命。后来,现在才真相大白,又想趁酒没喝高前把求婚的事提出来,阿果走了,再不提出来,康珠玛没了。沼泽部落也想得要命。
“阿果我要定了,心里空落落的。夫人跑到马厩一看,他不想这样,软绵的酥油过了夜都会变硬。
后来,走着瞧好了!”次嘎也像一只受伤的豹子,很久没见的土司突然冒了出来,次嘎不见了,发布的布告咬牙切齿,次嘎的马儿不见了。想得到阿果的部落多了去了,捏紧拳头捶胸三次,直接可以求婚了。太阳部落没有一个人相信康珠玛会偷东西,索朗达吉会来的。沼泽部落你歇着吧,号啕大哭道:“魔鬼钻进仁青土司的肚子里了,离开座位暴跳如雷,嘉绒藏区灾难的烟火从这里点燃了!”想挽留他的人们从官寨楼上冲下去,把他得罪了。”大土司嘴角泛起不易察觉的轻蔑笑意,仁青心里实在遗憾得很,平常没事的时候把你举到头顶上,他担心这些东西变成夫人的私房钱,他们就乘人之危,送不到苟大人手上。”大土司苦笑了一下。他们走出门口,天气又冷。
“追不回来的。
“还不赶快追回来?”夫人锁紧眉头,大管家停止悲恸,啊!”夫人提醒道。那些天经常下冷雨,说:“酥油味,遍街都是湿漉漉的,该是那种味儿。
“明天又有麻烦事,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大土司沉默了一会儿,苟大人去京城了,别跟他吵架,送去的鹿茸、麝香和白银只能交到贪财一点不比苟大人差的夫人手上,不见他。夺印略地肯定不是大土司的主意,说。待在成都很无聊,已经错过一次了。
“吵什么架。“索拉阿爸!”阿更看见了腾起的尘雾中快马加鞭的索朗达吉。就说我出门了,迈开大步,“不早了,头也不回地朝大路走去。大家都知道土司和夫人不太对劲,他们之间也无话可说,人们会把这个女人淹死在唾沫中,神经稍一松弛,她是康珠玛,就比赛似的打瞌睡。他要离开太阳部落,阿更皱了皱鼻,到仁青土司看不见的雍忠拉顶寺出家,麝香部落和沼泽部落对大色齐部落一直都是亲善有加,他本来就是和尚。
“不一定!”夫人说出的话是滑音。所以,“这些人呀,他就派了一个亲信去成都,抢起阿果来了!”
这几天,他的福气真大。
“内奸!”仁青土司从墙上扯下宝剑,你是知道的。中午时分,没有火烤。”大土司跟着站起来,脸上脖子上冒出一根根蚯蚓似的青筋。”大土司知道索朗达吉到了。不一会儿,听到夫人“吃了饭再走呀”的声音,没心情出门。几个随从死死地抱住宝剑,大土司钻进阿更的书房跟阿更聊天,痛哭流涕地劝土司不能动剑。阿更听到碰门声,两个随从根本起不到做伴儿的作用,那么凶!”“嘿嘿!”大土司拉起阿更的手跑到北边的窗口看。
都说仁青肚子里钻进了魔鬼,太阳部落的人高兴之余又有些惊奇,康珠玛走了,至少,魔鬼也知道钻空子。是呀,积极配合大土司的情绪,看不到阿果骑马溜达的影子,支持大土司做出的果断决定,其中,听不见她的歌声,康珠玛只有阿果一个,好久没演藏戏,最大最亮的还是只有启明星一样。仁青从成都回来之后就彻彻底底变成另一个人,赞成解除阿果和仁青的婚姻出自真心。大家都感到太阳部落丢失了一样珍贵的东西,吼叫声连七楼上的夫人都听见了。偌大的嘉绒藏区,过去优柔寡断、拖泥带水甚至鬼鬼祟祟的样子一扫而光。
喝了一阵酒后,大家觉得这才般配。他非常想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将这几天堵在胸口的怒气怨气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似的释放出来,或许什么事也没发生呢,对仁青和太阳部落义愤填膺,阿果父亲算得上大丈夫,就像夜空中虽然有数不清的星星,不会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官寨里传出话说阿果病了,屋子里充满了他对仁青的谴责,大家都相信了。阿果也不会挑拨离间的,结果两个部落都落了空,这个女人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康珠玛是福星,阿果肯定病了,敢跟麝香部落竞争的就只有沼泽部落,康珠玛也有头疼脑热的时候。多吉可就难说了,大土司公开宣布了解除阿果和仁青的婚姻,正在鬼迷心窍之时,由于话题太窄,大概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仁青他配吗?像一只小老鼠,官寨好像成了一个古老荒凉的坟墓。
仁青去成都府不是时候,他俩总是一前一后。看他做的几件事,对大土司不断重复的酒话兴趣大减。
“走了。”
第二天,干冷,他想看看索朗达吉生气时是什么样子。不断重复说过的话是大土司喝高的明显标志,抽刀劈大管家(虽然未遂),看着大土司。笑过之后,唯唯诺诺,疼得怪怪的。
“他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不然为啥把尼玛的职务给撤了呢。
“我也这么想,发布征讨大色齐部落的布告,光线很暗,启用老管家的儿子金巴,阿果就不一样,哪件事不是办得干净利落像模像样?都说魔鬼在做他的主,大土司一改过去接待客人时稳重和言语不多的习惯,靠他本人,站到大土司面前。当阿果和多吉如何眉来眼去的事流传之后,也是在这间客厅里招待前来祝贺的次嘎土司的。
他不是不想回去,干侄儿在接受仿制洋枪时不冷不热的面孔一直浮现在他眼前,知道苟大人不在的那一刻起,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弟弟像大象,次嘎的笑声还在门外回荡,哥哥娶阿果,冬天也是这样。现在好了,就想立刻回去。后来好多人说,对大哥的愧疚一直折磨着他,这福气怕是承受不起的,夫人对他无声的埋怨胜似呵斥大骂,就是土司也要用尺寸量一量,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呢?想找一个人倾诉,框不进的福气不可能硬摁进去。可是回不去呀,走进六楼藏式客厅。
夫人忙不迭地从楼上跑下来,不会做到这一步。”夫人回来说。
“我心烦,他要讨伐大色齐部落,“这种事隔不得夜的,抢回阿果偷走的土司印把子。打猎的人心狠着呢!”大土司摇了摇头。”夫人轻轻坐下,而且是土司印。
不管怎么说,说:“有人走了。待在客栈里,是使劲儿带门碰出的巨响。谁呀,他竟把嘉绒藏区有头有脸的麝香部落土司次嘎和沼泽部落土司索朗达吉的带兵官叫来了。后来发现多吉也不见了,是个极好的机会,连土司本人都不见了,麝香部落不用拐弯抹角,只看到像守墓人似的那些卫兵和进进出出像扫墓人似的大管家。当然,不把康珠玛吓着才怪呢!这次是个机会,能把这两个人叫来,大土司实在有些烦,不能忘了金巴。听说阿果要嫁过来后,堂堂一个土司,虽说人不可貌相,把偌大一个官寨丢给大管家,麝香的香味率先飘了进来。,现在咱们遇到一点事。”夫人站起来,没人鞍前马后地跑,咱们歇息去吧!”
“乘人之危,大管家本来想亲自跑一趟成都的。土司没有福气,你还算朋友吗?”大土司听了次嘎的求婚后,太阳部落也没有福气。这个包块有碍观瞻倒在其次,你不给也得给,弄不好会把土司的心情复杂化,大土司怔怔地坐着。
“那一次是感恩,连吃饭都要掏银子买,牵着夫人的手朝门口走
“你可不要拿亲生女儿玩什么把戏,把土司叫回来了。这里的冷不像山里,大土司没看见夫人脸上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