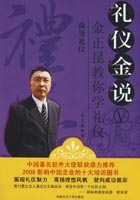莫要忘了钓鱼回。
嘎嘎嗦呀嗦啦嗦……
嘎嘎和索拉一听到这首新编民歌就感到别扭,歌中的衬词怎么会是嘎嘎嗦呀嗦啦嗦?很多民歌的衬词固然用了嗦呀啦嗦,但是也有不用嗦呀啦嗦的呀!这首民歌通篇戏谑那一对不醒事的孩子,用一下“嘎嘎”这个表达“亲爱”意思的词也不是不贴切,但是会这么巧合吗?他俩哼了几遍,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嘎嘎嗦呀嗦啦嗦就是咱们两个人的名字呀,歌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对孩子难道指的就是咱俩?用上嘎嘎,还暗含一层意思:宝气!嘎嘎和索拉坐不住了,去问唱歌的演员们是谁先唱出来的。歌都流行一阵子了,都是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他又传给你,形成一个循环。要查第一个唱的人,就等于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难。尽管难查,他俩还是不死心,很难咽下这口气,继续寻找线索。有一个现象引起他俩的注意,即从来没听见多吉唱过这首歌!不甘寂寞的多吉怎么就不唱大家喜欢的歌呢?他俩十分怀疑第一个唱这首歌的人就是多吉,有人会唱后他就不唱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恰恰把自己暴露了吗?说不定歌都是他编的呢。曲子是他们那边的民歌调,多吉平常又喜欢瞎写一些歪诗,不是他是谁?
那天,藏戏团的演员们又在帐篷里唱起了这首流行的民歌,嘎嘎和索拉斜着眼睛看多吉。多吉和往常一样,不唱这首歌,发现有人斜着眼瞟自己,遂走出帐篷,从帐篷拉绳上捡起一条毛巾,到色齐河边去了。嘎嘎向索拉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帐篷,来到色齐河边,看见多吉解了腰带,正在脱外衣。
嘎嘎和索拉顺着那条下坎小路跑下去,多吉听到脚步声,慌忙蹲在地上,扭头朝这边看。
“坐下,有话要说。”索拉掀了一把多吉,多吉倒在地上。嘎嘎坐在多吉旁边,手臂按住多吉肩膀。
“那首歌,怎么回事?”索拉两手叉腰,站在多吉面前。
“哪首歌?”多吉看看索拉,又看看嘎嘎。
“就是你不唱的那首歌。”嘎嘎用胳膊使劲儿按了一下多吉的肩膀。
“我编的。”多吉一抖肩膀,把嘎嘎的胳膊甩开。
“你编的?我们查了很久,怎么不早说?”索拉逼近一步。
“没问过我呀!”多吉下意识地举起一只手,扶住脑袋。
“嘎嘎嗦呀嗦啦嗦,什么意思?”嘎嘎又把胳膊搭在多吉肩头。
“这……”多吉支支吾吾,最后干脆笑了。
“谁是想摘白云的牧羊娃?”索拉一拳头击中了多吉头部。
“谁是想牵凤凰的寻狗娃?”嘎嘎站起来,一个飞腿踢在多吉腰上。
“谁是想捞青龙的钓鱼娃?”索拉又冲出一拳,多吉流出了鼻血。
“你们别做梦了,阿果是我嫂子。”多吉昂首挺胸,站了起来。
“嫂子?什么嫂子?”嘎嘎揪住多吉头发。索拉瞪着牛眼般大的眼睛,半空中举着拳头。
“我也是咱们首演藏戏那天晚上才知道的。”多吉说了实话。
“嫂子,嫂子!”嘎嘎和索拉整个脸都气歪了,边喊边打,把所有的愤怒都倾注在歇斯底里的喊叫和拳打脚踢上,打累了之后扬长而去。
阿果和绕拉把多吉扶进官寨,让他躺在床上。那些天是多吉最幸福的日子,没有嘎嘎和索拉在眼前晃来晃去,阿果每天来探望好几次,给他端来好吃好喝的。可惜不到半个月伤就好了,他宁愿一辈子就这么躺在床上,看阿果进进出出,端水送饭。心里又在狠狠地给自己扇耳光,多吉呀多吉,你可不能胡思乱想!
大色齐部落今年的看花节没怎么过好,半山上和山脚下搭起的帐篷里,人越来越少,都跑到广场去看藏戏团排戏。就是不排戏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到广场闲玩,只看这些美如仙童的少男少女演员们,都是一种享受。藏戏团的演员们成为大家崇拜的偶像,戏演得棒,人又长得好看,他们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大色齐部落繁华的地方是草滩市场,演员们只要逛市场,操各地方言的商人们就要叫苦连天。赶场的人们忘记了买东西,跟在演员们屁股后面跑,演员们走到哪就跟到哪。其实叫苦的商人们也跟在后面,忘了做生意。演员们怕逛市场,待在广场上不出来,这些商人把货摊摆到广场周围,因为赶场的人都跑到广场这边来了。商人们总会指着某一种货说,这个都不买呀?某演员都买了呢!买东西的人一听这句话,不再犹豫,价也不讲,马上成交。绕拉成为市场上抢手的伸袖筒人,只要有大一些的生意,卖家和买家都喜欢找绕拉做中间人。绕拉把手伸进卖家袖筒,摸一摸手指,又伸进买家袖筒,摸一摸手指,不一会儿就成交了,以至于绕拉成为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自己也热衷于在市场上摸来摸去的营生,这实在太有意思了,充满神秘和不可知,又可在瞬间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色齐甲布发现绕拉的经商才能,索性让他负责官寨贸易,藏戏团由阿果挂帅,色齐甲布把阿果当大人看待。
藏戏团的巡回演出是在秋末庄稼收割完后开始的,这时,戏已经排练得十分成熟,嘉绒藏区也进入农闲期。按照演出地点的排列顺序,第一站是嘉德陇瓦部落。
嘉德陇瓦部落属于大色齐部落属下的一个小部落,都是一家人,不用繁缛礼节的,可是尼玛木一大早就带着两个随从,骑着精心打扮过的高头大马,到大色齐部落第一官寨迎接藏戏团来了。尼玛木头戴一顶蓝色波斯礼帽,右手露出白色衬袖,身穿一件藏青色獭皮镶边长袍,脚蹬一双乌亮的黑皮马靴。经这么一打扮,十一岁的他俨然像个大小伙子。
尼玛木一面吩咐随从向演员们献哈达,一面从马背上跳下来,从怀里抽出一根上等哈达,献给阿果。
“阿果,上路吧。”尼玛木献了哈达后,只跟阿果说话,对站在阿果旁边的多吉看都不看一眼。
“叫姐姐呀,这么大了,还不改口!”阿果瞟了一眼旁边很不自在的多吉,向尼玛木说,“你呀,还是老样子。”把尼玛木献过来的哈达交给多吉。
藏戏团现在演的《智麦更登》里没有多吉的戏,他主动承担了服务工作。收拾服装道具,安排食宿,对外联络,维持演出秩序这些杂七杂八的事,都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还像团长阿果的保镖,只要没事,就不离阿果半步;他又像团长阿果的仆人,小心翼翼地侍候着阿果。
演员们都是天真活泼的少男少女,在广场排练了几个月的戏,都有些待不住了。今天出门换新地方,都十分兴奋,一路上自由自在地放声歌唱,嘉德陇瓦部落不远,大家还没唱尽兴就到了。
刚收割完庄稼的青稞地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大伙儿就等着藏戏团的到来。青稞地里留下的青稞茬儿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亮光,还闻到一阵阵野薄荷的芳香。部落头人尼玛和夫人,也就是原东女国丞相,带着排列成队的年轻人敬酒来了,那边的观众都朝这边看。演员们都是孩子,不喝酒的,敬酒只是做个样子罢了。
“阿爸阿妈都好吧?”尼玛握住阿果的手。
“都好。好久没见到伯伯和丞相了。”阿果说。
“还丞相呢,哪朝哪代了!叫婶婶。”尼玛夫人开心地笑了。
演出开始前,又出现了在大色齐部落官寨广场首演时的那种场面。观众发疯似的高呼:“阿果,阿果!康珠玛,康珠玛!”尼玛夫人有些紧张,站起来向观众挥手示意安静。尼玛和尼玛木父子若无其事地坐着,他俩心中有数,阿果会有办法的。
果然,阿果故伎重演,唱起了吉祥颂歌:
天上有太阳月亮和星星,
她们是天上的三宝。
愿天上三宝吉祥!
……
阿果清泉流淌般的歌声,把现场的观众带进了鲜花盛开的山野,碧草连天的草地,飞瀑流辉的丛岭,獐鹿嬉戏的林苑。荆棘丛生的心田被歌声的铁铧犁过,枝蔓藤条不再张牙舞爪,温润的本色是那样的安详。人们静了下来,听阿果歌唱吉祥颂歌,《智麦更登》顺利地粉墨登场。
《智麦更登》的故事在藏汉杂居的嘉德陇瓦部落也是家喻户晓,汉人们还把智麦更登比喻成男观音。现在看了藏戏,观音菩萨离他们更近了,几乎就在他们眼前。多吉手里照例拿着一根短柄白色牦牛尾巴 维持秩序,今天,牦牛尾巴失去作用,没有一个人乱跑乱挤,大家都看得聚精会神,不少人向“智麦更登”磕头作揖,三个时辰的演出就像喝一碗奶茶一般飞快过去了,人们掏出哈达向在场中谢幕的“智麦更登”抛去,哈达像雪片一样纷飞,不一会儿,场中堆起了一座雪山。
演出场次越来越多,大部落请了小部落请,小部落请了各个村寨请。阿果从十五岁演到十八岁,整个嘉绒藏区还没有转完。那几年,嘉绒藏区掀起了智麦更登热,古代的智麦更登成为今天人们的楷模。人们尽量改变自己,使自己更像智麦更登。阿果也变了,她同意嫁给自己并不喜欢的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