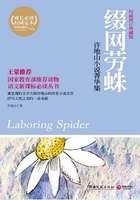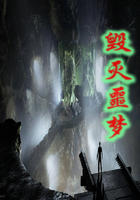河沙里有金子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各个部落都忙碌起来,人们提着木槽,扛着铁铲,踏遍了本地所有的山沟,搅浑了所有的河流,人没少累,汗没少流,最终一颗沙金都没捞着。他们忍不住头一回骂老天爷,老天爷呀,你也有偏心的时候呀,凭什么把所有的宝贝都送给女人部落呀!
各个部落都想得到去色齐河里淘金的权利,使者又络绎不绝地来了,在东女国的雍忠颇章宫里进进出出。这一次他们的运气没有上次好,都碰了钉子,没有一个使者能说服小松罗木让自己获得参与沙金开发的权利。
女人部落怎么这么不好说话?所有的部落都生气了,淘不淘金是小事,不把男人部落放在眼里是大事。土司们立即成立了临时部落联盟,给东女国带去一副弓箭和一根红辣椒,向东女国宣战!
东女国收到弓箭和辣椒后,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会上,大臣们的意见分成两派。小松罗木和尼玛主张迎战,趁机试一试邛笼的厉害。其余的女大臣都主张和解,她们觉得跟生命比,金子实在算不了什么,让他们来淘吧,反正都淘得差不多了。主战方和主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不欢而散。
东女国的百姓无论男女都支持主战派,备战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铁匠们又有了显露手艺的大好时机,打制起刀剑箭镞来手舞足蹈。各家各户都把粮食搬到邛笼里,甚至把山上的泉水都通过暗沟引入邛笼中,在做打持久战的准备。
嘉绒藏区因为沙金正在酝酿一场战争,川西坝子的人偏偏这个时候掺和进来。不过也是,谁不喜欢黄金呢!
川西坝子自古以来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天府西端有一个重镇叫灌县,灌县以西的坝子尽头地形突然起了变化,不再是一马平川,开始有山了,虽然不高,还是叫山。从这里再上行一百里后,才是真正的高山峡谷,才是嘉绒藏区。天府人和山里人过去接触不多,只是道听途说对方如何的糟糕透顶,于是无端地相互蔑视。天府人称山里人为番人,山里人称天府人为下坝子。
现在,天府人也知道色齐河里有沙金了,还传唱一首歌谣:西山高西山深,西山有条色齐河。色齐河里流黄金,黄金灿灿河似虹。黄金流跑了多可惜呀,天府人提着木槽,扛着铁铲,向西山拥来。
进山淘金的天府人很多,有段时间把道路都堵塞了,发财的机会谁也不想错过。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运气并不好,进山以后迷了路,在高山峡谷中走散,走到色齐河边的人只有几十个。
那天午后,山梁上的邛笼冒烟了,这是发现敌情的信号。东女国早就得到部落联盟组织联军的情报,做好了迎战准备。山梁上出现了人影,几十个人顺着下山小路一瘸一拐地走着,看样子不太像联军,他们走了很久才走拢盆地。
东女国的男人们把搭在弓上伸出射击孔的箭收回来,打开小窗户,看看这些陌生人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人的装束很奇怪,头上都有女人才有的那种辫子,有的背在背上,有的盘在头上。身上穿着开了衩的长衫子,腰带里别着烟杆,脚上穿着草鞋。这不是传说中的天府人吧?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说不定又渴又饿呢!女人们心软,都准备回家做饭给他们吃。不,没看见吗?没安好心呢!还是男人们警惕性高,看到了这些人手里拿着的木槽和肩上扛的铁铲,又把收起的箭搭在弓上,送出射击孔。
这些人一边一瘸一拐地走着,一边东张西望,看到偌大的村寨没有任何动静,眼里流露出惊奇和侥幸的神情。远处有几只野狗朝他们吠叫,这些人把扛在肩上的铁铲拿在手中,防范野狗的进攻。
他们走下河坎,鞋子也不脱,涉进河里,伸手抓起一把河沙,用手指翻检了一会儿,突然举起双手,歇斯底里地吼叫:“色齐!我们找到色齐了!”
邛笼里的人都吼叫着冲了出来。冲到河边时,那些人吓得慌不择路,扑通扑通往河里跳。他们可能想逃到对岸,拼命向河中心蹚,可是河心水深浪急,水已经淹到脖子,再向前走几步就没命了。只有一个人没跑,站在河滩上,面朝琼日神山,双手合掌,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刚才没人注意他,现在才发现此人穿的竟是嘉绒服装,虽然短衣薄裤,一身夏季打扮,但仍看得出来他是本地人。审问后才得知,他叫罗尔依,就是嘉绒藏区太阳部落的人。他会说汉话,就跟着这些汉人来了,而且是他给这些汉人带的路。
“拖回来!”小松罗木现场指挥。个儿高力气大的几十个小伙子跳进河,拽住那些人的胳膊拖到河滩上。那些人湿漉漉地跪在地上,捣蒜似的磕头。
“回去吧。”小松罗木挥了挥手,原谅了这些人的侵犯行为。
这些人跪着不起来,嘴里嘟囔着什么。罗尔依翻译说,他们不想走,没地方去。他们若有地方去,就不会到这里来。
“好吧。”小松罗木爽快地答应了。他们想留下来也好,女人部落需要男人。
这些人的运气还算不错,化险为夷不说,走投无路时还被东女国收留,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做淘金梦的大批天府人一进山就迷路了,在各个山沟里乱窜。征讨东女国的联军刚上路就碰上他们,误以为是东女国搬来的援军,便调转枪头追杀。追杀一阵后就不再追杀了,因为联军发现这些人不太像援军,看他们的装束,更像传说中的下坝子的人。被俘的人没有任何杀伤性武器,除了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把铁铲和一只木槽外,连一根锥子都没有。联军中只有太阳部落的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是他们的土司曲登指使负责守桥的管家放过来的,为的是赚他们的过桥费。凡是过桥的人,每人要交银一两,因此,太阳部落的人管这座桥叫收银桥。比画半天之后联军才明白,这些人想去色齐河淘沙金,土司们知道后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们靠近东女国的人都没沾上沙金的边,这些山外人倒是毫不客气地打从老远跑来了。而且,还误了联军的大事,部落联盟好不容易把联军组织起来,正要讨伐东女国时,却让这些外来人给搅和了。这些迷了路的汉人被集中在一起,关进了牛头山露天牛圈里。
牛圈旁边的草坪上,土司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打算。参加紧急会议的有十七个部落的土司,嘉绒藏区有十九个部落,除了东女国女王和琼日部落松罗木兄弟外,其他部落的头头都来了。
这些人不可能不来,这次向东女国宣战,意义非同一般。参加紧急会议的各部落土司,他们的祖先们都有占山为王的经历,但是地位没来得及被官府认可。为了得到朝廷的册封,在元代成吉思汗的骑兵一次远征云南经过嘉绒藏区时,他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纷纷献上哈达俯首称臣。自那以后,他们的历代祖先带上本地的贵重礼品和部落土地人口名册,不远万里奔赴京城归附,陆续得到皇室的册封,堂而皇之地成为土司。嘉绒藏区经过漫长的岁月,各个部落土司的领地已经十分清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相互械斗争夺而使领地权属变得模糊不清。土司们知道,整个嘉绒藏区,目前只有东女部落占的地盘不属于任何部落所有。东女部落迁来之前,没有一个部落发现这块地盘,现在东女国虽然发现了它,还把它占了,但是,东女国是外来部落,没有占据嘉绒藏区地盘的资格。更重要的是东女国部落女王没有被朝廷册封过,还煞有介事地称国,整天女王、丞相、大臣、王宫、内阁地叫着,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羞死人了。女人的脸皮一旦厚起来,男人是远远比不上的。前几年大家没在意,女人部落嘛,逃难来的嘛,荒山野地嘛。现在感到她们越来越不像话了,越来越不好说话了,越来越不把男人往眼里放了,越来越感到不教训一下是不行了。说到底,大家都认为瓜分新土地的机会来了。难怪土司们说到讨伐东女国时,一个个眼里放光,心里激动。
十几年后,在大色齐部落官寨的一个宴席上,沼泽部落土司索朗达吉回忆起那次部落联盟紧急会议的情景时说:“当时我们争论的事情很无聊,现在想起来都脸红。我们不是经常嘲笑古代养马的那老两口吗?母马临产时不去照料,而是争论产下的马驹长大后作何安排,结果母马难产,母子双亡。我们当时恰恰就是这么争论下去的。”当时他们确实把如何攻打东女国的事搁置一边,心思都用在如何处置东女国的领地和财产上面。土司们各有各的想法,意见统一不起来。色齐部落土司色齐甲布在众土司中威望最高,这次各部落得以联盟,主要得益于他的穿针引线,但他也不能把意见统一起来。别以为平常所有部落首领都尊崇他,部落之间的纠纷也只有他才能调解,但在遇到瓜分东女国这样的巨大利益面前,各土司绝不会轻易放弃原则,至少,沼泽部落土司索朗达吉和太阳部落土司曲登是这样,觉得没必要看色齐甲布的脸色行事。要说势力,北边的沼泽部落有十几万头牛,几十万只羊,能够随时召集数千骑兵,色齐部落有吗?没有。要说地缘优势,太阳部落占据东边的沿河良田,那儿可是嘉绒藏区的粮仓,色齐部落有吗?没有。不仅没有,色齐部落在地缘方面还处于劣势。色齐甲布的祖先当初从象雄国迁徙到嘉绒藏区时看走了眼,把色齐河的一条支流当成主流,将其部落扎根在那里。奇怪的是大家都看走了眼,都认为那条支流就是色齐河的主流,连这个部落和部落首领的名字都带上了“色齐”两个字。大家都认可色齐甲布,最根本的原因是色齐家族的血缘有些来头。现在的色齐甲布的祖爷或许是祖爷的祖爷,曾经是喜马拉雅山区当时最强大的象雄帝国王室的重臣,与国王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象雄帝国瓦解后才被迫远迁到嘉绒藏区的。远迁的实质虽然为落荒而逃,但其正宗的王室血统不会因之改变。这一血脉除了高贵还兼神圣,象雄王室的祖先就是神鸟夏琼。在如此既高贵又神圣的血统面前,嘉绒藏区所有土司都自然感到矮了半截。
色齐甲布反复斟酌,始终觉得东女国现在占的地盘早就应该是他的,自己的部落和自己的名字都带着“色齐”两个字呢。东女国占的地盘就在色齐河的主流上,就凭部落和自己的名字,拥有这个地盘不仅名正而且言顺。再说,祖先虽然看走了眼,部落扎偏了点儿,但是地域之间都连着呢,只要稍稍挪动一下位子就正了。而且东女国也信奉琼鸟,说起来还是一家人,因此他甚至不想打仗,只想径直走进雍忠颇章宫,搂住女王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