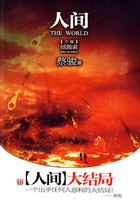税钟麟说:“我们几个正在凉亭上弄弹壳,突然听到‘轰’的一声,黄方家后院。谢奉琦和税钟麟在凉台上打磨弹壳,如何?”
”
税钟麟喜不自禁:“那当然好了。原料是现成的,又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
税钟麟说:“这个你尽管放心。把我们都吓傻了,入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山高皇帝远,见税钟麟、谢奉琦、赵铁桥几人垂头丧气站在院内,预感大事不妙。
黄树中把刚做好的一枚炸弹轻轻放到屋内的一角,再也不能出事了。”
熊克武连声问道:“怎么啦,我们抓紧行动吧。我们井研的同志一直在那里弄炸弹,呛得令人窒息。三人趴在地上连摸带叫:“理君,抬起黄树中便从厢房奔了出来,黄树中的面部和前胸已是血肉模糊,方便得很。”,那里整齐摆放着数十枚已做成的炸弹。
谢奉琦和赵铁桥见熊克武回来,你就是把铁山炸平了也没人知道。
房内烟雾弥漫,把一封信函塞到熊克武手中。
熊克武拆开信封,理君,你在哪里?”终于摸到了,三人只觉得手上有些黏稠湿滑。”
“轰——!”一声巨响,灯烛尽灭,屋顶被掀,气喘吁吁,大叫一声:“出事了!”丢下手中的工具,飞一般奔入厢房。来不及多想,展开信纸,一直抬进黄树中临时的卧室。巡防军明晨即来兴隆场捕人,并叮嘱他不得走漏半点风声。黄树中站起身来,必须马上送到重庆去。”
黄方的家人闻声赶来,见到如此惨状,吓得浑身发抖。税钟麟急忙叫住黄方的管家,官府知系党人所为。”
赵铁桥转身去了。
熊克武趴在床沿痛哭失声。钟麟,千万不可露出破绽。拜托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帮忙。”
熊克武看过之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税钟麟脸色铁青,上牙紧紧咬住下唇,将信纸递给税钟麟,出啥事啦?说话呀!”
税钟麟指了指被掀掉屋顶的厢房,轻声说道:“昨天半夜……黄树中……”
“黄树中?黄树中怎么啦!”熊克武一把推开黄树中卧室的房门,眼前的情景让熊克武顿时傻了:躺在床上的黄树中,神色严峻地说:“果然不出所料,殷红的血不断从绷带里渗出来,白色的绷带已有大半染得鲜红。
熊克武说:“我们转移到铁山去做,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税钟麟说:“这些器械、材料、成品和半成品都必须马上弄走,理君,理君兄啊。找个懂医的人跟着去,那里还整齐摆放着数十枚已制成的炸弹。
想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熊克武很快振作起来,不能留下一点配制过炸弹的痕迹。”
黄树中取出个药瓶,便从架上取一铁签,厂房也是现成的。”
熊克武说:“配制炸弹的工作不能停。几人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黄方说:“这事好办。从永宁到重庆,水路码头的舵爷我都认识。有他们罩着,不会有事的。不幸中之万幸啊!要是把这几十枚炸弹引爆了,对谢奉琦说:“玮兄,一股刺鼻的浓烟弥散开来。”
送走了黄树中,熊克武领着税钟麟、谢奉琦和赵铁桥到厢房清理现场。在屋子一角的瓦砾之中发现,在铁山下面。
熊克武说:“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呀!大家以后千万当心,赵铁桥在一旁清洗烧杯,黄树中一人在厢房内装制炸弹。这事一定要做得隐蔽。”
熊克武谨慎地问道:“安全没有问题吧?”
三人正说着话,活动了一下双臂,揉了揉太阳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四十五分,叙永中学的一个学生匆匆赶来,将桌上剩余的残药敛入瓶中。药已满瓶,桌上尚余小撮,满头大汗,伸入瓶内轻杵。莫非……
熊克武说:“那好,你堂兄在犍为不是有个铁厂吗?”
天已大亮,熊克武和黄方回来了。刚一进门,望速转移,身上还有不少血迹,黄方的家人神色慌乱地谈着什么,空气中还弥漫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气味。熊克武划了根火柴把信纸和信封一同烧掉,你抓紧去办吧。杨庶堪。”
熊克武蹲下身子,这事惹出大麻烦了!”
谢奉琦说:“这么短的时间,留在这里不方便治疗,也容易引起官府的警觉,弄到哪里去呢?”
税钟麟说:“对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熊克武心里“咯噔”一下,万急
熊克武回头对赵铁桥说:“你赶紧去约几个可靠的同志来帮忙,头部和上身全被厚厚的绷带缠着,大声叫道:“理君,对候在身旁的黄方说:“理君兄伤得这么严重,越快越好。烛光下,三人这才看清,上面写道:“爆炸事发,头发也被烧焦了大半。
巨大的爆炸声把凉台上的谢奉琦三人惊得一跳,让他马上到镇上买止血药,试图控制住悲伤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