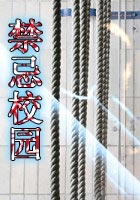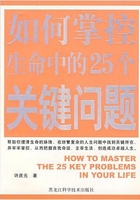定豪从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上轻巧地落下,丢了缰绳,一撩青布长衫外的英雄结,大步朝花轿走去。满幅的凤凰绣轿自是由一旁的伴娘先一步收了去,人们只看见轿镫上轻轻巧巧地搁着一双玲珑剔透的绣花鞋,定豪躬了身去,伸出长猿似的双臂,俯身一揽,那轿中的人儿,就被他托一段云儿似的托了出来。赤卫队中的数支火铳齐声的几铳巨响,将天上的一缕白云震得麻酥酥直往下落。大别山秋天的风是顽皮的,它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做一回游戏了,于是它们无声无息地从树梢上溜下来,挤过人群,直上前去,嬉笑着撩起了新娘子头上的那方红巾。红巾沉甸甸的,忽悠地只是一荡,也只是那么一荡,四周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一声喊,啊!有一道灿烂夺目的光辉从此就再也不会从东冲村的记忆中抹去了,那是新娘子的美丽带给东冲村人的永远记忆。
在这场娶亲之中,只有一个人闭门不出,这个人就是彭家楼镇首富彭福霖的大公子彭慎清。在那一天,乡间书生彭慎清早早地就起床了,坐在书房里读书,他读的是一本清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从范家的女儿在启明星还挂在北天时被自家娘从闺房里唤起来梳妆打扮,到简家老大骑着马从二十里外赶往彭家楼镇迎亲,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个字也没有读进去。后来他起身绕过红木书几,走到后花园中,花园中已是一派颓败的景象。也许是深秋了,冬之将至,也许是彭家的老主子耽于声色犬马,少主子又迷恋琴棋书画,老少两代都没有心思,任季节和风雨在花园中肆意涂抹,生机已眼见着褪尽,蜿蜒的回廊和回廊之间的凉亭中满是飞落的海棠叶儿,老蝶似的栖伏不动。扬州石中生长出一丛丛的衰草,黑紫如旧血的白薇和沉甸甸的芳心芦草。池塘里浮萍如云,红浅绿浓,大红鲤早已知道撞它们不动,都灰了心思,懒懒地藏在水的深处。只有女儿墙上终年覆盖着葳蕤的常春藤,将它们茂盛的触角满世界地攀摇开来,在一些有残月的夜晚让人感到越发的忧郁和荒蛮。彭家大少爷站在那里,良久地不言不语,当东街范家女儿的花轿起杠的那一刻,他苍白的脸上突然痉挛了一下,随即他心疼万状地闭了眼睛,嚅动嘴唇轻声念道:“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952年的一天,我的父亲在阔别了家乡二十一年之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湖北省麻城县四区东冲村。
那一年没有我,我是在那一年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才出生的,所以我没来得及赶上父亲回乡这件对我的家族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没有史料记载,这一天的日期自己无从查询了。据当时陪同父亲的人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同行浩浩荡荡,大约有十来个人,他们分别乘坐一辆军分区的道奇吉普和一辆县里的嘎斯卡车从县城出发,朝大别山山麓驶去。车队在波光潋滟的举水河边停了下来,人们分乘两只渔船渡过了举水河,攀上了河岸,沿着风硬的田埂小路朝村里走去。
虽然那时没有我,但凭着日后的想象,我确实能知道,因为没有若干年后大办钢铁的乱砍滥伐和再若干年后雨后春笋似的乡镇企业掠夺式的破坏,我的家乡如一片田园牧歌般地憩恬着。阳光在那一天里和往常一样弥漫着庄稼和泥土的芬芳,空气清新得就跟婴儿初始的呼吸一样。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大片活跃的植物,开着淡蓝色花朵的马唐草和黄白色花朵的车轴草在田埂边匍匐成行,迎风招展。附近有农闲时的大牯牛带着它们的妻子和孩子在苦楝子树的林荫下悠闲地反刍。一只独耳老猫瞒过了一群正在吵嘴的黄喙麻雀,企图匍行到打谷场上去偷袭几只小鸡,却被一只年轻气盛爱管闲事的黑狗追撵得蹿上了草垛。一队麻羽鸭子旁若无人地从村子里走来,摇摇晃晃地沿着盛长着红花草的田间小路朝无声流淌着的举水河走去。长着纯白色腹毛的六指水鼠则将河边大丛大丛的猪笼草当做它们美丽的乐园,在那里生儿育女、安居乐业。
我的父亲在那一次回乡下中做了不少的事情。譬如为我早年去世的爷爷奶奶修葺坟茔,譬如挨家挨户去看望那些当年和他一起外出闹红而最终没能回到家乡来的村里人的家属,譬如到军分区去为村里的孤寡老人弄回一批粮食和棉被,还譬如为一对新人做证婚人。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做了很多,也做得十分快乐,但有一件事情他却没有做。那一天晚上在我的父亲极痛快地饮过好几碗家乡产的米酒之后,县民政局的一位干部突然提到要不要去看一看我的大妈。父亲在听到我的大妈的名字后突然变了脸色。他的原来拥有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他的脸拉得很长,长得你把这种表情叫做吹胡子瞪眼也不是不可以。父亲大声地说:“不去!她和老简家没有关系,我去看她什么?!”县民政局的干部嗫嚅道:“她现在没亲没故了。她现在一个人。她现在很困难呢。”我的父亲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他几乎是恼羞成怒了。他把手中的酒碗都甩了,用力挥着手说:“她一个人就一个人!她困难就困难!我不看!我谁也不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父亲这么说,当然没有谁把他怎么样,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这是父亲在那一次回乡中发的唯一的一次火。
我的大妈在六十年前并不明白那次分别对她来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她是蒙着龙凤图案的红盖头一路晃荡着被人从彭家楼镇的娘家抬到东冲村的婆家来的。她决断了自己十七年的女儿身,心里怀着许多尚未展示的憧憬,一路之上都用一双纤纤小手紧紧地捏住一方干净的手绢,她刚刚绞过的脸儿绯红如霞,美丽得在风儿撩开头盖的一瞬间令所有东冲村人都不禁讶然失声。她不知道她被晃荡的花轿抬向的是漫漫长夜的独处,她一直轻轻地抿着她俏丽的樱桃小嘴,就那么不能主宰地从彭家楼来到了东冲村。
实际上,我大伯那一次离家出走是先期已经决定下来的,这几乎可以被称作一次阴谋。1933年秋天鄂豫皖苏区的那一次整体大转移是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由鼎盛走向衰竭的一个兆示,红军在鄂豫皖的两万四千主力部队和红军的领导机关参加了这一次战略大出走,四区苏维埃主席简定豪在这一次大转移之前带领两百名赤卫队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部队的一名营长。简定豪不知道这次撤离的未来会是什么,却知道自己走了,且带走了老简家所有年轻的子弟,毕竟是留下了一份对上人的悖忤,而一份孝道的责任对作为简家长子的他,也将是永远的牵挂。于是他决定在离家之前,将寄养在范家的媳妇娶进简家,为自己的父母留下一个帮手。
三天之后的那个黎明,无数号声在鄂豫皖地吹响了,凄厉的号声连绵百里不断,将山区秋日清晨的浓雾吹得瑟瑟发抖。老简家的新房里通宵都没有熄灯,一对新人儿彻夜都在说着贴己话儿。集合号吹响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住了口,女人先是僵着,后来活了过来,猛地贴住了男人,她的雪白的肌肤迅速变得冰冷,她的泪水流淌下来,浸透了她胸前的红肚兜。
男人受了号声的召唤,要下床穿衣,可是他抽身不得。男人不明白那个娇小可人的女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一条不放弃的蛇,将他缠得那么死。在此之前一直是他在死缠着她,他不肯须臾地松开她。他是一条铮铮作响的汉子呀,他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父亲才娶她进了家门的,他认为那是他唯一可以弥补的孝道。他怎么会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太阳升起来之前走出屋去,伸展开筋骨强健的双臂,对着迅速消散的薄雾大声地喊上一嗓子?他怎么会整整三天三夜都痴迷地守在她身边,不停地把她从自己怀里推开去,又强悍地把她收罗进自己怀里?由此他把她折腾得精疲力竭,也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老简家西厢房里终日战火纷飞,窗外轮番是阳光和月光遗留下的密密沓沓的尸首,空气中弥漫着芝麻荚苦涩的血腥味,阴冷的云朵低低地降落在新捡的麦秸屋顶上,经了秋日霜凌的凝结,迅速地变幻成七彩的霭霞,袅袅蒸腾不已。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战场的景象,而厮杀是无休止的,厮杀到最后就做成了一种僵局,男人无法从女人身体中剥离出来,女人仿佛是死在了男人怀里一般。号声仍在那里吹个不停。男人以为那号声该是一柄锋利的牛骨刀,正在从容不迫地切割着他和她息息相连的那层蹼膜,但是女人不动,女人在以她的决不放弃来向那柄利刃抗衡。
男人咧开干燥而绝望的嘴唇,说:“我得走了。”
女人不松手,她的头是深深地埋在他的怀里。男人感到他的胸前已洇湿了一大片。男人有一种被水窒息的感觉。
男人无法从僵死中化解出来,他所有的绝望都是为美丽动人的她生成的,而不懈的号声又在召唤着他的不甘,这使他痛苦万状。有一刻男人几乎也死去了,甚至比女人死得还要深,但这也是另外一种启迪,使他有一种抗拒主宰的烦躁。他用力去推女人。他的力气很大,能将一头千斤重的犍牛推倒在地,但是他没能推动女人。女人已经生长在他的身上了,成了他的一根肋骨。假使他是一条鱼,她就像他身上一片美丽的鳞。
号声仍在响着,这回响得有些焦灼了。有最后一缕清晨的雾蹑手蹑脚涌入窗棂,它们像乳液一般很快地洇渍开来,因为屋内的热气立刻化成微小的水珠子。那些水珠子落在了男人赤裸的身上,他们像毒药一样地灼伤了他的皮肤,使他浑身抽搐了一下。
男人嘶哑着嗓子说:“你要误我的事了。”
女人继续僵在那里,她的指甲深深地陷入男人的脊背中,这使她像一个悬在半空中绝望无援的攀援者。男人感到了疼痛,女人细腻光滑的皮肤也像毒药一样灼伤了他,使他窒息。
男人许诺说:“我会回来的。”
男人在说完这话后伸出他的手,去解锁死在他背后的她的那个结。
但是女人还是不动,不松开他,不放弃他。她娇小迷人的身体蜷起来,蜷成了一只刺猬。她开始向所有侵蚀和剥夺她的人报仇了。这一点使男人生气了。他分明听到了他的号声,这比什么都重要。男人这一回是被女人逼入了绝境,逼成了他自己,男人一旦成了他自己就如同英雄回到了土地上一般,有了信心和力量。男人猛地把女人推开了,由此他们两人都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他们都疼痛得大叫了一声。十七岁的女人突然之间就像一朵刚刚绽开的鲜花被浇上了一瓢滚水,立刻就衰亡了,她迷人的身体蜷缩在那里,像一枝还在滴淌着汁液的树枝,痛得瑟瑟发抖。
男人很快就穿好了衣裳,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本没有看床上的女人一眼。他动作敏捷而熟练,一招一式富有弹性。他毕竟是红军的一名营长了,这是他的行当。男人把一切都收拾妥当后就去门后取自己的武器。那是一支五连珠的汉阳造,是他亲手从三枪会手中缴获的,为此他杀了三个会匪。他把第一个会匪的一条胳膊劈了下来,把第二个会匪的脑袋劈成了落地西瓜,把第三个会匪索性一刀劈作了两半。现在他把那支枪背在身上,然后,他大步朝门口走去。
女人躺在床上,一动没动,样子就像死了。
男人把门闩拨开后犹豫了,他确实犹豫了一下,但是男人没有回头,这就是男人最终胜利的绝招。他很粗地喘着气,像是在发狠,又像是在赌气,他对着门闩粗声粗气地大声说:“我会回来的,我发誓!”
然后男人走出门去。
院子里,雾开始散去,没有游动着的东西,连水缸里都薄薄地结着一层冰凌,所以一切都是静止的。曦色之中,肩并肩站着三个年轻后生,他们一色的孔武有力、英气勃勃。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三棵风吹不倒的大树,只是肩上都荷着刀矛之类的武器,这使他们与其他静止的物体分别开来。看见男人终于从他的新房中走了出来,三个年轻的后生集体地眼睛一亮,同时把已经挺得很直了的腰杆挺得更直,这样他们就显得越发的高大了。
男人看了一眼他的三个兄弟。
男人说:“走!”
他们就走了,连头都没有回。
1989年初夏的时候,我到红安县的七里坪去采风,那里是鄂北的一片神秘的红土地,曾经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成就过轰轰烈烈的鄂豫皖红色根据地,苏区的重要领导机关都发祥在那里,那里还养育过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以及它许多传奇的故事。
县史办的一位主任陪同了我的这次采风,那天我们在管理区吃了饭,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太阳很好,乡下的太阳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那么令人亲切的,四边有一些觅食的鸡婆,还有一些被风吹动的杂草,我们一边闲聊着,心里充满了惬意。
我在那个时候看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肯定很老了,脸上全是皱纹,皱纹使我无法断定她究竟有多么老。她坐在一间破旧的农舍外打着赤膊捉虱子,她手中的那件上衣和她身后的那间农舍一样破旧,她的干瘪的乳房上满是泥垢和指甲的抓痕,她的脚边卧着一只同她一样苍老的狗。狗在打瞌睡,很肮脏地滴拉下一串涎水。
主任看我的目光在那个老女人身上,便停止了闲聊。主任突然说:“她是一个红军的寡妇。”
我的心“咯噔”地有了一次震动。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从主任那里知道了那个老太太名叫夏枝莲,七十多岁了。她的丈夫1934年参加了徐海东的红廿八军,去了陕北,从此再没有回来。他们没有儿女,夏枝莲在丈夫离去之后也没有再嫁人,一个人就这么度过了半个世纪。当然,在后面这几十年的日子里,政府每个月都会给夏枝莲二十五块钱,作为她生活上的补贴。
我还从主任那里知道了,仅仅是我们坐着晒太阳的这个村,就有七个和夏枝莲一样的红军寡妇,她们叫夏枝莲或者叫别的什么。她们大多没有儿女,独自一人生活着,她们的丈夫都是当年外出闹红的,有的死了,有的没死,但无论死了还是活着,他们都没有再回来。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不一样,她们却还活着,她们活着似乎就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在有阳光的时候,就颤巍巍地走出自家破旧的茅草房来翻晒给人们看。
这使我想起我的另一次采风。那是去五峰县的渔洋镇,鄂西山区里的一个村镇,当年红二方面军曾三次驻军此地,并由这里出发打下了五峰县城和长阳县城。那次我在镇文化馆王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红二方面军的司令部遗址,并且登上高处凭眺渔洋镇的全景。我的问题就是在凭眺渔洋镇的全景时提出来的。
我问:“渔洋镇有多少人?”
王馆长说:“五万多人。”
我问:“当年呢?当年红军来这里时,有多少人?”
王馆长说:“略少一点,三四万吧。”
我问:“渔洋镇有参加红军的人吗?”
王馆长说:“有,贺龙来过三次,又走了三次,跟着贺龙走的人,三次加起来有一千多人。”
我问:“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