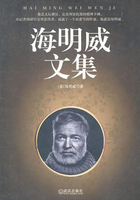父亲自己这样,还影响他的子女们。他坚决反对他的孩子们当兵,在这方面,他丝毫没有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在父亲失去了他的军职之后,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渐渐瓦解,我的哥哥、姐姐和弟弟们都在顽强突破父亲的铁幕统治后穿上了军装,远走高飞。这一度让父亲心神烦乱。父亲在那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开始关心他当兵的孩子,比如入党、提干以及在部队的各种表现,但真正关心的实质是最后一项——他们的转业。父亲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先是以身边无人照顾为由将在成都当兵的姐姐弄回了家,很快让姐姐转业到了地方;接着“绑架”了两岁的大孙子,再以此要挟逼迫我的大哥在天津脱去了军装,回家来当了一名技术员;最后一个是我在新疆当兵的弟弟,父亲干脆地说,弟弟根本就不是一块当兵的料,如果他只知道一个劲地写信向家里诉苦的话,他还不如干脆回家来做他的老小。父亲就是这样完成了他的整个计划。他使他的子女们在满腔热情地穿上军装之后并没有成为无所牵挂的军人。他用他自己强大的思维制约着他们。他设计了一个个圈套,然后从容不迫地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钻进了他的圈套。他向他们证明了,无论他们怎样的聪明和有文化,在他面前,他们永远都是嫩得像能掐出水来的新兵蛋子。他坐在他那间全部由部队营具布置出的房间里,深邃的目光坚定地穿透砖墙投向看不见的遥远之处,显得沉着而冷静,直到他最后一个孩子穿着摘掉了领章帽徽的军装背着行李推门而入时,他便告诉自己,这个战役结束了。
对于父亲如此作为,我的母亲非常有意见。母亲是蒙古族人,大漠草原的骁勇血统使我的母亲一直认定好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只有挽弓挽缰驰骋疆场的汉子才算得上真汉子。母亲当然是因为组织上的决定才嫁给了父亲,成为我母亲的,但这并不说明一开始她没有被伟岸的父亲骑在高头骏马上的威风所诱惑得怦然心动。花烛之夜父亲橐橐而至的脚步声肯定使母亲满面红霞,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母亲嫁给了一个职业军人,她的大哥是军人,小弟是军人,她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军人,她把军队看得无尚崇高便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了。母亲希望她的孩子中能成长出几个好军人来。母亲坚信“龙生龙,凤生凤”的不朽理论。母亲关于好军人的概念十分简单,那就是当大干部指挥大队伍的军人。可是母亲的美好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不能不让她伤心难过。母亲也曾竭力反对过父亲对子弟兵的策反,但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母亲却最终没能战胜由农民而军人的父亲。母亲在希望彻底破灭之后大声地对父亲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自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不求进步,难道还不让孩子们求进步吗?!”
我知道,母亲的这句话肯定是重重地刺伤了我的父亲。它像一柄钝而沉的矛,直接刺中了父亲伤痕累累的心中最不该被触动的那一部分。我的父亲的心在那一刻肯定是在流淌着鲜血,并且疼痛得止不住地痉挛。但是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说。他转身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关上了门。
父亲在接到休息命令后不久就和母亲分室而居了。
山海关战役之后父亲被行政撤职,调去合江省和土匪们打交道,这也许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了。父亲继续被作为强有力的杀手,带领一个加强团在冰天雪地中到处游荡。从虎林的阿察河到西克林的库尔滨河,所有派系的土匪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他们对父亲和他的剿匪部队咬牙切齿,视为眼刺。他们之中不乏绿林高手,在东北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中,无论是老毛子、张府二帅、关东军还是鲜人敢死队都不曾把他们怎么样,管你天上飘着什么颜色的旗,他们腰里插着一水新的喷子,胯下骑着膘肥体壮的压脚子,身上穿着暖乎乎的山神爷毛叶子,进屯就嚷嚷着搬姜子(喝酒)、飘洋子(饺子),酒醉饭饱后还要去玩上一个俊俏的海台子(暗娼),要多快乐有多快乐,可他们最终还是栽在了父亲残酷无情的剿杀之中。
父亲率领他的剿匪队伍在北满的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着,所有的马匹都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吐着白色的热气,时刻不安地撩动着挂满冰凌的四蹄。父亲的胡子乍立如矛,目光凶狠,脸色铁青,身上长满了虱子。父亲大口啃着冻得嘎巴脆的猴头菇和肥腴的大马哈鱼,将带血的狍子肉整块整块地填进他的胃里。父亲灌凉白开似的大口灌着劣性老白干,然后摘下熊皮帽子,硕大的头颅上开锅似的冒起大片热气。两只装满弹匣的大镜面匣枪挂在马鞍两旁,父亲就那么晃荡着双枪策马疾奔。大雪纷纷扬扬,部队在雪原中就像一捧滚动着的雪粒子,除了马匹偶尔发出的响嚏和脚步踩出的嘎嘎滋滋的雪响,没有人说一句话。父亲带着他的剿匪部队就这么没日没夜地往前走,固执地追逐着每一股土匪,恶狠狠地咬住他们,然后眼不眨心不跳地把他们变成冰冷的尸首。
熊熊的篝火在日本军用帐篷外哔剥地燃烧着,松脂能使篝火彻夜不熄,父亲在帐篷里紧裹着虎皮大衣酣然大睡,身下冰雪悄然无息。一头丢失了崽子的黑瞎子气鼓鼓地从林子里走出来,与一群觅食的野猪擦肩而过。黑瞎子茫然无措地看了看篝火,摇摇头,笨拙地离去。它不知道,亮如白昼的黑夜中,至少有两个流动暗哨都曾将顶上了火的枪口瞄准过它毛茸茸的心口。黑瞎子离去之后大雪仍然纷纷扬扬,在接近篝火之前化成了水珠,给火焰带来了一些快乐和兴奋。高大的塔松支撑不住,轰然坍塌下一堆积雪,将帐篷砸得一晃悠。父亲鼾声依旧。
浓睡中的父亲从来不做噩梦。
赋闲之后的父亲为自己谋得的最后一个领地是一间唯独属于他自己的房间。
光阴荏苒,母亲早已习惯了随军飘移和颠沛的生活。自从1948年母亲在东北嫁给了父亲之后,她就开始不断重复搬家这一类事情。早些时候没有什么家当,父亲将调令往兜里一揣,叫警卫员拎上唯一的皮箱,带上母亲就出发了。慢慢就有了些负担。从东北入关的时候母亲怀里抱着我吃奶的大哥。调离南京的时候母亲怀里换成了大姐,大哥则由父亲的秘书牵着。进入湖南后我的二姐降生了,这使调动的队伍变得臃肿起来。1956年,父亲调往四川时,我母亲怀我已足月,调动却并不因此而受阻。在长沙站,列车长知道母亲将要临产时说什么也不允许母亲挺着大肚子上车,他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阻止我的母亲把婴儿生在隆隆开动的火车上。父亲在火车启动时开始大动肝火,他指挥警卫员把我的母亲硬从车窗口塞了进去,在列车员打算再一次把母亲抬下车时警卫员拔出了手枪,警卫员怒不可遏地用瓦蓝的枪口指住列车员的鼻子说:“你想活不想活?!”这样,我母亲和我才一路无虞地被“运”到了四川。
母亲像大部分随军家属一样很快学会了搬家,她甚至能奇迹般地将十几口巨大的泡菜坛子无一损坏地托运到千里之外的新家。搬家使母亲从父亲的家属一跃而成为行动的总指挥,怎样将父亲几十套各个年代配发的军装打包,怎样将一家人的棉絮装进八二迫击炮箱里,带上什么丢掉什么,这都是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管。父亲关心的只是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便自己挑选一间单独的卧室。父亲长久地坐在他那间紧闭房门的屋里,默不做声。有时候家里没有别的人,有外人在院子里叫门,他任凭来人在院子外面叫,却一声不应。他的目光中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骁悍,花白的鬓角和松弛的两颊使他显出莫名其妙的慈祥,一双被火药燎灼得面目全非的大手安静地搁在老式藤椅的扶手上。只有他的腰,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挺得笔直,即使他坐在那里,也从不塌陷下去。父亲守着他的房间,就像守着他的阵地,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进入,有时候连小阿姨进去叠被子拖地板他也要大发脾气。
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他自己不求上进,他还要怎样呢?”母亲这么说,但母亲仅仅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是要我们真的附庸她。如果我们不懂事,把母亲的意思弄拧了,表现出对父亲怪异性格的不满,那我们可就自讨没趣。母亲会瞪着惊诧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弄不明白她和我们的父亲怎么会生下我们这一群不肖的犊子。母亲斥责我们的口气比她说父亲的更激烈。母亲大声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你们的父亲?你们难道有吗?嘿,别看你们一个个长得骡高马大的,也只有这点你们才多少有点像你们的父亲,别的任何地方,你们半点不如!你们配吗?你还自以为什么似的,你们,连他的一个小拇指也够不上!”母亲这样说。母亲双手叉腰,高高地扬着下颏。母亲在这种时候绝对像极了一头护卫自己伴侣的骄傲的母豹,她的瞳人闪闪发光,她站在那里训斥我们的样子美丽动人。
1967年秋天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那天父亲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回来之后便去翻箱倒柜。父亲把十几套充满樟脑味的军装扔得满床都是,黄色和绿色的军装立刻就使父亲呆板的房间充满了生动。父亲在那一大堆压了多年箱底的军装中翻找着,像个小学生一样拿不定主意。他的举动使母亲感到蹊跷,母亲弄不清父亲在干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是早出晚归,整天待在由花园开垦出的菜地里,种白菜或者萝卜,父亲挑着晃晃荡荡的粪桶在菜畦里穿过,往手心里吐唾沫,然后捏紧锄柄用力锄地。他仍然穿着军装,那是用结实的咔叽布做成的,上面满是黄泥、汗渍和粪水。锁在衣柜里的军装他原本是用不上的。母亲不明白,母亲便问。父亲抓着一件军装怔怔地盯着母亲,仿佛没有明白母亲问的是什么。好半天父亲才哈哈大笑起来,把军装往母亲怀里一塞,洪亮着嗓门说:“什么事?还能有什么事?大喜事!告诉你老婆子,我要进北京去见毛主席了!”
1967年秋天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毛主席突然想着要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军以上干部,这对休息了多年的父亲无疑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毛主席是军队的统帅,统帅要接见他的兵了,父亲在如此巨大的喜讯面前无法抑止住他内心的喜悦。父亲也许还下意识地揣测过这次接见的重大意义,是毛主席要重新整顿军队了?是什么地方又要打仗了?是和苏联或者印度干还是要收复台湾?不管怎么样,不管和谁打,新兵蛋子总没有老兵好使唤。父亲激动得要命。他拿不定主意穿什么样的军装去朝见最高统帅。他吩咐母亲为他找出一副崭新的领章帽徽。他对母亲的针线活不满意得近似挑剔,直到母亲用尺子量好位置屏住呼吸缝好领章帽徽,他又满脸严肃地认真检查了三四遍方才过关。
在那以后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不眠之夜,让父亲食不安睡不宁。他连一天也不愿等待,恨不得拔腿就去北京。好在晋京之前还有许多的事要做。有关部门组织老干部学习各种文件,大家畅谈对统帅的崇敬之情和幸福感受,回忆当年在统帅的亲自指挥下不断打胜仗的革命历程;被服厂的老师傅来为每位晋京人员量尺寸统一制装;军医带着脸蛋红扑扑的小护士来为首长们检查身体,热情而又严格地写下诊断书;宣传队的男女文艺兵们送来一台台文艺节目,让首长们大饱眼福。院子里那些日子就像过节一般充满了喜庆的欢乐,同时呈现着一种让人揣度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