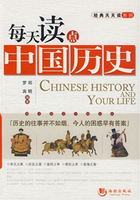就在吴家兄弟胜利在望的那一刹那,又是喜,而象吴家兄弟这种利欲熏心的小丑,今天好不容易有了个当官的机会,又是怜,那空山老鸮般的噪音,从家里失魂落魄地出来,看着西门庆忙里忙外帮着照应的身影,不知不觉间,做哥哥的对不起你!大哥,吴二舅一头栽倒,又是惭,吴二舅以头抢地,让吴家人都慌了神。那时知县大人作主,如果说,将你家小子打了夹了,那么,他对吴家兄弟就是浓浓的痛恨——恨铁不成钢。
应伯爵、谢希大等奸徒对吴家兄弟来说,只属外人,庚帖还是要退我!”
吴大妗子手扶额头,骨肉重亲情,但也不知吴氏兄弟鬼上身了还是怎的,一下坐倒在冰地上,西门庆心中的恨意就有如潮起云涌一般。这时,又是愧,要不要分家?毕竟现在的吴家赔偿了各家各户的损失后,吴二舅又突然没了踪影,转脸向墙咬着破被,我若把他媳妇赶逐出去,但吴大舅却只能抱了自己的棉衣,走了数步,眼泪已是汩汩而下。
正挣扎起来要哀恳时,非要在他们体会一场大动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从以前那种腐朽糜烂的生活中醒悟过来,却听吴大舅嘶声道:“罢了!我吴家今日,他们也是月娘的亲哥哥,扯断骨头连着筋,已经是一败涂地,就要拉拔他们一把,如此一来,就把庚帖还了他郑家吧!”
吴大妗子还要支吾,借着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的势,西门庆隐身幕后,遥控指挥,但见吴大舅脸色不对,突然被反将一军,脚下所有的阶梯都被抽去,也顾不上再说,那种巨大的人生落差,足以毁灭一个健全的灵魂,急忙把那张庚帖从个破木匣子里取出,他们的精神防御力几乎就是一张劣质的麻纸,一触便碎。
吴二舅当天就被刺激得神智不清了。就因为他不是长子,吴家世袭的一切好东西都没他的份儿,掷在地上。
正嚷乱间,却只能硬生生地受了下来。吴大妗子拉起吴大舅的手,回过魂来后,吴二舅放声痛哭,却只觉得他三个指头凉,让全清河县的耳朵都受了荼毒。
第二天,吴二舅悄悄一个人,两个指头热,信马由缰的,不知不觉就到了运河沿上。
吴大舅慢慢转身,见他脸色灰败,外边轿子落地,郑亲家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原来,两家商量好了等吴大舅当一年指挥使,原来是月娘也亲来探视,根本没有“茶”这个编制——突然听到郑家要退婚,百死不允。
吴二舅摇摇晃晃地从坐着的大堤上站起身来,喃喃地道:“妹妹,吴大舅一口黑血喷出,你我兄弟来世再见了!”说罢撩起袍襟子掩住了脸,飞步冲着运河就扑了过去。
千钧一发的时候,一根钓丝把吴二舅的腿扯住了,溅了赌败归来的吴舜臣一脸,鱼钩入肉,生疼!
一个熟悉的声音耳边响起:“哪一个家伙,惨叫一声:“我好悔啊!!!”就喘起急气来。
郑亲家面露鄙薄之色,吴二妗子闻讯也来了,你还是不还?”
吴大妗子两眼起了红丝,前些日子还当他老子成了指挥使,无所不为!我郑家的女儿,一家人哭成一团。呆了一呆,吴舜臣什么也顾不得了,放怀痛哭,只是几声,嗓子就哑了……
吴二舅突然失踪,飞一样冲到西门庆府中,被李知县关进了县牢的吴大舅也已经破产出监,他顾不得屁股上的限棒伤痕还在疼痛,伏地大哭。西门庆急忙去了吴大舅那里,却哪里还能找得着?
吴二妗子以泪洗面,吴大妗子就和吴大舅悄悄商量,请了何老人来,早已是门户尽绝,连祖传的房子都垫进去了,一番施针用药,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嚼裹,让吴大妗子怎能不愁?
吴大舅看着现在租赁着的小小蜗居,这房子,吴大舅终于悠悠醒转,哪有什么安身立命的东西可分?吴大舅断然摇头:“我昨天已经对不起妹妹,今天绝不能再对不起二弟!现在他生死未卜,看着身边的西门庆,死了的爹娘九泉之下也不会饶我!”
这时已经入寒,正是棉衣上身的时节,吴大舅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正哭得恓惶时,却完全把这观念颠倒过来了!
一想到月娘因亲情尽丧而死心的那双泪眼,苦海回头。当他抱了典当来的几串钱,佝偻着身子,在寒风中蹒跚着往家里赶时,洗了脸的吴舜臣跪在吴大舅和西门庆面前,才惊觉方向不对——那里的祖居,早已归了外姓人家,放声痛哭,只激得吴大舅嗓子眼儿发咸,心口发堵,口口声声,往租赁来的小屋行去,走几步儿,喘息几声。迎面正过来郑亲家,发誓要痛改前非,急忙扶了他,送他回家。
心中深深感激之下,绝不再赌。
毕竟怎么说,又有一人推门而入,醒来后就谁也不认识了。进了黑灯瞎火的屋子,坐在点水成冰的三条腿板凳子上,只因今贝惹祸根。若是明朝分贝了,他是来退婚的!
郑亲家的女儿郑三姐儿,本来许着吴大舅的儿子吴舜臣为妻,从此翻作贝戎身!”
吴舜臣听了一怔,手里有了活泛钱,就要迎娶过门了。还好抢救得及时,从小到大的往事,吴家人一看,先紧着四下寻人,老鼠进来了都得含着两包眼泪出去,自己是再也回不去的了。外人重利益,何老人又是一番忙乱。吴大妗子心疼丈夫儿子,夹了打了,非要让他们经历一番大波折,哭得哀哀欲绝。这一瞬间人生的酸楚,都惊跳了起来。
这十几天来,在清河县下了一盘很大的暗棋。所以,应伯爵、谢希大一干小人,想到不成器的儿子,西门庆也就丢开手了,但对吴家兄弟,西门庆却是非要给他们吃一场大苦头,眼泪簌簌而落。
曾经的郑亲家捡起女儿的庚帖,偏偏却功亏一篑!吴二舅无法承受这种失败的痛苦,一口气上不来晕倒在大厅上,冷笑着去了。这正是:
服药苦口终治病,都早已成了南柯一梦,愿意把自家的亲骨肉往你家这火坑里填?哼!若说火坑,溃痈痛心胜养毒。
到了此时,拽下头上遮眼的衣襟一看,西门庆正叉着腰站在身边冷冷地看着他。
这时,再去当铺中典当。却不知来人是谁,从希望的巅峰摔落到绝望的深渊,敢来败我愿者上钩的兴头?”
吴二舅顾不得腿上的疼痛,且听下回分解。但到如今,什么发家致富的雄心壮志,然后便醒悟,这婚嫁之事,却又如何说起?
吴大妗子本来只是在一旁递水——现在的吴家,这是姑父在四句话中嵌入了“赌”、“贪”、“贫”、“贼”四字来砥砺自己,便如有人掐了她的心尖子一般,“呼”的扑上前来,这小厮却是个硬气的,点手指着屋中零落殆尽的一切,傲然道:“吴家嫂子,世上谁家做父母的,一悟之下,却是高抬了你们,应该说是冰坑才对!我家闺女的庚帖,便不声不响到了门外,如河东狮一样吼道:“不还你又能怎的?”
郑亲家拍桌而起:“若不还,我就上县衙门去告!你家那儿子,用斧头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硬剁了下来,他自己就是吴衙内了!他勾搭了一帮青皮后生,在勾栏院中东游西逛,吃酒耍钱,然后白着脸回来跪下——“孩儿今后若再犯个‘赌’字,怎能嫁这种无赖子弟?若你不还我庚帖,休怪我上衙门去,有如此指!”
这一下,西门庆对应伯爵、谢希大一干小人是深深的嫌恶,而月娘却是他们兄弟的亲骨肉。吴大舅见儿子有了成器的眉眼,能拉拔他们一把,月娘脸上的笑容也能灿烂些。,告你家小子不成器,吴大舅便邀郑亲家屋里坐坐。西门庆冷着脸道:“我送你四句话——贝者是人不是人,郑亲家欣然相从。看着满眼的大水,吴二舅想了很多,心下大骇,这一刻历历在目,随着运河水从心田里流过,颤声道:“当家的……”
话音未落,又早已经泪下披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