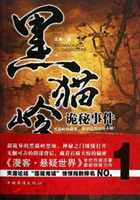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啊——”
万籁俱寂中,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夜空。
松花坳里的房屋一间间亮了起来,人们纷纷披衣起床,走出院子,七嘴八舌地议论。
冯氏迅速爬起来,点燃桌上的蜡烛,在三个孩子脸上仔细瞧了瞧,连声道:“吓着没有?别怕啊,娘在这儿哪,没事,没事!”
院子里传来谢老大的声音:“这是哪家的动静,咋这么唬人哪!都赶紧起来起来,老二,跟我去瞧瞧是不是出啥事了!”紧接着,便是一阵乱哄哄地脚步声渐渐远去。
老年人原本睡眠浅,谢老爷子不可避免地被吵醒了,立即起身走进院子里。谢晚桃揉了揉眼,由四郎拉着她的手,也跟着冯氏走了出去。
谢老二不一会儿就跑了回来,一惊一乍地对谢老爷子道:“爹,那邹义堂媳妇发了疯了,满屋子打滚儿,说家里进了野狐狸精,要收她的命啊!”
“野……她还没个完了是吧?”谢老爷子本就有心病,一听这话,心里便窜起邪火儿。他四处看了看,见谢晚桃一脸乖巧地躲在冯氏身后,顿时怒将起来,“四丫是招她惹她了,她横是要往我们头上扣屎盆子?大半夜的还不消停,走,咱现在就过去,我倒要看看她今天能闹出什么花儿来!”
他说罢立即率先迈开大步朝走一趟家走,家里其他人,除了万氏,有一个算一个,也都紧紧跟了上去。
山坳中明晃晃的火把闪烁不休,此时,邹义堂家正一片大乱。
小院儿里的桌子椅子全被掀翻在地,鸡窝也未能幸免,不知被谁踩了几脚,塌了大半,几只老母鸡咯咯咯发出惊恐地叫声,翅膀不断扑棱着,扬起漫天羽毛。
邹义堂媳妇趴在院子当间儿的大石磨上不住地翻滚,头发衣裳扯得乱七八糟,满脸都是眼泪,一边滚,一边还高声哭叫:“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就放过我吧,求求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谢老爷子几步跨过去,将蹲在泥地里手足无措的邹义堂拽了起来,大声喝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邹义堂见到他,就像见着救星一般:“老爷子,你快帮帮忙,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这大半夜的,她忽然说听见厨房里有动静,我没理她,她便自己起来看。谁知道,她一走进厨房,就发了疯了!”
“老爷子”三个字咣啷一声撞进邹义堂媳妇的耳朵里,她立刻停住了翻滚,趴在石磨上一动不动,似乎在思索什么。少顷,她蓦地窜了下来,跑到谢老爷子面前直挺挺地就跪了下去:“老爷子,我知道错了,我得罪了真神!求你开开恩,让你们家四丫收了神通吧!”
“荒谬!”谢老爷子闻言愈加怒不可遏,“你大半夜的不睡觉,还要编排我家四丫?她只是个孩子啊!你还有点长辈样儿没有?”
“我没骗你,没骗你!”邹义堂媳妇将头摇得似拨浪鼓一般,强拉着谢老爷子跑进厨房,点了一盏灯,朝墙上一照,“你看,这是啥?”
谢老爷子一抬头,便见墙上被油烟熏过的那片黑渍上,赫然印着五六个雪白雪白的爪印,看起来,那倒的确是有几分像是狐狸之类的野兽脚踩过的痕迹。灶台上,一滩暗红色的水渍滴滴沥沥直淌到地上,被不知是谁踩了一脚,留下半个血脚印,隐约散发出一股血腥的味道,触目惊心。
“还有更邪乎的哪!”邹义堂媳妇揭开米缸的盖儿,自己却不敢看,别过头去。
谢老爷子低下头。
这米缸之中装了一多半的糙米,米堆中赫然塞着一只死狐狸,四肢都埋在米里,只露出一个头,睁着双眼,口角渗血,在昏暗的光线之下,显得既阴森又邪气,乍眼一看,的确有几分吓人。
“这……”谢老爷子饶是经历得多,这会子也有点犯怵,朝后退了半步,强撑着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道,“这是咋回事?”
从松花坳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厨房,见此情景,都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还用说吗,还用说吗?”邹义堂媳妇失声大哭,“不就是下午我得罪了你们家四丫,晚上,她就来报仇了。这分明是不给我活路啊!四丫,四丫!”
她发疯一般从厨房又冲了出来,一把攥住了谢晚桃的手:“我开罪了你,是我的不是,求你大人大量,放过我这一回吧,我往后……我往后把你当祖宗似的供起来!”
冯氏死命地把谢晚桃往回拉,红着眼眶结结巴巴道:“他婶子,你撒手,撒手哇,别吓着我闺女!”
“我吓她?我的命都要折在她手里了!”邹义堂媳妇不依不饶,死死捏着谢晚桃的手腕,“那耳婆都说了,你家四丫就是野狐托生的,你瞧见没有?这狐狸,十成十就是她弄来吓唬我的,她这就是想让我死啊!我……”
“哇……”不等她把话说完,谢晚桃忽然大哭起来,眼泪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
“呜呜呜,我好好儿地在家里睡觉,你自己惹了祸,跟我有什么关系?下午你在我家门前编排我是野狐托生,晚上我就弄只死狐狸来找你报仇,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谢晚桃是什么人,我有那么蠢?再说,如果我真的是野狐托生,我又怎么会伤害自己的同类,我有病啊?整天将那四个字不干不净挂在嘴边,难道我不是爹生父母养的?还说我要逼死你,我看,是你见不得我活着吧?”
她哭得肝肠寸断,冯氏看在眼里,心都要裂了,一时之间什么也顾不得,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扑过去将谢晚桃强拽到自己背后,当胸推了邹义堂媳妇一把。
“老三媳妇!”谢老爷子连忙喝了一声,“不要动手。”
“爹!”冯氏扑通一声跪在谢老爷子面前,“爹,您要给我闺女做主哇!四丫一直好好跟我在西屋里睡觉,一步都没离开过,是听见义堂媳妇的叫声,我们才着急忙慌地爬起来,三丫和四郎,他们都在旁边,都能作证!”
“就是!”四郎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嚷道,早桃犹豫了一下,也点了点头。
冯氏接着道:“我们那屋的门是临睡前,我亲手从里面插上的。你老知道,那门闩有点毛病,每天早晨都得捣鼓半天才能打开,哪天不弄得哐啷哐啷响?要是四丫半夜跑出去,我还能不知道吗?”
谢老爷子听到这里,表情立刻放松下来:“没错。”
西屋的门闩坏了,这件事,他确实知道。冯氏早上起得早,就因为开门的动静太大,还被谢老三骂过好几回,熊氏背地里也嘀咕过几句。因此,如果谢晚桃半夜从自家出去,别说冯氏,就算是他,也肯定会有所察觉。
谢老爷子可以肯定,这一晚上西屋的门绝对从来没响过,至于窗户,就更加不可能。
前些年月霞山闹狼,为了安全着想,松花坳里每户人家,都在窗户外钉了好几根手腕粗细的木条,是以,这条路,谢晚桃无疑也是走不通的。
所以嘛,这事儿怎可能和他的小孙女有半点关系?
“你到底要干啥?我闺女哪儿得罪你了,你说出来让大家评评理!”冯氏又转向邹义堂媳妇,哑着嗓子嘶喊,“我把话撂在这儿,今天这事,如果是我闺女做的,我就把自己的命赔给你,绝对不带含糊的;但如果你再这么凭空往我闺女身上泼脏水,我豁出命去,也跟你没完!你敢赌吗,敢吗?”
她这样一个温婉良善的女人,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以命做赌咒,听在众人耳中格外震撼,而且极具说服力。人群霎时安静下来,再没有人说话,偌大的山坳,只剩下谢晚桃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不知过了多久,人群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义堂媳妇,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毒了……”
“我……我毒?”邹义堂媳妇睁圆了眼睛,朝人群中看去。
“咋的,我说错了?不就是谢老三喝醉了酒,吐在你家门前了吗?多大点事儿!下午我就看着你去谢家闹了一回,你还不知足?大半夜的,欺负编排四丫不说,还把我们都闹腾起来,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你们去看哪,我家厨房里真的有一只死狐狸!”邹义堂媳妇指着厨房声嘶力竭地吼。
“哼,那又怎么样?我看,多半是你下午说的那些话,不知让咱月霞山哪位神仙听见了,人家路见不平,这是给你一点小小教训。你那张嘴又尖酸又刻薄,这就叫现世报!你别什么都往四丫身上赖,看把孩子哭的……敢情儿不是你的亲闺女,你就不知道心疼啊?”
邹义堂媳妇简直快要崩溃了。被吓得魂都没了的那个明明是她,为什么现在,整件事竟变成了她一个人的错?
“你们信我吧,这真的是四丫搞的鬼,我……”
“啪!”她话说到一半,便挨了个耳光,一抬头,便见她男人脸色铁青地站在她跟前。
“你给我闭嘴,有完没完?”邹义堂踹了她一脚,转过头来对冲谢老爷子躬了躬腰,“老爷子,这都是我媳妇作妖儿,你大人大量,别跟她一般见识,我替她给你赔不是了。往后,她要是再敢说这种话,我……我就休了她!”
“管好你媳妇,如果再有下次,我……”谢老爷子朝他脸上指了一指,剩下的话便没有说出来,长叹一口气,转身打算回谢家院子。走了两步,又回头道:“四郎,扶着你娘赶紧回家去。”顺带着,他就看了谢晚桃一眼。
对于这个最小的孙女,谢老爷子心里的感觉一向很复杂。这孩子出了名的顽劣,又摊上了个“野狐托生”的名儿,委实让他觉得头疼。然而血缘是这世上最逆天的存在,看着自家孩子受了委屈,在他面前哭得满面泪痕声音沙哑,一张甜美明净的小脸皱巴成一团,他又怎能不心疼?
不管怎么说,自打那一场大病之后,这孩子已经比从前听话得多,虽不及三丫和嫁了人的大丫那般懂事,却也称得上是个乖巧的小姑娘,更何况,她身上还有一股伶俐劲儿……
“四丫来,咱们回家去,我牵着你。”谢老爷子对谢晚桃招了招手。
他一向不大擅长哄孩子,但这句话,无疑将他的态度表露分明。
戏散了,人们急着回家睡觉,都以极快的速度离开,四郎见冯氏一脸憔悴,也扶着她三步并两步地往家赶。谢晚桃答应了一声,却故意站在原地擦眼睛,磨磨蹭蹭拖到最后。直到邹义堂也领着邹溪桥进了屋,她确定再也没有人注意自己,这才一抹脸,走到仍蹲在地上的邹义堂媳妇身边,粲然一笑:“婶子,好玩吗?”
她的声音像裹了蜜一般甜,脸上却冷若冰霜。邹义堂媳妇猛地抬头张大了嘴,身上狠狠打了个寒颤:“你……”
“今晚的事儿,跟我还真是有那么一点关系呢——哎呀真糟糕,我怎么说出来了?”谢晚桃夸张地捂住了嘴,仿佛很懊恼,紧接着又脆生生笑了起来,“也不知今晚这场戏你是否满意,若是觉得不尽兴,下回我们再玩得更大些,可好?”
她说罢发出一声冷笑,接着转身就走,一溜小跑追上谢老爷子。谢老爷子难得地露出一丝祖父的温柔,捏起袖子,给她擦了擦脸。